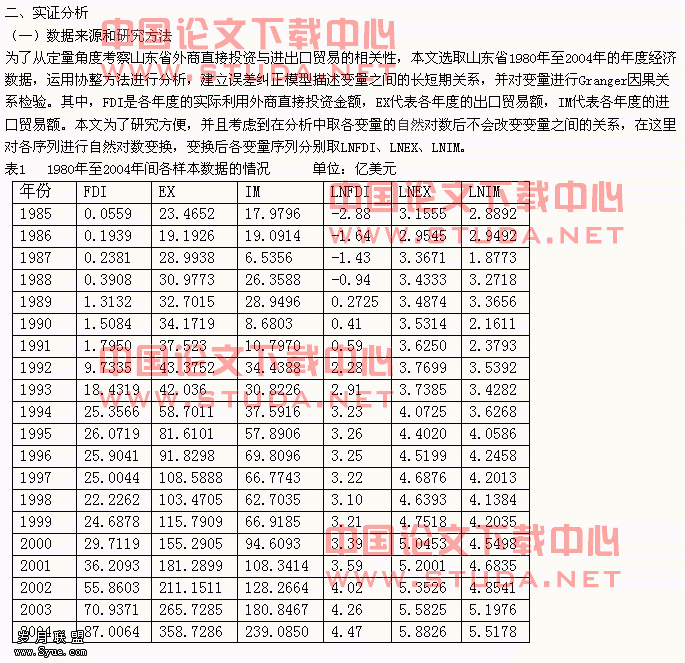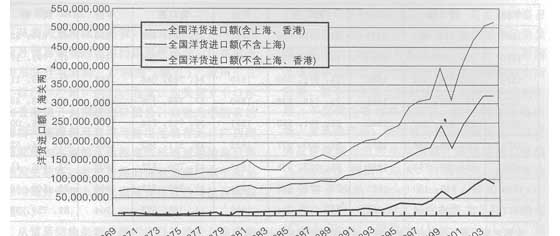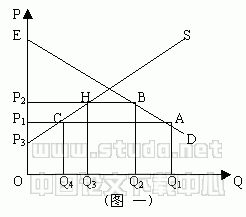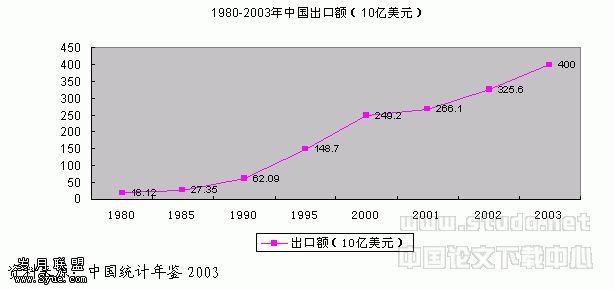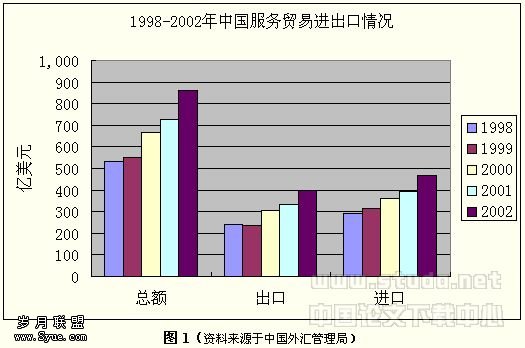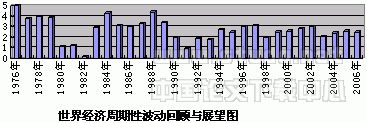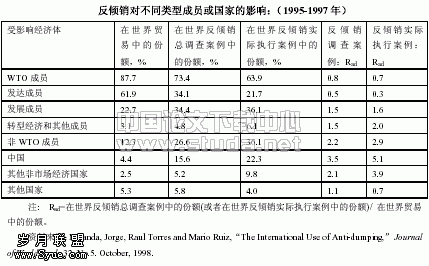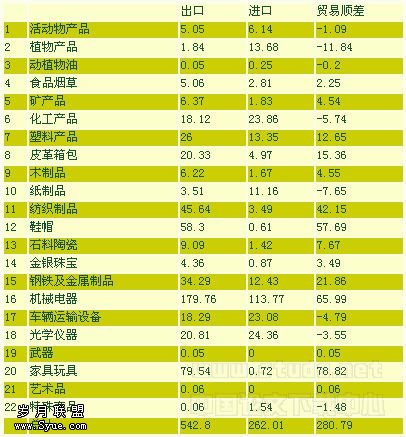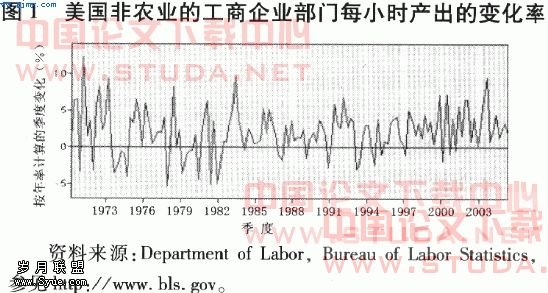浅谈唐代海外贸易管理
摘要:大体说来,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对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的管理两个方面。以下依据有关史料,分别予以探讨。
关键词:唐代;海外贸易;管理
Abstract: Speaking generally, Tang Dynasty ultramarine trade's management, mainly includes the Tang government to pay tribute the trade and the city ship trade management two aspects. The following basis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gives to discuss separately.
key word: Tang Dynasty; Ultramarine trade; Management
(一) 朝贡贸易的管理
唐政府不仅与其周边诸少数族政权之间存有朝贡贸易,与海外诸国之间也存有朝贡贸易,同样在政权关系的色彩的光环下,进行着实际上的物与物的商品交换。史料表明,在朝贡使的礼仪接待和贡物的回赠酬答方面,唐政府对海外诸国也实行着与对周边诸蕃相同的制度和规定。《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赞语称唐对朝贡使“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1] 就对朝贡物品的酬答而言,唐政府也有着一套较为细致的制度,其详见前文民族贸易的管理部分,兹不赘述。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朝贡使团入京觐见人数的控制上,唐政府对海外诸国使团的限制,要比对周边诸蕃使团的限制严格得多。《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鸿胪寺》载云:“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规定由陆路而来的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境时边地政府部门要将其使团人数的一半留于边境安置,只准许另一半人员随同使者入京觐见;对由海路经广州入境的,则只准许使者及随从二人入京觐见,对海外诸国朝贡使团的入京人数有着明文限制。而周边诸蕃朝贡使团虽有时因过于宠大要由边地政府部门留其一部分人员于边境外,对其使团入京觐见人数,唐政府并无制度上的明确规定。对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京人数的严格控制,反映的应是唐政府对国家安全更为谨慎的考虑。
唐政府对非经广州而由其他沿海口岸入境的外国朝贡使团的管理,可由《空海入唐求法记》寻得一些端倪。记文载空海随同日本国朝贡使团,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当时日本使船,率由扬子江向苏、扬。闽疆僻左,罕睹外人,州吏闭船待命。空海乃代大使上福州观察使书……刺史阎济美阅之感动,因开船存问,给资粮,借屋十三烟,并奏长安取进止,全船感激流涕。数十日敕令至,大使给七珍鞍。十一月三日,一行二十三人,溯闽江向长安,空海与焉。余人及来船则回航明州,以待大使之归”。入京使团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达长安以东的长乐驿,二十三日,宦官赵忠将飞龙家细马二十三匹来迎,兼持酒脯宣慰,由春明门进城,入住宣阳坊官宅,二十四日,国书、贡物附监使刘昂献上,皇帝嘉纳。[2] 可见,日本国朝贡使团到达福州之地后,福州地方政府一方面招待使团,一方面上报朝廷请示如何处理。等皇帝敕令到达后,州府乃准敕允许使团中的二十三人入京觐见,其余人等及所乘船舶回航明州以等待入京使团的返回。入京使团到达京师长安附近时,由宦官赵忠负责一番接待,进行慰劳,然后进入京城,被安置在官宅中居住。次日国书及贡物由宦官专人进献,德宗皇帝嘉纳。虽然入京使团的人数不止三人,但是由此仍可看出,政府在朝贡使团的入京管理上,一是行事十分谨慎严肃,二是也有着明确的人数限制。从宦官赵忠率二十三匹飞龙细马迎接使团,可以推定二十三人的使团入京规模是早由德宗所颁“敕令”规定了的。总而言之,作为唐政府与海外诸国沟通政治关系的辅助手段,朝贡贸易有其特殊意义。这类贸易不与国内百姓接触,完全由唐政府一手操办,实为官方贸易。
(二) 市舶贸易的管理
这里的市舶贸易,也可称之为通常的海外贸易,是指不以沟通政治关系为目的、专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海外贸易。在唐代,市舶贸易集中在东南沿海之地,而以广州为中心。如天宝九载(750),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到达广州时,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崑崘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3] 市舶贸易已有相当规模。从现有史料看,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管理经历了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上的逐步变革过程,以下详为论之。
最早反映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史料见于《唐会要》。《唐会要》卷66《少府监》:“(高宗)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有学者认为,敕文所云“所司”应即是唐政府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广州市舶使院,并认为到显庆六年(661)或稍前的时候,广州市舶使之职即已创置。[4]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依笔者愚见,高宗的敕文是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做出规范。敕文中的“所司”是泛指中央各有关政府部门,并非专指某一机构。而敕文中的“本道长史”,显然指的是高宗永徽之后于广州设立的岭南节度使府长史,即岭南道长史。[5] 敕文的大意是规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如果需要购买海舶之物,则要在每年的四月份以前,支付需要购进物品的所须钱物,交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去负责购买。长史在海舶到境十日之内,将官方拟购的物品购买完成。官市之后再允许外商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长史购进之物,要送到中央少府监,由少府监选取一些精品送入皇宫,供皇帝、皇室使用,其余物品,再发送各有关政府部门。
就对市舶贸易的管理而言,敕文所云有两个要点:一是外商以船舶载货物到达广州后,先要与唐政府官方进行交易,然后才能与国内百姓进行交易,即政府官方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是政府官方购物由岭南节度使府的长史负责,即由岭南节度使的属僚负责,尚无专门的市舶贸易管理机构及管理官员的设置。不过,长史作为正五品上的职事官,为岭南节度使府的高级幕僚,这足以反映出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管理的重视。
另一条较早的史料见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光宅元年(684)七月条载:“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崑崘所杀。元睿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略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崑崘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史料表明此时市舶贸易的管理权仍属岭南节度使府,即广州都督府所有,由都督府属僚具体负责,仍无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在管理体制上,与高宗显庆六年时的情况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已故著名史专家傅筑夫先生,依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所载“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莞四色,并押解一分”,推测从唐初起,南海市舶贸易就置于市舶使的管理之下。[6] 这一推测是错误的。对顾炎武所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已指明其误,是误将《宋会要》关于宋绍兴十七年之事记为唐贞观十七年之事。[7] 所言甚是。
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发生变化至迟不晚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显示这一变化的史料见于多处。如《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载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使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新唐书》卷112《柳泽传》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使,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书奏,玄宗称善。”《册府元龟》卷101《帝王部·纳谏》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岭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帝嘉纳之。”同书卷546《谏诤部·直谏十三》亦载,“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云云。
诸处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均载明玄宗开元二年时广州已有市舶使之职的设置。需要指出的是,《唐会要》关于此事的记载与诸处史料有所不同。《唐会要》卷62《御史台下·谏诤》载云:“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监选司、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把诸处史料所载之“市舶使”记为“市舶司”;“监选使”记为“监选司”。对《唐会要》的这一不同记载,喻常森先生已研究辨明其误。[8] 遗憾的是,迄今仍有一些学者还将《唐会要》的这段记事据为信史,错误地断定开元二年时唐政府已在广州设立管理市舶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从诸处史料不难看出,市舶使周庆立的职事本官为右威卫中郎将,官阶四品,是唐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可以肯定,他是以中央禁卫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出任广州市舶使。根据唐代惯例,周庆立可能是由君相直接任命出使的。[9] 这表明,开元二年时,市舶使已握有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也反映出唐中央对市舶贸易管理的愈益重视。然而,由于诸处史料所云太过简略,周庆立管理市舶贸易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他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限有多大,是全部拥有,还是部分拥有,也不清楚,但是,毫无问题的是,市舶使的设置说明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已发生重要变化。幸好,后来的相关史料证明,市舶使对市舶贸易并不握有全权,而是形成了与岭南节度使共掌市舶贸易的管理新体制,取代了先前由岭南节度使属僚具体负责的旧体制。
上述史料说明,在自玄宗开元十年至唐中晚期,一直有宦官市舶使的存在,多数由朝廷差遣、少数由岭南监军使就地充任。从史料中还可看出,宦官市舶使对市舶贸易并不拥有独立完全的管理权,岭南节度使也参与市舶贸易的管理,也有着对市舶贸易的管理权,形成了宦官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共同负责官市,以“賝赆纳贡”,确保向朝廷“进奉”。笔者以为,时下许多学者所持之市舶使是专门管理市舶贸易的官员的认识并不准确。
需要强调的是,开元二年后,除了以朝官和宦官充任市舶使之外,还有以岭南节度使兼任市舶使的情况。如德宗贞元年间,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即兼任广州市舶使,一身而二任。[13] 也有以岭南节度使府的幕僚充任市舶使的情况。如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马君墓志》所载墓主人马某即曾以幕职出任广州市舶使。[14] 这说明,开元二年后形成的由市舶使和岭南节度使共同掌理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并不十分固定,只是一种大体上或总体上的格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市舶使属使职差遣,需要时,则由朝廷任使派出,不需要时,则仍可由岭南节度使府负责,实行与高宗、武后时期相同的管理方法。不过,就管理的性质而言,不管是由岭南节度使府单独管理,还是由岭南节度使与市舶使共同管理,是并无差别的,即都是由唐政府的官员,按照政府的利益进行管理,都具有由政府官方一手操控的显著特点。而这一特点还可由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看得出来。
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也有一个前后变化过程。前述高宗于显庆六年所颁的敕文,明确规定在由岭南道长史完成官市后,听任外商与国内百姓进行贸易,说明此时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内容即是官市。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所云市舶使对外商“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15] 的管理内容,从该项记事前后皆述贞元、元和间事推测,应是德、顺、宪三朝时期唐政府对市舶贸易的具体管理内容。这比高宗时期有了重大变化,管理内容增多起来。后来到文宗朝时期,唐政府对市舶贸易规定了纳舶脚、收市和进奉的三项具体管理,制度上的规范更加明确。[16] 唐政府对市舶贸易具体的管理内容虽有前后时期的简繁变化,但这些管理的共同特点是市舶贸易必须首先满足政府的官市或征税、索取的欲望,即以政府获取利益为前提,市舶贸易的生死盛衰实际上操控在唐政府手中。
总起来说,市舶贸易管理体制上的调整,以及管理内容上的由简到繁,反映了唐中央对市舶之利的日益重视。事实上,随着对市舶贸易进行管理的内容的增多,特别是征收重税和进奉聚敛,使得市舶收入在唐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17] 一语道明市舶收入在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 境内居留外商的管理
作为市舶贸易管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唐政府对居留境内的外商也有着相应的管理措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蕃坊制的创立是这种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表明,至迟在文宗太和末年,唐政府即开始在外商聚集的广州、泉州等地设立蕃坊,[18] 作为外商的集中居住区和商品交易区。蕃坊有蕃长或都蕃长负责,对外商进行集体管理。蕃长、都蕃长的产生,可能由外商推举,但须经唐政府认可,或者由唐政府直接挑选任命。有的还被唐政府授以勋官,如《唐会要》卷100《归降官位》载,“(昭宗)天祐元年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宁远将军”。蕃长、都蕃长的职责,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宋人朱彧《萍州可谈》卷2所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大体上反映了唐代时的情况。[19] 有关史料表明,唐代时蕃坊蕃长、都蕃长所掌蕃坊公事,主要包括管理坊内商品交易活动、处理坊内的违法犯罪事件及主持宗教活动;所掌招邀蕃商入贡,主要是指代理外商与唐政府进行商贸交涉。[20] 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蕃长、都蕃长须由唐政府承认任命,他们实际上是代理唐政府对外商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虽享有一定的权力,但必须对唐政府负责。另外,毋需证明的是,在蕃坊设立之前或不在蕃坊之内而在其他地方进行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外商,也必须遵守唐政府关于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的管理制度。总而言之,外商入境后的商贸活动处在唐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
综括而言,虽然现有史料所反映的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内容尚不够具体清晰、管理的制度化方面也不很规范成熟,但前后管理表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反映了唐政府对海外贸易之利的日益看重。市舶使的设置更表明了封建朝廷已直接插手海外贸易的管理,与隋代以前海外贸易概由地方政府管理大有不同,这是唐代海外贸易管理上的一大。政府对海外贸易管理的强化,虽不无积极作用,但其中的官市优先以及重征关税、进奉掠夺等,无疑会破坏海外贸易的真正繁荣,损伤外商来唐贸易的积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外商与国内百姓的直接的商品交流,从而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也不无阻碍作用。我们认为忽视唐政府所体现的封建主义对海外贸易管理所起的消极作用,无益于全面地认识唐代海外贸易管理的实质。
注释
[1] 《新唐书》,第6264-6265页。
[2] 转引自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第14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向荣校注本。
[4] 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载《史研究》1992年4期;乌延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载《教学》1957年2期。
[5] 据《旧唐书》卷141《地理志四·岭南道》载,唐高宗永徽之后,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州中都督府都督统辖,谓之五府节度使,亦即岭南节度使,管理“南中”之地。
[6]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第4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陈裕菁译《薄寿庚考》第一章注1,第7-8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8] 喻常森:《海交史札记》,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
[9] 参张国刚:《唐代官制》,第169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0] 《中国钱币》2001年1期。
[11] 参《全唐文》卷473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第4828页。并参《资治通鉴》卷234德宗贞元八年六月条,第7532-7533页。
[12] 《全唐文》卷764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第7945页。
[13] 《全唐文》卷515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第5235页。从表文可知,王虔休一身而二任是“亲承圣旨”,即经过唐德宗的亲自授权。
[14] 见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4期。
[15] 《唐国史补》卷下。学津讨原本。
[16] 参《全唐文》卷7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第785页。
[17] 《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第4633页。
[18] 范邦瑾:《唐代蕃坊考略》,载《历史研究》1990年4期。
[19] 参方亚光:《唐代外事机构论考》,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