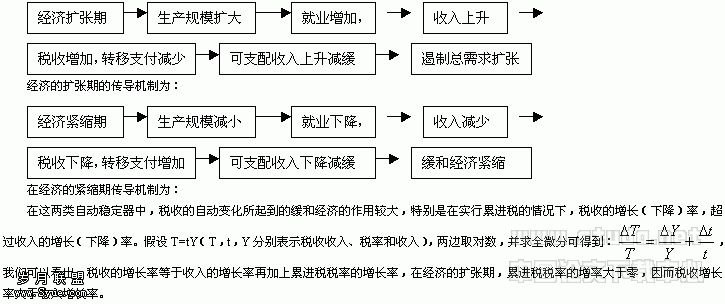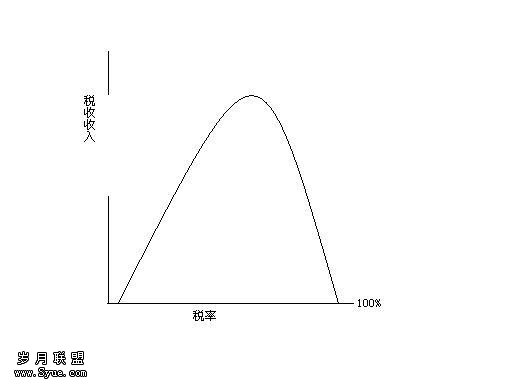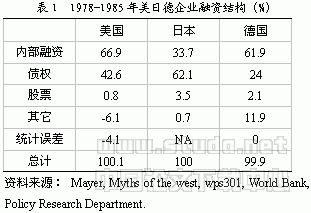土地财政/土地流转
编者按:过去30年来,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土地问题对正在发生的这些变革有着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中国渴望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社会稳定,而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权利的分配和安全必然成为举足轻重的砝码。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土地税收一直是重头戏;在各级政府的相互关系中,它也扮演着十分微妙的角色。土地相关事务及其财政安排,与财政的稳定和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中国的旧城区改造拆迁,或者农地征迁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政府强行征地,已成为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来源。对于那些可以被称之为“芸芸众生”的人们来说,房屋和土地是他们人格权、生存权不可或缺的构成。然而,中国特有的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土地的正常转让,在这个市场上,由于不稳定、缺少政策支持、法律约束等原因,土地的价值被极大地低估。政府给予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渐进式改革的土地流转正在悄悄进行,小产权房市场依旧繁荣。
应对土地问题——慎重!
30年间,中国农村地区经历了重大变革:公社解散了,家庭责任制重建了小农经济;30年后,随着商品性农业不断扩展,农民开始向城市移居,中国正面临着农村生活的另一重大变化。然而,十七届农村事务的变革尤为艰难:干部和农民争夺土地权,城乡地区之间扩大的收入差距激起社会不满,城市拒绝向农村移民提供社区服务。
为何在此时?
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关注农村问题,原因很多。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随着农业税在2006年被取消,地方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土地的征用。据香港《商报》所说,“仇富仇官情绪”有着强化的趋势。类似地,《南方周末》报道,国土资源部“每年收到数十万来自农民的投诉”。而由此导致的矛盾占到了群体事件的65%之多。然而,决策者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问题。据《望》周刊报道,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居民寻求更好的膳食,这一直以来都在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而这又促使价格的上升和进口的增长。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大约相当于在国外用了3000万公顷的土地,而考虑到中国大约为1.2亿公顷的耕地面积,这一比例实在可观。
除此之外,城乡地区的收入差异已经造成农村地区相当多的不满,而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开创一个“平等对待城乡工人”的体系。《望》周刊称,有必要“使长期流入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在社会权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转化”。换句话说,有必要强调户口问题,正是这一户籍体系,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造成了二元社会经济体系。最后,对于中央领导来说,在发起农村改革的30周年纪念日,回到小岗村,回到这个改革的标志性发源地,这种诱惑实在无法抗拒。
所有制问题
或许最敏感、最需要协商的问题就是有关所有制的了。无疑,一些社会改革者曾希望全会能够正面解决这一问题,就像林权改革所做的那样。知名改革家高尚全向香港凤凰卫视表示:“如果允许农民卖土地,那么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同样会增加的还有大陆其他商品服务的内需。”类似地,社会学家于建嵘说,土地应该“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这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此外,如果农民选择卖掉土地,那么从土地转让中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可促进农民向城市流动。
对于弥补农村地区干部和农民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明确所有权也至关紧要。显然,干部和农民的关系是群体事件的症结所在,其原因也很简单:在现有体系下,拥有土地的是“集体”,而农民无法和土地的潜在买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讨价还价。因此,农民无法从土地卖得的高价中获益,就会愤恨从出售土地中获益的地方干部。
启示
从许多方面来看,土地流转的渐进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行动:企业依靠当地政府的帮助,让农民移出土地,支付微薄的补偿,同时在土地上建立起商业农场。现在,中央政府竭尽所能,为土地权的有序流转和城乡地区渐进一体化勾画前景。在此过程中,政府尽量平衡相抗争的价值。一方面,政府设法向农民确保,其土地合同权利将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政府敦促合并土地,以使商业性农业得以发展。同时,政府尽力在城市化和避免过快发展(导致贫民窟)的意愿间进行权衡。此外,要解决农村地区的土地问题,不能不强调户籍制度,可是该制度扎根中国政治体系(和控制机制)颇深,只能进行渐进式变革。考虑到所有这些相争的利益,共产党在发布文件时选择慎重就毫不奇怪了。然而,回避了所有制问题,共产党使农民对来自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压力无力抵抗,而留下的体系似乎在面对经济压力时一直频频让步。这看上去是个秘方,似乎能解决长久以来的农村矛盾以及中国农民被剥夺权利的问题。可是尽管如此,通过宣布土地合同将“长久不变”及要求土地流转的有序市场化,共产党已经开始走近所有权问题,或许也在为今后更大的变革开启道路。
中国的“致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