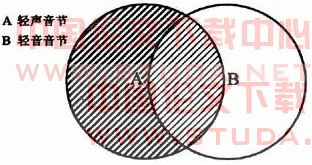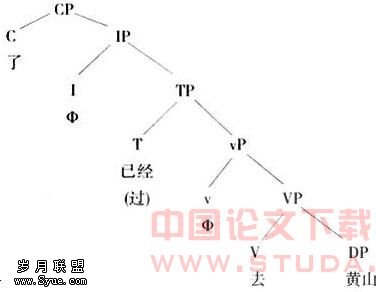用先进的当代思想去研究古典文学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论文摘要:学术研究在求“真”求“善”,文学则在此基础上求“美”。研究古典文学,主要在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素质,使之更崇高、纯洁、美好,所以,不能对古典文学只作纯文学的研究。古典文学的“用”不是实用主义的“用”,研究者必须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用我们当代先进思想去研究。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意识问题,在我看来,本不成为问题。因为研究过去,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不管哪个时代,谁也知道,著书立说,是给当代和后代的人看的。问题是自觉与否。
例如王国维,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使后人研究“兄终弟及”的王位承袭制度时,更准确地理解了“国赖长君”的道理。
这看起来似乎和我们当代无关,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不然,它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逻辑:奴隶主政权为了统治的巩固、秩序的稳定,它深思熟虑,设计出当时认为合理的王位继承方案。这一方案直到春秋时期,吴国还在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还曾嘱咐宋太祖死后应传位于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那么,这一制度后来怎么又让位于父传子的世袭制呢?原来兄终弟及制多次发生抢班夺权、兄弟相残的现象,因此认为索性确定立嫡长子,以免旁支的觊觎。当然,如无嫡长子,则立贤。而所谓贤,全凭“父皇”的认定,这就必然产生伪装,如隋炀帝之蒙骗其父隋文帝。这一继承人问题,纷纷扰扰,不但苦恼了,也苦恼了外国;不但苦恼了古人,也苦恼了今人。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勉强为这一纷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现当代人懂得这些,就既明白是这样过来的,一切存在过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断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转化为不合理的,最后,皇权的专制必然为民主的所取代。所以,研究过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历史的真相。
但,一切过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我们继承发扬善的,批判扬弃恶的,无论正反面,都可给后人以裨益:惩恶而劝善。
求“真”与“善”,是和(包括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而文学则在“真”、“善”基础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文学拥有“美”的专利。之所以出现“文”、“理”现象,背景或实质是由于“情”与“理”的存在。求“真”与“善”,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求“美”,则是感情的思维活动。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即前者,而形象思维则指后者。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任何人不能只有理性生活而没有感情生活。事实上,人的一生,比重占得大的是感情生活。感情生活为什么要追求“美”呢?因为正确而丰富的感情生活,必定是崇高、纯结、美好的精神生活,人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生活,才能脱离动物的本能。
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正是为了提炼我们的精神素质,使我们成为高尚的人,大写的人。所以说“文学是人学”。
明乎此,则研究者对古典文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完全是为了人的精神的升华。可以说,一切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为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心灵的洗涤,精神的昂扬。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深刻地指出了研究过去历史的“真”,都是为了当代人们的需要,谁也不会为古而古。
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即某些学人提出,研究古典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体,进行审美追求,作纯文学的研究。我不附和这种说法。窃以为古典文学研究不能仅限于美的领域,它必须在“真”与“善”的基础上来进行审美活动。
所谓纯文学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学形式的研究上。我认为,一定的形式总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像彼尔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实并没有脱离其相关内容,不过涵义隐晦,不易探测而已。现在有些学者研究《诗经》的四言、《楚辞》的杂言、汉代的五言、魏的七言,探索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这些似乎是纯文学的研究了,但是,我总以为,这些变化,都是和有关的人和事的内容的需要分不开。
比方《诗经》以四言为主,这是由于《雅》、《颂》的内容庄严肃穆,需要偶数词语、方正句式来表达;而《风》诗,据钱穆、朱东润等先辈研究,并非出自民间,和《雅》、《颂》一样,也是贵族所作,所以,基本上也是四言为主。当然,这跟先秦时代人们的个性单纯,语言结构简单、书写条件困难,也有关系。
至于《楚辞》,以屈原为例,他满腹烦忧,需要长吁短叹来发泄,加上南国民歌与北地不同,悠扬宛转,藉以抒发其缠绵悱恻之情。屈原的君国之恫,正好和民歌的风格一致,这就形成了《离骚》、《九歌》等的杂言体。
至于汉代的五言,魏晋以后的七言,则是由于时代越,人事越复杂,人的感情也日益多样化,这就在言志抒情的诗歌形式上,认识到四言诗的两个偶数的句式太呆板,太单调,于是发展出五言,有偶数有奇数,如“行行重行行”,偶奇偶,这一新形式就更方便情绪的抒发了。
后来发展到魏晋以迄于今,人的感情更丰富多彩,于是产生七言,如“秋风萧瑟天气凉”,偶偶偶奇;“草木摇落露为霜”,偶偶奇奇奇。这就更能充分地委婉而曲折地多变化地抒发诗人的激情或柔情了。
那为什么不向九言以下再发展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度(degree)”的问题了。凡事都有一个“度”,也就是极限。人的口腔、气息只能以七字为正常的“度”,这就是民歌何以迄今仍是七言的缘故,文人诗也是这样。 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明世上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即使先民陶器上的云雷纹和波浪纹,也寄托着先民们的素朴的神秘的情愫。换言之,研求古典文学,不能只限于审美活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和当代现实的效用问题,我觉得还要说几句。所谓“有用”、“无用”,据我看,只要我们的成果符合“真”、“善”、“美”的原则,它必然是有用的。问题是这个“用”不能太机械,文学,甚至人文的“用”,不是实用主义的“用”。《中外文摘》2007年第10期《沉浮于学术与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一文得好:“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中外文摘》2007年第2期摘录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谈到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当时的学生“大多对冯友兰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所谓身份,实质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回顾我个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一向重视对清代诗文的研究,即因清人和我们距离最近,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感情,也和我们大体相同。我们当代的先进思想是“民主”与“法治”,在郭丹教授对我访谈时,我们谈到拙著《清诗流派史》,我说:“从我的著作动机来说,我特别想探索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看当时士大夫的灵魂,怎样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痛苦,呻吟,挣扎,或转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样从西方获得民权、自由、平等诸观念,从而产生民主意识,把目光从圣君贤相身上转移到广大的平民百姓身上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在另一处,我又谈到:“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识的成因;而写《在学术殿堂外》,则是反映或当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同上)在《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14页论吴兆骞时,我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二十三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扭典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怒怼君上之意”。
我说的吴兆骞这则诗论,是其诗集《秋笳集》附录的《答徐健庵司寇书》,摘录如下:
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穷而后工,仆谓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如孟襄阳之不遇,杜少陵之播迁已尔;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耳已尔;至若蔡中郎髡钳朔塞,李供奉长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厄困之尤者,然以仆视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内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阔矣!同在覆载之中,而邈焉如隔泉夜,未知古人处此,当复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穷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惟其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万里冰天,极目惨沮,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所云矣。
同样的这一段话,同样一部《秋笳集》,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是那样一种分析,而我是这样一种分析。这就是因为我是在用当代的先进思想去剖析那孤苦灵魂,从而豁显出皇权专制的残酷、阴冷、非人道。而纪昀等则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这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限。就在纪昀当时,也有先进思想,即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揭示的清王朝御用程朱“以理杀人”的罪恶本质。所以说,一定要用当代先进思想去研究过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