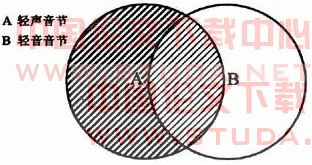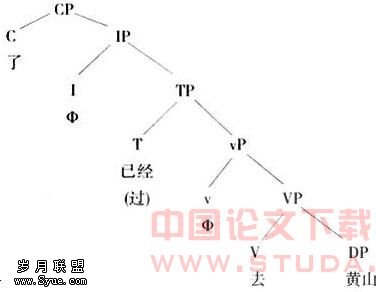以《红字》看霍桑的宗教观
摘要:纳萨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由于清教自身的复杂状况,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复杂的。《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其中也深刻地体现了他对清教的认同与怀疑:一方面对人性恶与救赎之路进行深入挖掘;一方面又对清教的严酷极端予以批评和揭露。就整篇作品而言,后者占据了主要方面。本文通过对《红字》中清教对主要人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方面的讨论,来揭示霍桑矛盾和彷徨的宗教观。
关键词: 霍桑 《红字》 清教
引 言
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在欧洲的史上,宗教更是无处不在,特别是基督教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渗透于欧美文学中。基督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扎根在信仰上帝的人们的心里,主导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精神世界中不可获缺的存在。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就把关注的领域集中到宗教这方深沉而宽广的土地上。出生于清教世家的霍桑,自幼丧父随寡母寄居在外公家,超验主义对他的影响很深,再加上他很早就潜心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史,这些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但霍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对于清教自身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他有着困惑和怀疑。作为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最典型的体现了霍桑对待清教有着矛盾性这一特征。本文通过对《红字》中清教对主要人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方面的讨论,来揭示霍桑矛盾和彷徨的宗教观。
一、 原罪与救赎之路
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的经历,是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得拯救的典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踏上了痛苦的赎罪之路。《圣经》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救赎作为清教教义之一,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方面,霍桑是认同这样的清教教义的。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在霍桑看来,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后个人对待罪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个坚定而具有神奇般个性的女性——海斯特·白兰,由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受到清教教会的谴责。她胸前被佩以红字“A”做为惩罚并当众受到辱骂和羞辱。红字“A”针针扎进了海斯特·白兰的心里,即使“把那个记号遮起来”⑴,红字“A”是罪与罚的证明,是一个女人恶的体现。为了获得新生,海斯特·白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携带女儿在郊外的一间孤僻的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漫长的救赎之路。在霍桑看来,海斯特·白兰是有罪的,她犯了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罪,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欺骗罪,她和齐灵沃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沃斯不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向牧师暴露齐灵沃斯的真实身份。这样的手段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是为了爱。海斯特·白兰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牧师丁梅斯代尔,但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而她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自己的过失,以至于许多妇女向她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寻求安慰和忠告。“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能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1]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⑵“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⑶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霍桑《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作为牧师,却于海斯兰·白兰有了私情,这对于上帝的道德观是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当海斯特·白兰独自站在刑台上被人羞辱责骂,他却高高站在露天看台,笼罩在所有人的信任与崇拜下。为了保住地位和名声,他成了隐秘的罪人。他在欺骗了所有人以至于上帝之后,竟然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对公众的不负责和对上帝的亵渎。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我惩戒: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绝食反省悔悟,私下在自己的胸口烙上火红的红字“A”,“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颓废的趋势了”,⑷再加上齐灵沃斯把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丁梅斯代尔身上,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并终于走向刑台,在荣誉的顶峰,彻底坦白了自己,用最后一口气展示了胸口上的红字,倒在海斯特·白兰的怀抱里,从此也就从那个解不开的结中解脱了出来。霍桑让丁梅斯代而受到了长达七年的灵与肉的折磨,这比公开受罚更为残忍。霍桑想要表明为实现生命的意义的不朽是要做出相应的努力的,从而才能使无依的灵魂和有罪之身获得精神上的安定和肉体上的愉悦。
齐灵沃斯,是一个由受害者变为罪人的人。就他与海斯特·白兰的结合本身来说就是一种罪,因为这种婚姻是错误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的复仇上,霍桑认为后者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的周旋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灵魂、伤害他人的情感。复仇的种子深深的埋进了他的心里。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有着深沉的恶毒。正如丁梅斯代尔所说:“海斯特,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世上还有一个人,他的罪孽与这个亵渎神圣的教士还要深重!他阴险的侵犯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心。”⑸然而,齐灵沃斯的生存是有赖于丁梅斯代尔的,一旦牧师死去之后,他也失去了活着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的死去。罪恶深重的齐灵沃斯临死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时霍桑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宽恕的,有罪之身同样可以净化自己不洁的灵魂,这也是能获得救赎的。
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的生活精神中”。[2]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二、神性与人性压抑
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我们能看到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一定积极作用,但这毕竟是表层的。透过表层,我们也清楚的看到霍桑对清教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疑惑,这是由于清教对人性压制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
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但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缺陷:对外,清教主义者极端的迫害异己;对内,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性进行压制,主张禁欲主义。《红字》表现更多的是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严酷的教权统治下,宗教与几乎等同,支配着人思想的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是教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思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判断。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也许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极端。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权威的社会律令时,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保不住在人为操作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在《红字》中,我们始终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压力的阴郁之气,也更直观的看到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斯特·白兰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沃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沃斯近两年的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白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⑹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的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的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⑺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当海斯特·白兰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的会想起圣母的形象。”⑻当统治者的魔爪伸向她的女儿小珠儿时,海斯特·白兰不顾一切的公开反抗,据理力争,终于使母女没有分离。作者给予了海斯特·白兰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对清教严酷不近人情的一面进行的抨击。
丁梅斯代尔,他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得很高,而且养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的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⑼的人,但它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他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丁梅斯代尔与海斯特·白兰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有着神圣加挲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就是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齐灵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白兰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 白兰的青春。当海斯特·白兰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的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姆斯代尔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⑽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沃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的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沃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虚伪、残酷的一面。
小珠儿,作者把她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的不朽的花”⑾ ,“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⑿年纪虽小,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练出的凶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的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了小珠儿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在霍桑所表达的情感上讲,是有一种倾向性的,倾向于自由、美满、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的。
霍桑继承了启蒙主义者的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从每个人的人性出发,用抽象的形式和象征的手法揭露了清教的阴暗面,进而探索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结束语
《红字》体现了霍桑的宗教观,通过对其中各主人公在清教影响下,对待各种境遇不同态度的讨论,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霍桑思想的彷徨和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有罪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类似于红字“A”的罪的符号,每个人也都需要靠上帝的信仰与相应的行为来获得救赎。人人都有罪,人性都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是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霍桑心中的一个结。在其短篇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3]中,布朗发现他周围所有的人,无论是敬重的教长,还是他的亲人,都秘密的赴魔鬼的约会。《胎记》[4]中的家爱尔默的美貌妻子乔治安娜脸上有一块胎记象征着“凡人的不完善”,他试图去掉这块胎记,结果随着胎记的消失,乔治安娜的生命也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布朗,还是乔治安娜或是海斯特·白兰,霍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人类天生的自我完善的愿望,又总是让他们在罪恶的神秘中去探求救赎之路。霍桑对清教善的一面持有肯定的态度,但更加极力反对的是清教极端,偏执和严酷的一面。《圣经》[6]宣扬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审判一个人的灵魂,而自认为代表上帝意志的清教主义者却让海斯特·白兰在众目睽睽下接受凌辱和惩罚,在霍桑看来是极不人道的。事实上清教会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干着违背上帝仁爱宗旨和人性天理的勾当。霍桑思索人本身应有的生命状态,肯定了人在社会中应有合理欲望的追求,揭示了清教不合理的婚姻和伦理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巨大伤害。连霍桑本人对自由和解放都有着强烈的要求,这也是由于霍桑家庭中阴郁、压抑的气氛有关。无论是有着圣母形象般的伟大女性——海斯特·白兰,还是始终生活在痛苦笼罩下的丁梅斯代尔或者是恶毒但被视为清教教会朋友的齐灵沃斯和漂亮的小珠儿,在他们身上都会看到追求幸福影子。
霍桑在《红字》中肯定了某些清教信条,但更多的抨击了清教的残酷的条例和律令。他认为上帝是博爱的,人人都有被救赎的可能,但更多的宣扬的是人性的张扬,赞美对幸福应有的强烈的追求。所以,就整篇作品而言,霍桑揭示清教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制还是占主要方面的。从《红字》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霍桑的宗教观是复杂的,是矛盾的,这也使得《红字》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
谢辞
这篇文章的最终完成要感谢人文学院中文系马丽珠老师,她帮助我明确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更是在百忙之中帮我修改,并且提出十分中肯和宝贵的意见。
感谢这四年授予我知识的老师们,是诸位老师的教诲使我拥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是诸位老师的真知灼见使我的写作思路清晰明了,从而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的撰写。
注释:
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 本文所有小说引文均出自(美)霍桑《红字》.胡允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
:
[1] 付少华. 恶与善的选择——宗教对海斯特·白兰与潘金莲的人生结局的影响[J] .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3月 第三期.
[2] (英)加德纳(Gardner.H.)著.《宗教与文学》[M]. 沈弘,江先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
[3] [4] 陈冠商选编.《霍桑短篇小说》[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9月.
[5]《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 [J].基督教协会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