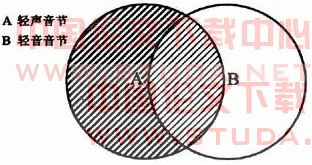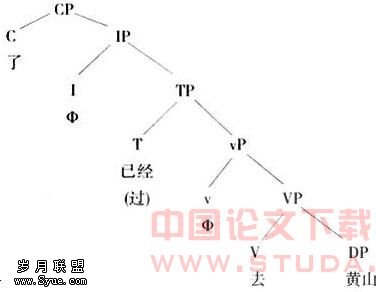殖民语境中鲁迅与马华文学
【摘 要 题】台港澳与海外华人文学
【正 文】
按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界定,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渊源于中国新文学,同属于语文系统,但在其中,又渐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界定从发生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中国五四新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了一种“形成性影响”。资料表明,也可以直接说是事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经典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当中,又以鲁迅为最:马来亚作家韩山元(章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文学家……”(注:韩山元:《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在马来亚广泛流传着一个小册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全是歌颂鲁迅如何伟大的;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被新马作家最大程度地摹仿、移植,单是《阿Q正传》就有上十个摹写本、改写本; 鲁迅的杂文在新马被极度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写作潮流;新马作家、学者方修、赵戎、高潮、方北方等论述文学问题处处以鲁迅为依据;鲁迅逝世后新马文化界对他的悼念,是新马追悼一位作家最隆重、最庄严、空前绝后的一次……问题是,为什么对马华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或说马华文学最多接受的,是鲁迅而不是别人,不是郭沫若、茅盾、巴金,不是在新马呆过的老舍、郁达夫……?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是: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从“放送者”考察,鲁迅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新文学中声名最大的,直接渊源于中国新文学的马华文学自是对这新文学的“奠基人”和声名卓著者有特别的关注;鲁迅作品本身的感召力又自有其向马华文坛的巨大辐射力。从“媒介者”考察,一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述,鲁迅“以左翼文人的领袖形象被移居新马的文化人用来宣扬与推展左派文学思潮。除了左派文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塑造鲁迅的英雄形象。”(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接着的问题是,也就是从“接受者”考察,为什么新马左派文人对鲁迅的更多“非文学性”的宣传会激起那么大的响应?王润华论述道:“共产党在新马殖民社会里,为了塑造一个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们采用中国的模式,要拿出一个文学家来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样这个英雄才能被英国殖民主义政府接受。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帜。”这段话启示我把问题放到殖民语境中去考察。面对殖民主义者,面对强权,马华文学自觉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而鲁迅恰恰被左派文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以文学来进行启蒙与救亡的民族英雄,从而进入新马文化人的“期待视野”。
一、殖民语境中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半殖民地”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或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主权所处的半独立的地位。部分的国家主权受制于他国。“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多次举行侵略战争,打败中国后,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国就“在形式上独立”,而等都严重“受制于”列强。生活在这种半殖民地处境中的青年鲁迅,高扬“我以我血荐轩辕”,其志不在文学,而在救国,转而以医学强国民之体,最后才落实到以文学变国民之心。也就是说,鲁迅自己对文学的选择,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生性中的文学禀赋,而是或主要是在于当时的他认定文艺更能改变人的精神,从而“立人”,从而进行民族自救。
鲁迅具体的创作是外国作品推动的,一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而鲁迅对外国作品的选择,不大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取舍,而注重挑选那些反映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人民苦难命运的作品来阅读和介绍,他曾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又在《杂忆》里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记得的人, 还有波兰复仇的诗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 fi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进入从文之初的鲁迅视野的、对鲁迅的创作构成“形成性影响”的外国前驱作家,并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果戈理,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乃至算不上经典的波兰的显克微支,菲律宾的黎萨尔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的反映,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争取独立富强的心声的抒发等等,正好满足了半殖民地鲁迅的情感诉求。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新马作家对鲁迅的接受上。1819年1月25日, 英国军官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后,新马便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在1958年独立,新加坡拖延到1965年才摆脱殖民统治。马华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殖民语境中生成。面对殖民统治,马华文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上的父亲”,来以文学作武器抵抗强权,这个文学上的又是精神意志上的“父亲”被塑造出来,这就是鲁迅。
许多论者都已指出,马华文学对鲁迅的接受,有一个“形象转变”的过程。20年代的新马文坛响应大陆的“革命文学”,批判鲁迅“落伍”。1930年,《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一位署名“陵”的作者写的《文艺的方向》,说道:“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注:陵:《文艺的方向》,《星洲日报·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又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册。)
然后转折出现了,1929年前后,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1930年“左联”成立,鲁迅成为领导人,于是他在新马的形象来了个大转变:不再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也不只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重要作家,而是一个左派的、反资产阶级的、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作家。这个“形象转变过程”即体现了马华文坛对鲁迅的选择更多地不是出于艺术的诉求,而是出于“革命”的诉求。拒绝与接受,批判与大肆宣传,都存在着对鲁迅的严重“误读”,都有过多的政治阐释。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对鲁迅的批判,是嫌这个文学与意志上的“父亲”不够有“革命”的力量;对鲁迅的推崇,是鲁迅在中国成了左翼领导人,是因为这个“父亲”成了强有力的“革命”的父亲。
移居新马的左派作家张天白(丘康)称鲁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与“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新加坡作家方修称颂鲁迅为“青年导师”、“新中国的圣人”,甚至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论证鲁迅就是“具有最高道德品质的人”;马来亚作家韩山元,著《鲁迅与马华新文艺》,宣称:“鲁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鲁迅的著作,充满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对于进行反殖反封建的马来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是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锐利思想武器。”……鲁迅就是这样被塑造成战士、巨人、导师、反殖反封的民族英雄进入新马。“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政治目标:推翻英殖民地。”这就是殖民语境中马华文学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突出思想政治功能而并不突出艺术功能,重政治的革命的身份和形象(民族英雄、战士)超过对文学身份和形象的看重。
二、殖民语境中的特定主题
可以说,殖民语境中的两个主题词是“启蒙”与“救亡”,两者并不构成对立。比如在鲁迅那里,就统一于他的“立人”思想。怎样“立人”?靠启蒙;“立人”后怎样?救亡,以立国。即是鲁迅所谓“救国之道,首在立人”。又统一于他的“遵命”而“呐喊”的文学观,呐喊是为唤醒沉睡的国民,承担启蒙的功能;呐喊以慰藉战斗的勇士,承担救亡的功能。
这种文艺观被殖民地新马文坛移植过来。在鲁迅还没有被新马“正式接受”之前,他的作品已传入南洋,他的文艺观已在那里得到认同与响应。1926年4月, 一家华文周刊《星光》杂志上,发表了南奎的文章《本刊今后的态度》,写道:“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注:南奎:《本刊今后的态度》,《星光》1926年4月。)大到观念,小到造句、用词,都明显有鲁迅《呐喊·自序》的影子。这样的文艺观对文学的主题表达以一定的规约,“惊醒沉睡的人们”,是为“启蒙”,所谓“沉睡者自沉睡”不过是愤激之词;“扫除黑暗,创造光明……忍不住呐喊”,在殖民语境里即是“救亡”。从而,文学的主题主要就不是抽象的爱与死、情与仇,甚至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惨淡的人生”和“改变”这人生;不是休闲甚至不是“雅致”,而是“呐喊”与“战斗”。
殖民地新马作家由于有着和鲁迅相同的情感和精神的诉求,在阅读和借鉴鲁迅作品时,首先就在主题和内容上获得共鸣,很快“认同”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对被奴役的处境的揭示,以及其所承担的启蒙、“立人”与“救国”。然后他们对之加以“消化变形”,力求以富于自己新马特色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南洋版的《阿Q正传》、吐虹的《“美是大”阿Q别传》、丁翼的《阿Q外传》、 林万菁的《阿Q正传》、李龙的再世阿Q……在对鲁迅的《阿Q 正传》加以“消化”后,又“变形”为殖民者统治下南洋国民的“精神胜利”的独特“行状”:一是拜金,“美是大”阿Q、再世阿Q等都千方百计地捞钱;二是逐色,丁翼笔下的阿Q“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是躺在布床上一面摸女人的大腿,一面吞其黑米”;三是忘祖,都反对学华语,不承认自己是人;四是崇洋,如“美是大”阿Q以“恶马劣根”(American)自居。鲁迅的《阿Q正传》已透露出殖民主义者与本地封建主合谋,构成对人民的掠夺——投靠洋人的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勾结,共同剥削雇农阿Q。马华文学的“阿Q”将这一点充分放大,暴露出殖民主义统治下, 新马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殖民文化打压华文、摧残华族文化,崇尚洋文化,从而导致拜金、忘祖、崇洋等南洋特质的“国民性”。正是经由类似的移植、变形、放大,马华文学呼应和延续着鲁迅的主题,在殖民语境中顽强书写着启蒙与救亡。
三、殖民语境中的偏好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时,表现出特定的文学思潮倾向,即特别青睐现实主义的思潮及作家。从1919年10月前后马华新文学运动兴起开始,文学工作者的兴趣就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方面,几乎全部模仿学习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以鲁迅的作品、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为主要对象。方修在《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中说:“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几十年来新马文学运动有时高涨,有时低沉,但现实主义精神却始终贯穿着战前新马的文学史,体现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未间断过。”然后他又进一步认为,只有鲁迅的作品是旧现实主义中最高一级的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只有鲁迅的作品达到这个高度。另一位作家,马来西亚的方北方,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论述马华文学时,也处处以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最高的典范与模式。这些事实这些论断说明,马华文学在对中国新文学的诸种思潮进行筛选后,主要选择的是现实主义,又主要是鲁迅的现实主义。
一种文学思潮只有在相对适宜的精神气氛中才能得到相对充分的移植和发展。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下的新马,没有适宜浪漫主义文学生长的精神气氛,因此一是迟至1925年7月15日(而现实主义早在1919 年即传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南风》上,才由一位来自中国的喜爱浪漫主义的移民作者“拓哥”第一次介绍五四新文学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二是浪漫主义文学在新马虽也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其势头还是远不如现实主义的创作。主义从、文化的高度对生活进行把握,它有意地将生活变形,与生活拉开距离,它在殖民地新马也没有适宜的土壤,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新马文化人无暇去对人生进行过多的抽象思辨,他们需要贴近现实的“地面”。于是,自觉承担反帝反殖、启蒙救亡的马华文学,与注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思潮相遇,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鲁迅相遇。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经典时,还表现出特定的体裁偏好,尤其体现在对鲁迅杂文的特别关注与推崇:“杂文,这种鲁迅所一手创造的文艺匕首,已被我们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即一般较有现实内容,较有思想骨力而又生动活泼的政论散文,也是多少采取了鲁迅杂文底批判精神和评判方式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理论批评二集》中,有许多短小精悍的理论批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鲁迅式底的杂文……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中,则更有不少杂文的基本内容是和鲁迅杂文一脉相承的……”与杂文被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写作潮流相对,写抒情感伤的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堕落,写闲适幽默的小品文遭到大骂。古月写杂文《关于徐志摩的死》,批判新月派的感伤文风;丘康作《关于批判幽默作风的说明》,将林语堂的文艺观斥为“堕落”。富于现实感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受到礼遇,感伤类闲适类的散文受到冷遇,这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个中缘由:“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注:《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443页。)在特定的殖民语境中对杂文的战斗性的强调,对闲适类小品的批判是必要的、合理的。前者更具有对现实的清醒度,更真切地触摸了存在之痛。
四、殖民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诉求
一个复杂的情况是,鲁迅是激进地反传统的,在文学资源和创作方面,他甚至主张“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17) 他的作品的欧化现象也确实很重,从结构到意象到造句。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之争”时,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是以民族传统的对立面出现而被一部分人竭力捍卫的。但另一方面,鲁迅的作品又极具民族性地方性,他笔下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七斤、华老栓乃至揭示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一“普遍”人性的阿Q,都打上鲜明的厚重的本土的烙印。阿Q,绝对是那个“未庄”的阿Q。鲁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江南风情,包含着深厚的越文化底蕴。即就艺术形式而言,鲁迅的讲究白描,在行动、对话在动态的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心理,包括《阿Q正传》对传统说书体的反讽式的模拟,都分明有“民族形式”的要素。以致我们在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时,常常以鲁迅为例。
鲁迅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存在,他在接受外国文学资源时其实同时又在抗拒,他对外国文学经典既吸收、借鉴,又误读、偏离,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而与西方经典抗衡;他以彻底“反传统”的面目出现,但半殖民地鲁迅又分明有着本能的民族文化自卫心理。他反的是传统的积弊,是礼教的“吃人”。在“反”的同时明明又有“树”,“破”时明明又有“立”。他树大禹、墨子等是“中国的脊梁”,在著名的《拿来主义》里极深入极理性地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拿来”,批判中分明有继承。
马华文坛是将鲁迅主要作为“反帝反殖的民族英雄”引进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树立鲁迅的偶像,是为实现其目的:推翻英殖民统治。马华人力图以民族主义为基础来抵抗殖民文化。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里,就是有着明确的民族性诉求,自觉追求作品的地方特色,着力营构一种“民族寓言”。
在半殖民地鲁迅的作品里,“未庄”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个缩影,《药》里上演了华、夏两家也即是华夏民族的深重悲剧,七斤的辫子风波是近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浓缩……深受鲁迅影响的殖民地马华文学,找到了它营构“民族寓言”的独特载体:橡胶树。橡胶树把华人移民及其他民族在马来半岛的生活遭遇呈现出来,把西方资本主义者与大英帝国通过海外移民、海盗式抢劫、奴隶贩卖的罪行揭示出来,把殖民地官员与商人进行压迫和资本输出的残忍勾当暴露出来。浪花的小说《生活的锁链》是建构“民族寓言”的代表性文本。在下着雨的、寒风刺骨的橡胶园,一个化学工程师兼督工的红毛人趁一位胶工的女儿来借钱为母亲治病时,将她奸污。阴森黑暗的胶园,呈现的是当时东南亚劳工的艰苦环境;少女任洋人发泄性欲,是华人劳工任人宰割的象征,是殖民主义者强奸土著的的缩影。作品内容本身即已显示出强烈的反帝反殖倾向。作品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寓言”的营构,又以其自觉的文学民族性诉求来反抗殖民主义的强势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