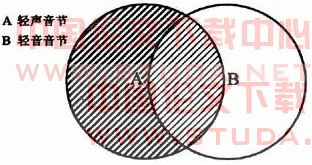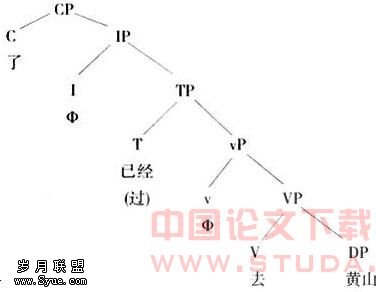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三国志》古写本残卷中值得注意的异文
【内容提要】跟传世的刻印本《三国志》比较,20世纪出土的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字数虽然不及传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拥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异文,有的异文至今鲜为人知。从文化史、学、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对此展开专题讨论与综合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 要 题】汉语言文字学
【关 键 词】《三国志》古写本/异文
【正 文】
近百年来,陆续出土的古文献使我们眼界大开,单是号称古写本《三国志》的残卷就已经多达六七种,即藏于我国新疆博物馆的《吴志·吴主传》《魏志·臧洪传》,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吴志·步骘传》,藏于日本的《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吴志·虞翻传》前篇及《吴志·韦曜华覈传》《蜀志·诸葛亮传》。
在上述古写本中,被推定为东晋时期的写本有《吴主传》《虞翻陆绩张温传》及《吴志·虞翻传》前篇,被推定为隋唐前后的写本有《臧洪传》与《韦曜华覈传》,被疑为近人伪造的写本有《步骘传》与《诸葛亮传》。据我们考察,落款为西晋元康八年“索綝敬书”的《蜀志·诸葛亮传》很可能是近人伪造的东西,但《步骘传》却不一定是赝品;退一步说,即使《步骘传》残卷出自近人的手笔,但抄写者必定有隋唐前后的《步骘传》写本作为样本。因此,本文所谓“古写本《三国志》残卷”,不包括《蜀志·诸葛亮传》。
据我们初步统计,传世本《三国志》有36万多字,六种古写本残卷共存3170字,古写本的字数虽然不及传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值得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
跟传世的宋、元、明、清刻印本及眼下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对照,古写本《三国志》残卷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异文。仅仅从校读古籍的角度看,不同的词、句及通假现象已有110多处;如果比较文字的形体,可发现异体字多达550个以上。
本文所讨论的异文,主要是如下三类:一是汉字演变史、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例如“凨”字(见第三段第5节第1例)。二是校勘学、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例如“潘阳”的“潘”字(见第一段第1节第3例)。三是训诂学、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例如《臧洪传》的“笱”字(见第二段第1例)。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其中一部分异文。之所以先讨论这些内容,是因为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都有助于推进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古文献研究及中古时代的俗字研究等工作。
一、关于《吴志·吴主传》残卷
这份晋人写本残卷1965年1月10日出土于新疆地区吐鲁番英沙古城南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共存40行,凡570余字,中间偶有残缺。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古写本第一行仅存“巫”字左侧,是“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的“巫”字的残余笔画;最后一行止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句的“高”字。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载《文物》1972年8期)在比较了传世本与古写本的内容之后,揭示了7则异文,并对其中5则发表了意见。
据我们调查,古写本跟传世本相比,除了出现异体字100多个以外,在校读古籍方面富有研究价值的异文实有10则。关于异体字,我们拟另文讨论,本文只就郭文提到的7则和我们发现的3则异文略述己见。
(一)郭文发表于30多年以前,现在看来,有不少地方需要进一步讨论,今依郭文次序论列于下。
(1)勉——俛
传世本“故遂俛仰从群臣议”的“俛”,古写本作“勉”。郭沫若认为,古写本作“勉”属于“误写”。
郭文断言“勉”为误字,恐怕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古写本的“勉”很可能是“俛”的通假字,它未必属于抄写的讹误。流传已久的古籍,其文本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一般说来,抄写或刻印时代越早的文本,其中的古字、俗字以及通假现象就越多。有迹象表明,在唐宋以前抄书人的笔下,“俛”与“勉”是一组通假字,例如《诗经·邶风·谷风》“黽勉”的“勉”,在唐李善《文选·文赋注》中引作“俛”,宋人所编的《太平御览》卷504也引作“俛”。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某些从“免”得声的字曾有通假关系。因此,传世本的宋(南宋)、元、明、清刻印本及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作“俛”,而晋代写本作“勉”,未必属于文献学上的校勘问题。从古音通假及古书形态不断演变的角度来看,古写本作“勉”而不作“俛”,正反映了魏晋时代的用字特点。
(2)“而”字的有无
古写本“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的“而”,不见于传世本。郭沫若说,传世本“无‘而’字,殆夺”。
郭文用“殆夺”二字评议传世本,等于向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进一步论证的要求。我们认为郭说可从,下面从两个方面略作论证。第一,上文出自东吴赵咨对魏帝曹丕称扬孙权的一段话:“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从文法角度看,古写本显然优于传世本。因为“获于禁而不害”“据三州而虎视于天下”两句排比,均用“而”字表示转折关系;传世本没有“而”,语义、语法、修辞上均有缺憾。第二,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时代最早传世本应推号称“咸平本”的《吴志》(实际上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从这个版本开始,直到最近40多年来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虽然都没有“而”字,但是,《太平御览》卷211的引文却有“而”字,足见北宋初期之人所见的文本还有不脱“而”字的,可与古写本互相印证。
附带说一下,赵幼文《三国志校笺》① 在“取荆州而兵不血刃”一句下面注释云:“《太平御览》卷463引‘州’下无‘而’字,考《文选》李注、《实录》《通鉴》、郝书,俱无‘而’字,应据删。”在这里,赵笺忽略了古写本有“而”这一事实,从而过早地得出了传世本“取荆州而兵不血刃”的“而”字属于衍文的结论。
(3)潘——鄱、番
传世本“鄱阳言黄龙见”的“鄱”,古写本作“潘”,郭沫若说,传世本“‘潘’作‘鄱’,殆误”。
郭文怀疑传世本的“鄱”属于误字,也值得讨论。在古代文献中,“潘”“鄱”“番”等字有同音通用的。例如《左传·定公六年》“潘子臣”的“潘”,《史记·吴太伯世家》引作“番”;《史记·陈涉世家》“鄱盗当阳君黥布”的“鄱”,《汉书·陈胜传》作“番”,唐颜师古的注释是:“番即番阳县也,其后番字改作鄱。”对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番陽令唐蒙”的“番”,唐张守节《史记正羲》的注音是:“番音婆”。从颜师古、张守节的解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唐宋以后习见的“鄱阳”,在先前的文献中通常写作“番阳”,有时写作“播阳”。按照古音假借的通例,当然也可以写作“潘阳”。这样看来,古写本作“潘阳”所反映的是晋代用字习惯,传世的宋元以下诸本作“鄱阳”是出自后世古籍整理工作者之手。唐人所编《群书治要·魏志》及宋刻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分豪不与”的“豪”,到了元、明、清刻印本中变成了“毫”,人们要么从历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古今字,要么从共时层面把“豪”与“毫”看成通假字,却没有人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说“豪”“毫”二字中必定有一个错字。古写本的“潘阳”到传世本里变成“鄱阳”,跟“豪”“毫”的演变属于同一类型。
跟郭沫若把《吴志·吴主传》的“鄱阳”看成“潘阳”的误文相反,陈乃乾把《吴志·吴主传》注文中的“潘阳”看成“鄱阳”误文。在陈乃乾校点的《吴志·吴主传》② 里,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中的“潘阳”,被校改为“鄱阳”,校改的依据是“从潘眉说”③。其实,清代学者潘眉只是说“潘阳当为鄱阳”,梁章钜也只是补充说:“吴时无潘阳县”。拿这种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说法作为校勘的依据,难免犯主观武断的错误。如今,1972年公布于世的古写本《吴志·吴主传》的“潘阳”赫然在目,跟《会稽典录》“潘阳”遥相呼应,说明近代人习知的“鄱阳(县)”在孙权时代写作“潘阳”。事情很清楚,潘、梁身在清代,不知有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陈乃乾在1959年完成的《三国志》校点本中采用潘、梁之说,也是因为没有看到古写本《吴志·吴主传》残卷。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古写本在文献校勘学等方面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
(4)“之际”的有无
古写本“君生于扰攘”,传世本作“君生于扰攘之际”,郭沫若说,传世本“下有‘之际’二字,较长”。
再好的古写本,也只能做到失误较少,绝不能保证没有任何失误。如果说,传世本《吴主传》有胜于古写本的地方,大约这一例是有可能通过论证得到承认的。
(5)“之”字的有无
古写本“埋而掘之,古人所耻”,传世本作“埋而掘之,古人所耻”。郭沫若只说传世本“‘古人’下有‘之’字”。只揭示异文,不发表意见,是存异待考的谨慎态度。
陈寿所著《三国志》以“高简”著称。经初步考察,我们认为古写本长于传世本。王沈《魏书》载公孙渊令官属上书给魏明帝有这么一段:“自先帝初兴,爰暨陛下,荣渊累叶,丰功懿德,策名褒扬,辩著廊庙,胜衣举履,诵咏明文,以为口实。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诸侯,犹慕著信,以隆霸业。”其中“埋而掘之,古人所耻”两句,显然是汉末流行的格言。这两句没有“之”字,跟古写本《吴主传》正可互相印证。传世本多一个“之”字,虽然无碍文义,毕竟跟陈寿行文求简的特点不合。此外,“古人所V”的句式,在《三国志》中多次出现,又如《魏志·袁绍传》载韩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又《蒋济传》载其答曹丕曰:“‘天子无戏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又《钟会传》载诏曰“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执,以成其美。”《吴志·华核传》载其上疏曰:“唇亡齿寒,古人所惧。”
(6)之——者
古写本“犹冀言之不信”的“之”,传世本作“者”。郭沫若对这组异文也没有发表意见。
从语法、语例两个方面考察,仍以古写本为优。第一,古写本的“言之不信”表示“所言不可信”,而传世本的“言者不信”则表示“发言之人不可信”,显然是前者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第二,“言之不信”也是当时的常用语,又如《魏志·蒋济传》注引《列异传》载孙阿事云:“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其中“言不信”三字,《太平广记》卷276《列异传·蒋济》引作“言之不信”,恰与古写本《吴志》之语相合。
(7)靡——麾、摩、
古写本“口陈指靡”的“靡”,传世本作“麾”。郭沫若说:“系抄本之误。”
郭文所谓“抄本”,指古写本。就我们考察,断言古写本的“靡”字是误文还为时过早。从“”“麾”“摩”“靡”的音形义的关联情况来看,“靡”与“麾”不见得没有通假关系。先看“”与“麾”的关系——“”字见《说文解字·手部》“,旌旗”,段玉裁指出:“许伪切,古音在十七部,俗作麾。”这就是说,“麾”跟“”是异体字。再看“麾”“摩”“靡”之间的关系——《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下麾”的“麾”,在《汉书·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中作“摩”,可见这两个字在距《三国志》成书时代并不遥远的古籍中有通假的先例。“靡”跟“摩”也是这样,例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下摩兰惠”的“摩”,在《文选·子虚赋》中作“靡”,可见汉魏六朝时二字可以通假。既然“靡”可以通“摩”,“摩”可以通“麾”,“麾”又同,而靡、麾、摩、四字又均从“麻”得声,那么,“靡”与“麾”很可能在魏晋时代具有通假关系。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靡”与“麾”通假的第二个例子,因而不能断言这两个字一定具有通假关系,但同样也不遽从郭文的意见。
(二)郭文没有提到的3则异文。
(8)传世本“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的“之”,不见于古写本。
上文有“之”无“之”均可通。古写本没有“之”,跟陈寿《三国志》行文求简的特点相合,比传世本更接近于陈寿原著的面貌。“破”字煞句(后面一般不加逗号或顿号),“斩”字紧跟,这种文句在传世本《三国志》并不罕见。例如《魏志·袁绍传》:“太祖救延,与良战,破斩良。”又《于禁传》:“復徙攻張繡於穰,禽吕布於下邳,别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蜀志·马超传》裴注引《典略》:“超后为司隶校尉督军从事,讨郭援,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破斩援首。”
(9)传世本“讨备之功,国朝仰成”的“成”,古写本作“诚”。
古写本作“诚”,是“成”的通假字。这类通假现象屡见于其他古籍,例如《战国策·赵策一》“恐其事不成”的“成”,汉墓出土的帛书作“诚”。《老子》二十二章“诚全而归之”的“诚”,景龙碑作“成”。
(10)传世本“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的“敕”字下面,古写本有“令”字。
“敕令”作为复音词,屡见于《三国志》,例如《魏志·公孙瓒传》载刘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又《武文世王公·中山恭王衮传》载曹衮“疾困,敕令官属曰:‘吾寡德忝宠……亟以时成东堂。’”又《牵招传》载魏文帝“敕令还击比能”。《蜀志·姜维传》:“寻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吴志·华覈传》:“晧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由此看来,古写本作“敕令”,比传世本更富有三国语词的特色。
二、关于《魏志·臧洪传》残卷
这份残卷字体为隶书,存21行,计370余字。异文12处,异体字共66个。首行起于“不蒙观过之贷”的“贷”,末行止于“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的“姻”。
据李遇春《吐鲁番出土〈三国志·魏书〉和佛经时代的初步研究》④ 一文介绍:1965年1月10日,一农民在吐鲁番安加勅克(Anjanlik)南郊附近的一座早已颓废的佛塔下层发现一个装着《三国志》残抄本二卷及其他古的陶罐。其中一卷是前面提到的《吴志·吴主传》残卷,另一卷就是1977年《新疆文物》⑤ 一书收录的《魏志·臧洪传》影印件,这份影印件虽然图象模糊,但图象下面的说明却十分醒目:它的抄写时代是“十六国”时期。跟李文同时发表的有关,还有吴金华《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⑥ 一文。此文根据《新疆历史文物》影印件上所能辨认的一部分内容进行研究,其中有关古写本的引述,有与原件不相吻合的地方。李文在引述“中华书局本”及古抄本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李文引述中华书局本时所出现的讹误主要是由《敦煌学辑刊》的印刷错误造成的,而征引“抄本”时所出现的问题也可能与印刷过程中的造字困难有一定关系。
本文拟说明两点:
(一)拿古写本影印件⑦ 跟宋刻本对比,除了李文揭示的异文12则,我们还发现异体字60多个。
(二)上述李文、吴文均有订补的必要,兹订补如下。
(1)畏君亲怀——畏威怀亲
传世本作“畏威怀亲”,古写本作“畏君亲怀”。吴文认为传世本的“畏威”的“威”是误文,应当根据古写本校改为“君”;“亲怀”二字误倒,应当根据传世本乙改为“怀亲”。
李文说:古写本“‘亲怀’二字旁加两点,以示颠倒”。
李文的根据,是古写本原件;吴文的根据,是古写本影印件。这样看来,古写本的原文应当是“畏君怀亲”,其中“君”字胜于传世本。吴文⑧ 关于“亲怀”二字误倒的内容应当删去。
(2)众——求
李文说,传世本“以诈求归”的“求”,古写本作“众”。
如果古写本确实作“以众求归”,那么,其中“众”字当属误抄。
(3)——兵、侯
李文说:传世本作“增兵讨仇”的“兵”,古写本作“侯”。
我们怀疑,古写本的原字未必是“侯”。从字形上推测,它很可能是“兵”字。中古时代,“兵”写作“”,是隶书中流行字形。例如古写本《吴主传》《虞翻陆绩张温传》中的“兵”字都写成“”。“兵”的这种字形,跟“侯”的隶体字颇为相似,例如《王基断碑》、魏《三体石经》残石中“侯”都写作“”,跟隶书“”接近。因此,从字形来看,在三国时代,“兵”的写法与“侯”的写法非常相似,极易相混。可惜我们所见的影印件不很清晰,这个问题只能存疑待考。
(4)泯——民
李文说,传世本“背弃国民”的“民”,古写本作“泯”。
我们揣测,古写本的原字应是“氓”。手写的隶体字“氓”“泯”二字很相似,这两个字的释读,只有文义才有可能区别开来。在古汉语中,“氓”跟“民”有时是同义词,例如《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毛传的解释是“氓,民也”。古写本作“氓”,后世刻印本作“民”,在文本上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用字特点。
(5)“心”字的有无
吴文说:古写本“用命心此城”的“心”,当为衍文。
李文说:古写本“心”旁加两点,以示除去。
既然古写本的“心”字旁边有删字符号(即“两点”),吴文关于“心”为衍文的内容应当删去。
(6)顶——顺
李文说:传世本“可谓顺矣”的“顺”,古写本作“顶”。
隶书“顺”“顶”二字字形相近,就像前面提到的“氓”“泯”一样。古写本的原字是不是“顶”,待核。
(7)笱——苟
李文说:传世本“苟区区于攘患”的“苟”,古写本作“笱”。
由于我们所见到的影印件图象不那么清晰,以前我们不知道古写本作“笱”。今知古写本作“笱”,我们对古写本的通假字多于后出刻印本这一特点有了更深的体会。“苟”与“笱”作为一组通假字,屡见于西汉以前的文献,例如传世本《战国策·魏策》“苟有利焉”、《燕策》“苟无死”的“苟”,在西汉墓出土的帛书里均作“笱”。由此生发出来的问题是:上古时代(东汉以前)抄本的这种通假现象,到了宋元刻印本中似乎已经消失了,那么,魏晋时代这组通假字是否存在?这是汉语史研究者关注的课题之一。在这里,《臧洪传》古写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古时代通假字的可靠资料。
三、关于《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
20世纪前期出土于新疆吐鲁番、日本上野淳一所藏《三国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晋写本残卷,共80行,存1090余字。跟传世本《三国志》对照,晋写本起自《虞翻传》“权于是大怒”的“怒”,止于《张温传》“臣自入远境”的“境”。跟宋刻本比较,共有异文45处,异体字120多个。
这是出土古写本中篇幅最长的残卷,也是古写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研究者最多的一种。然而,要充分发掘出这份残卷的文化意义和利用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仅就异文的研究而言,至少有六项工作要做。
(一)继续揭示尘封已久的异文。继白坚在日本杂志上首揭异文之后,张元济《校史随笔》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三国志校勘记》⑩ 曾经陆续介绍古写本异文43则,易培基《三国志补注》(11)、赵幼文《三国志校笺》也着意向读者介绍古写本异文,但是,至今仍有下面两则异文隐而不显。
(1)氾——汜
传世本“汜弟忠”的“汜”(音祀),古写本作“氾”(音泛)。虞氾,字世洪,名与字相应,都是水势洪大的意思。“氾”与“汜”音义不同,不可不辨。
(2)大末——太末
传世本“太末徐陵”的“太”,古写本作“大”。《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有“大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大’,音如‘闼’。”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惠栋曰:“‘太’当作‘大’,孟康音‘闼’。”孟康是三国时代的注家,他的注音说明了“大末”是三国时代的写法,而古写本作“大”不作“太”,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宋刻本等作“太”,系后人所改。
(二)有许多早先被揭示的异文,一直没有受到注意,我们应当一一研究。下举两例。
(1)成名——名盛
张元济早已揭示:传世本《虞翻传》的“旧齿名盛”,古写本作“旧齿成名”。但是,至今未见有关“名盛”与“成名”的比较研究。我们的粗浅看法是,第一,“成”跟“盛”是通假字,“成名”就是“盛名”,例如《荀子·非十二子》:“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俞樾说:“成与盛通……成名犹盛名也。”唐代杨倞在注《荀子·王霸》“以观其盛名者也”的时候指出:“盛读为成,观其成功也。”第二,旧说出自三国人王肃之手的《孔子家语·大婚》有云:“孔子对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其中“成名”表示已有美名的意思。虞翻品学兼优,当时又任职于朝廷,是东吴不可多得的宿儒君子,说他是“旧齿成名”,正是三国时代的语言。第三,古写本的“旧齿”与“成名”是两个偏正结构并列,而传世本作“旧齿名盛”则是主谓结构。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据此断言传世本的“名盛”是倒文,但也不能忽视古写本异文的存在。
(2)责怒——积怒
白坚早已揭示:传世本《虞翻传》“权积怒非一”的“积”,古写本作“责”。但“责”“积”之异,尚待研讨。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古写本较可取。第一,“责怒”是同义复词,犹言“谴责”“谴怒”。《原本玉篇残卷》云:“謮,侧革反。《苍颉篇》:‘謮,谪也。《广雅》:謮,怒也。謮让也。今并为责字。在贝部。’”汉刘向《列女传·张汤母》:“母数责怒,性不能悛改。”据此可知,“責怒”即“謮怒”。《虞翻传》说“权积怒非一”,既云“非一”,就不必再用“积”,所以,我们怀疑传世本的“积”可能是“謮”的讹字。第二,“责怒”又见《吴志·吴主权王夫人传》:“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又《朱然传》:“权深嘉绩,盛责怒融,融兄大将军恪贵重,故融得不废。”“责怒”前面用程度副词修饰。而“积怒”指忿怒蕴积于心,如《战国策·秦策》云:“先王积怒之日久。”用“日久”作补语,只论时间长短,不论次数多少,程度如何。从语词的用法看,古写本为优。
(三)有些异文的研究,虽然有了结论,但前人的结论还有重申或修正的必要。例如:
(1)囗十九——七十
传世本《虞翻传》“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的“年七十”三字,古写本作“囗十九”
关于古写本的“囗十九”,卢弼《三国志集解》先解释成“七十九”,接着批评古写本说:“果如所言,则在南二十九年矣。与上文在南十余年不合。不问而知其误矣。”蒋天枢也认古写本是“七十九”,但结论不同于卢弼;卢弼认为古写本不如传世本,而蒋氏不轻易怀疑古写本。
今细审古写本影印件,可以确认古写本作“囗十九”。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残缺字“囗”是“六”。这种假设能不能成立并不是本文要说的事,该不该进一步研究才是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
(2)臣自远境——臣自入远境
传世本“臣自入远境及即近郊”的“入”字,不见于古写本。中华书局校点本据古写本删去传世本的“入”,缺乏必要的论证。《册府元龟》卷658及卷664均有“入”,可见北宋人所见的抄本已经跟古写本不同。既然我们目前还不能排除古写本有脱字的可能,那就只能存异待考。
(四)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不少异文的研究成果未被利用,甚而出现误用现象。如所周知,中华书局校点本(12) 将这份残卷作为书影,并根据残卷校传世本改12处,其中11处在《校记》中简述了校勘的依据是“古写本”。可是,要正确地、充分地利用古写本,并非易事。下举二例。
(1)——充
这是由于不识古写本俗字而误校的例子。
传世本《张温传》“军事兴烦”的“兴”,中华书局校点本根据古写本校改成“凶”。事实上,古写本作“”,是“充”的俗字。
(2)“當閉反開,當開反閉”二句的次序
这是没有充分利用古写本的例子。
传世本“當閉反開,當開反閉”,白坚指出古写本作“當開反閉,當閉反開”。蒋天枢认为:“二句虽‘开’‘闭’二字先后使用之不同,所关甚重。缘上句言当前实况,下句则讥芳开门迎降吴人(关羽之死即由芳开门迎降)。翻之言应景而发,决无先讥刺而後言实况之理,自当以写本‘當開反閉,當閉反開’为是。但向来读史者于此不切实际之错误,甚少注意,益见书之不可不校也。”中华书局校点本至今已印刷多次,重印过程中往往在校点工作上作局部调整,但蒋氏的研究成果一直被出版者所忽略。
(五)古写本中有待研究的异体字很多,以往的学者未曾提及,为我们留下了极大的研究空间。下举二例。
(1)凨——風
“凨”字不见于《康熙字典》。这个字始见于近人李家瑞、刘复所编《宋元以来俗字谱》(13)。1932年国民政府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简化字表将“凨”列为“風”的简化字。李圃《异体字字典》(14) 附录的《胶东地区俗字表》提及“凨”为胶东地区的俗字。在晚近所编的《中文大辞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凨”字的出处均为《宋元以来俗字谱》。张书岩等所编《简化字溯源》(15) 说:“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中有‘風’的简化字‘凨’。”总而言之,近百年的学者一直认为“凨”是最早见于元代文献的俗字。
然而,古写本昭示我们,在早于元代一千多年的东晋时代,“凨”字就流行于世了。传世本《虞翻传》“故海内望风”及《张温传》中的“遐迩望风”的“风”,在晋写本里均作“凨”。
顺着古写本提供的线索去上下探索,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宋元以前“凨”字的源流:魏甘露元年的写本《譬喻经》、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北魏正光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