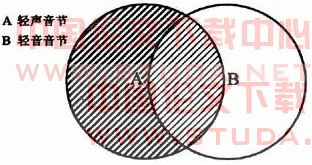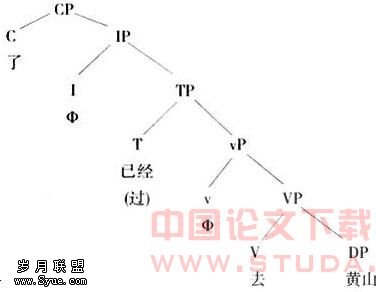中国古代剑侠小说的发展及文化特质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古代社会弥漫着浓烈的好剑之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剑崇拜心理。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剑”的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在诗歌里,剑作为文学意象被热情赞美;在小说中,剑衍生为神奇的“剑术”。唐代是剑侠小说的勃兴期,清代是剑侠小说的辉煌期。剑侠小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有着浓郁而深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关键词】 剑崇拜 剑术 剑侠小说
剑侠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其表现内容和手法都有独到之处,其间更浸透着中国民间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迄今为止,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未见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笔者不揣冒昧,搜检思索,形诸文字,对中国古代剑侠小说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剑”的崇拜和“剑术”的产生
剑,薄体而双刃,是古人随身佩带的兵器,轻便灵活,被誉为“百器之君”。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好剑之风。当时,著名的铸剑大师有薛烛、风胡子、欧冶子、干将、莫邪等人,而著名的剑器则有莫耶、鱼肠、吴鸿、扈稽、湛卢、钝钩、胜邪、巨阙、龙渊(也作龙泉)、泰阿(也作太阿)、工布等。贵族们更是把剑作为饰佩物和尚武精神的象征。藤国的国君自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①莒国的国君更是“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②。赵惠文王则养了三千多名“剑士”,令其“日夜相击于前”③。野史笔记中也记载了楚王为得利剑而杀人及越王勾践向民间求教“剑术”之事④。
先秦社会弥漫着的好剑之风,不但造就了一批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浓烈的对剑崇拜的文化氛围。先秦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严重的威胁。随着剑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人们对剑器产生了崇拜心理⑤。这种崇拜心理,在民间巫风及宗教鬼神观念地推动下,很地升级为一种超自然的幻想。东汉吴康《越绝书》卷一一记载,晋郑联军围楚三年,楚王甚忧。于是,楚王亲自登城,高举干将、太阿两把宝剑指挥作战,楚军士气大振。晋郑联军被击败,楚国之围遂解。楚王在胜利后问大臣风胡子:“夫剑,铁耳,故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的回答不但肯定了剑器精神的存在,而且认为“铁兵之神”(剑)与“大王之神”(人)是相通的⑥。这一传闻说明,在剑器的物质载体中凝聚了人的精神情感,剑器被神秘化、人格化了。
最能体现剑器的神秘化、人格化特征的,是有关铸剑的悲壮感人的神奇传说和剑器变形化龙的记载。《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云:
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鉄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莫邪曰:“先师亲烁身以成物,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翦爪投于炉中。使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龟文,阴作漫理。⑦
唐陆广微《吴地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云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于炉中,铁汁乃出。遂铸成雄雌二剑,取名干将、莫邪(人名剑名合一)。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自藏雌剑。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两处记叙略有不同,但都表现出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对剑的心理崇拜,体现出人剑合一、物我合一的古代中国人的哲理思维。剑分雌雄,成为以后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固定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典籍中,剑往往与龙互相化形,合为一体。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颛顼高阳氏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克伐。未用之时,常在匣中,如龙虎之吟。”⑧是书卷五“前汉上”记叙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将所佩斩蛇剑藏于武库,库中剑气如云,直冲户外,“状如龙蛇”⑨。雷次宗《豫章记》亦载宝剑化龙之事。云有二宝剑深藏地下,紫气充斥牛斗之间。丰城县令雷孔章掘出,自留一剑,另一剑赠张华。张华死后,其剑飞入襄城水中,另一剑也从孔章腰中一跃入水,化为二龙。《晋书·张华传》在此基础上演绎增饰。称二剑名为龙泉、太阿,入水后,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潘萦有文章,没者惧而返。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⑩。
龙,是我们炎黄子孙普遍崇拜的一种图腾,对龙的崇拜象征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力和超能力的向往,以及要求了解自然、掌握自然、征服自然、融汇自然的美好愿望。龙剑合一表明,在对剑的崇拜心理中积淀着我们祖先对神的崇拜、对“力”的追求和赞美。
古人对剑的喜爱与崇拜心理,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剑的神话传说,使剑成为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也使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涉及“剑”的文学体裁主要有两类,一是诗歌,一是小说。在诗歌中,剑被文人当作一种文学意象,诗人借此表达情怀,抒发感慨。如东晋鲍照《赠古人马子乔》诗:
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烟雨交将夕,从此忽分形。
雌沉吴江水,雄飞入楚城。吴江深无底,楚关有崇扃。
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神物终不隔,千祀倘还并。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中第十六首也吟咏相同的宝剑典故:
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
一去别金匣,飞沉失相从。风胡殁已久,所以潜其锋。
吴水深万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
鲍照、李白的这两首咏宝剑诗,都以西晋张华、雷焕观剑气得雌雄双剑,各佩一把,而最终双剑入水化双龙的传闻为题材,但两首诗所表达的情怀是有差别的。鲍诗是为古人送别而作,故借雌雄双剑的分而复合表达对友人的思念和再次相逢的愿望。李诗则引出古代相剑名师风胡子,感叹人间知己难遇。清人王琦评论这两首诗道:鲍诗为古人而赠别,其居要处在“神物”一联;李诗感知己之不存,其警策处在“风胡”二语。辞调虽近,意旨自别(11)。
大量吟诵宝剑的诗歌都将剑视为有灵性的神兵利器,满怀深情地予以赞美,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傲视群伦的豪迈气势。欧阳修《宝剑》诗:“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突出了宝剑作为神物所具有的镇妖驱邪、诛奸除佞的正义之气,提出了宝剑的伦理实用价值。先于欧阳修的贾岛《剑客》一诗则写出了另一种境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在这首朴素自然、清新爽健、毫无雕琢、率真奇迈的咏剑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和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
在诗歌创作中,剑的描写大都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或表现出诗人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抨击,或表达了诗人对功名进取的追求,或洋溢着诗人的豪侠气概。而在小说创作中,“剑术”描写成为格外引人瞩目的内容。这里所说的“剑术”,不是武术中的剑术套路,而是古代小说中一种特定的常见的文学表现内容。古代小说里描写的"剑术"融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侠士的正义之气、佛教的神通和道教的法术,变幻无穷,神鬼莫测,威力无比。“剑术”的运用主要靠剑。剑术练成之后,剑可长可短,随意变化。剑侠平时或将剑纳入口中,或藏入指甲里,或置入袖子里,或变成小丸子随身携带,用时只要张口一吐,或伸手一指,或随手一抛,即可放出一道剑光,杀向敌人。剑光闪过,剑既失去踪迹,敌人已身首异处。
在“剑术”描写中,剑是有灵气、有意识的兵器。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侠女》一篇,写侠女用“剑术”诛杀轻佻无礼的狐精。侠女将短剑向空中一掷,狐精即死于非命,可见短剑具有识别敌我和寻找目标的能力。〈〈聂小倩〉〉篇写剑客燕赤霞将短剑置入箱箧内,半夜,夜叉来袭,“忽有物裂箧而出,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棂,焱然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12)”剑器不需主人驱使,自出自入,重创夜叉于瞬间。即便盛剑的革囊也能令鬼物心惊胆战,自行将鬼物抓住,化为清水。
古代小说中“剑术”的形成既有上述剑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因素。最早对“剑术”予以文字描述的是庄周。《庄子·说剑》篇中描述了战国时期的击剑之风气,并具体细微地阐述了运剑的法门。汉代赵晔《吴越春秋》卷五也描述了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女子的剑术之道。两书阐述的剑术理论异曲同工,都极为深奥而又充满辩证法的因素。此类“剑论”对后世剑侠小说创作中神奇剑术的形成,无疑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佛家密宗的修行剑法的法门,道教有关“炼剑”之术的记载,都对古代小说中“剑术”的描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如果说在诗歌中,剑是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被诗人热情赞美和反复歌颂的话,那么在小说中,剑就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让小说家们浮想联翩、心动不已,而且将它与民间自古以来就为广大民众所向往的游侠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剑术”描写的具体化、形象化和类型化,标志着剑侠小说的成熟。民间尊崇剑术的文化心理和民众要求公平正义、斩奸除恶的美好愿望,在“剑术”的描述中被成功地融会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武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剑侠小说的与主题
剑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分支,奇幻的“剑术”与传统的游侠精神是剑侠小说的两大支撑点,从这两大支撑点中,衍生出许许多多的炼剑修行、镇妖诛邪、斩奸除佞、匡扶正义的人物形象和传奇故事。
“剑侠”一词,北宋时期已有记载。苏东坡在《渔樵闲话录》中就曾对唐传奇中的女剑侠发出感慨:“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质,而能持刀以决凶人之首,非以有神术所资,恶能是哉!(13)”宋洪迈《夷坚志补》卷一四“郭轮观灯”篇中也有“剑侠”称谓出现。在此之前,虽已有剑侠小说风行于世,但时人尚未以“剑侠”名之。至明代始有人在《太平广记》“豪侠”类的基础上辑唐宋剑侠小说精品编成《剑侠传》一书,“剑侠小说”遂成为此类小说的固定称谓(14)。
唐代以前,未有成熟之剑侠小说问世,但有些作品可看作剑侠小说的雏形。《搜神记·三王墓》是比较重要的作品。这篇小说以铸剑传说为题材,突出宣扬了干将之子赤比的不屈不挠的复仇与反抗精神。小说将复仇与反抗暴政联系起来,塑造了一位自掌正义、为民伸冤的侠客形象。这篇小说有剑有侠,剑与侠都是不可或缺的情节要素,推动了后世的剑侠小说创作。受时代风气之影响,魏晋小说情节怪诞,侠客虽以法力行侠人间,但此时“剑术”未成。
唐代是剑侠小说的勃兴时期。“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水深火热。此时佛道二教十分流行,人们对宗教深信不疑。加上叙事文体的发展完善,传奇小说的日臻成熟,剑侠小说的大量涌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唐代剑侠小说约有数十篇,其中《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崔慎思妾》、《贾人妻》、《义侠》、《僧侠》、《兰陵老人》、《京西店老人》等篇都是极具影响的作品。《虬髯客传》叙述“风尘三侠”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之间的一段浪漫豪迈的传奇故事。三位主角形象生动,性格丰满,英姿勃勃,在胆识兼备、豪情四溢、侠义雄心的共同性格基础上,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个性,向人们打开了各自不同的心灵发展的画卷。尤其是江湖异人虬髯客,似飞将军从天而降,挟狂风迅雷而来,使人惊悸,又化明月清风而去,令人神往。整篇小说结构严谨,情节逐次展开,文笔虎虎有生气,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聂隐娘》与《红线》都是描写剑侠依凭剑术为主子效力,其中《聂隐娘》更是情节曲折怪诞,文字幽玄奇诡,或学剑于深山,或杀人于闹市,或藏剑于脑后,或隐身于人体,无形灭影,行踪难测,其隐身、变化、飞行及比剑斗法的巧妙构思,为剑侠小说的发展踏出了通途。书中人物“妙手空空儿”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飘然远逝,“自来武侠小说中,从未有过如此骄傲而飘逸的人物”(15)。《崔慎思妾》、《贾人妻》均写女侠隐身伺机复仇,篇中女侠忍辱负重,行为果敢,心态怪异,来去如风,成为复仇女侠的固定叙事模式。唐代剑侠小说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优异,在中国剑侠小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剑侠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模式、叙事手法和“剑术”演示,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依据。
宋元人创作的剑侠小说偏于对唐人小说的模仿,缺乏创新,在情节上不如前人曲折、生动,文笔没有唐人的气势,人物形象更是远不及唐人小说有神采,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宋元剑侠小说之“剑术”描写,侧重道教法术,如咒语、画符、托梦、隐形之类,与唐代剑侠小说有所不同。再有,宋元剑侠小说内容往往涉及国土沦陷、流浪思乡、亡国之恨。此种差别当与宋元时代道教广为流行以及异族入侵,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现实有关。
明代是剑侠小说创作的低潮,但有两篇小说对剑侠小说的关系重大。一是钱希言所著文言小说集《狯园》中的《青丘子》。小说叙丹溪生王生,误入深山,巧遇七世祖先王重阳。经王重阳指点,王生入武当山拜剑仙青丘子为师,修炼剑术之事。小说首分神仙剑仙之别,认为剑仙骨骼资质不及神仙,“因缘尚隔一层”,为后世剑侠小说区分剑仙、剑侠等级开了先例。本篇小说最早提及王重阳及全真教,又详述道教炼剑之术,虽是小说家言,却为以后的剑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二是话本小说《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这篇小说借十一娘之口,讲述了剑侠的发展历程以及如何运用剑术和剑侠必须遵守的戒律。它具体了明代以前剑侠小说的内容,正式提出了剑侠的戒律和剑术运用的法则,首次将是非善恶、忠奸斗争纳入小说评判中,对后世剑侠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晚清的《七剑十三侠》,民国年间的《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其作品的立意皆源于此。
清代是剑侠小说创作的繁荣时期。此时不但涌现出大量的文言短篇剑侠小说,还出现了《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等长篇白话剑侠小说,很多著名的文人如王士禛、蒲松龄、纪昀、袁枚、沈起凤等都加入了作者的行列。尤其到了晚清,社会激荡,民生多艰,这类小说更是充斥坊间,广为流传。在小说内容上,这一时期的剑侠小说都自觉地将善恶、忠奸的斗争作为小说的重要情节,剑侠凭借神术入世行侠,诛佞锄奸,造福人类。小说作者想象力丰富,剑术描写神奇诡异,匪夷所思:
只见凌云生、御风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自全生一起吐剑,九道白光望空而下。余半仙连连吹气,三枝剑又化出九枝剑来,共是十二枝剑,抵住十二道白光,空中交斗。忽如群龙戏海,忽如众虎争锋,忽如一阵苍鹰击于殿上,忽如两山猛兽奔向岩前(16)。
作者纵奇思、发妙想,使这类剑术描写既形象生动,又绚丽多彩,光怪陆离,曼妙无方,成为小说中最具传神和意境的情节。清代剑侠小说不但剑术描写神奇,而且炼剑的过程与运剑的方法往往与儒释道的传统观念互相融合,儒家的经世致用、佛教的神通、道教的法术和民间对剑的崇拜心理汇合,一起构成神奇剑术的理论依据。如此修练出来的剑术,既具有儒家的伦理道德倾向,又有着佛道救人济物、镇妖除邪的宗教救世精神。清代剑侠小说上承唐代剑侠小说的余绪,下开民国剑侠小说的先河,承上启下,影响深远。
自唐至清,古代剑侠小说逐步发展、壮大、成熟、完善,作品主题与情节模式也基本定型。炼剑学艺和剑术行侠是剑侠小说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又源自中国民间文化心理的两个支撑点——剑崇拜与游侠精神。围绕这两大主题所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曲折离奇、多姿多彩的故事情节,都是中国民间文化心理在文学中的集中表现。两大主题紧密结合,互为因果,炼剑是为了行侠,行侠就必须炼剑,两者不能分离,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剑侠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明清以后,中国主流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儒、释、道的观念)逐渐渗透到文学作品中,并与中国民间的传统文化精神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制约着中国剑侠小说的发展走向。
三 剑侠小说的文化特质
中国剑侠小说是一种带有理想和奇幻色彩的大众通俗文学,是从中国民间社会的土壤中绽放出来的奇葩,在其文本中有着浓郁而深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色调。本文从“天人合一”思想、隐逸文化、伦理道德观三个方面来谈剑侠小说的文化特质。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中最根本的命题。在儒家、道家等中国主流文化的哲学体系中,“天人合一”观被反复强调。《周易·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7)”《中庸》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18)《孟子·尽心上》亦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19)。”老子在《道德经》上篇第二十五章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1)到了汉代,董仲舒更将日月山川等自然界与人的身体搭配,提出所谓的“天人感应”说。直至宋明,历代哲学家都对“天人合一”的命题进行过论述。
“天人合一”的思想核心,是指人与界达到和谐一致,这在传统中被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剑侠小说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基本精神给予具象化、形象化的生动描述,尤其是在剑术的修炼过程中将其精神内涵予以充分展示。
在剑侠小说中,剑术传承于天,天命是不可违的。即使是身怀绝技的剑侠,也须依天命而行,替天行道,而不能任意胡为。唐袁郊《甘泽谣·红线》篇中红线依持神奇莫测的剑术,一夜之间平息可能发生的战乱。然而面对薛嵩的挽留,她却说:“事关来世,安可予谋?”(22)表明不可与天命对抗。元伊世珍《琅嬛记·玄观手抄》叙赵主父凭借剑术入秦宫行刺秦王,却因秦之运数未绝,只能依天命而放弃。龙辅《女红余志·侠妪》写一老妪用神术救一对母女于盗乱之中,盗乱平息后,老妪运慧剑斩盗首。当人问及为什么不早除掉盗贼,老妪答道:“虽系盗乱,亦天数。然吾小术耳,何敢违天?今天命吾斩,则斩耳。”(23)《初刻拍案惊奇》“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一篇中也借韦十一娘之一番宏论,说明剑侠运用剑术乃是替天行道,代天罚诛,“纵有剑术,岂可轻施”(24)!而滥施剑术者,必遭天谴。在“天命不可违”观念影响下,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当然有着君权神授甚至荒诞、迷信之类的消极落后思想,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古代小说家试图解释剑术行侠与天道同体一致的努力,感受到“天人合一”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巨大的支配力量。
小说中精彩纷呈的剑术描写更为形象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蕴。在小说中,凡剑侠炼剑或练功一定是在深山大泽之中。这里远离尘嚣,回归自然,人心澄静,不受外界干扰,人与自然容易沟通,达到和谐一致。《七剑十三侠》里海鸥子说:“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练气,采取五金之精,练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方才有用。”(25)明钱希言《狯园·青丘子》写青丘子铸剑,“悬于绝壁之下,以飞瀑溅激其上,日月之光华烛之,历经旬朔,剑质始柔”(26)。剑侠炼剑,摄日月之精华,采自然之飞瀑,自然与人力合为铸之,汇融于一剑之中。剑侠之剑术造诣,有高低之别,唐裴铏《传奇·聂隐娘》中聂隐娘曾说:“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27)这种剑术境界,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化而为一,无处不在,却又遍寻不得的“天人合一”的人生意境。
剑侠游戏人间,拯救苍生,轰轰烈烈,但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归隐。隐逸文化深深地制约着剑侠小说的创作。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它与中国的文人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和道家,隐逸文化观各不相同。儒家主张立身处世因势而异,隐现变通。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8)并以赞赏的口吻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9)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0)儒家的隐逸是与环境、理想抱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道家则不同。道家的隐逸是要挣脱一切羁绊,放任个体生命,从而达到一种永恒的绝对的精神自由,也就是庄子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这两种隐逸文化观都对剑侠小说产生影响。
与儒家一样,小说中的剑侠也是或隐或现,不同的是,剑侠是“天下无道则见,有道则隐”(31)。《七剑十三侠》书前“小引”云:“所谓剑仙大侠,似乎都是在世乱之时才出现人间,其实这也是必然之理!因为盛治之时,文教昌明,民心耻格,事实上也不须有剑侠的白刃;到了纲常废弛,道义沦亡时,奸邪当道,强梁横行;居上位的只管淫侈骄恣,在下位的也只管阿谀囊括,土豪劣绅棍徒恶霸辈便益发肆行无忌!良善的人们只能遭摧残,被冤抑,受压迫,忍哀怨,于是一般剑侠便要来代天伸诛了。”(32)剑侠的理想抱负虽与儒家大致相同,但行为处世有别,隐现的时机当然也就不同了。尽管剑侠依持利剑,纵横人间,神出鬼没,震绝人寰,但最终要“事了拂衣去,不留身与名”,归隐才是剑侠的完满结局。这种隐逸自然与道家思想有关,它既是对现实社会深刻反思的结果——功成身退、全身远祸;又是对宇宙本源和生命本质的探求——追求永恒、羽化登仙。在熙熙攘攘的尘嚣之外,在清静岑寂的山林之中,与清风明月做伴,与白云山泉为伍,气定神闲,悠然自得。由“侠”而“隐”,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修养成仙,更是中国文人的梦幻,在这种人生模式与人生境界中,道家乃至道教的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剑侠小说是社会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宣泄情感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有着中华大地泥土的芳香,有着中华民族的特有气质和情感,也带有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色彩。具备“剑术”本领的剑侠,必须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七剑十三侠》里的飞云子曰:“谈道术者,第一要戒淫。”(33)玄贞子云:“古来剑仙侠客,哪一个不从忠孝节义四字上做起?”(34)可见,剑侠必须是一位心无杂念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正人君子。我们在剑侠小说中经常看到剑侠艺成出山,其师必然再三叮咛:不得持“剑术”为非作歹,否则必遭天谴。剑侠必须有严格的自律精神,清心寡欲,一心修道,“就是报仇,也论曲直。若曲在我,也是不敢用术报得的。”(35)如以“剑术”假公济私,必遭报应。况且,如以“剑术”行不义之事,“剑术”也会失去应有的灵验。所以,明清以后剑侠小说写复仇往往将个体行为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突出忠奸斗争、善恶伦理以及扶危济困的“利他”复仇,伦理道德色彩更浓。在复仇中,“剑术”的使用也更加谨慎,严禁滥杀。
综上所述,剑侠小说源自中华民族的剑崇拜心理和传统的游侠精神。唐代是剑侠小说的勃兴期,清代是剑侠小说的辉煌期。剑侠小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其文本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芬芳。
①(19)(30)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第114页,第301页,第304页。
②《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1500页。
③(21)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第270页,第19页。
④参见《搜神记》、《吴越春秋》。
⑤关于先秦时期的好剑之风及剑崇拜心理,参见拙文《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的阐释》,载《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2期;《古代武侠小说对“剑术”的表现及其文化意蕴》,载《南开学报》(社会版)2006年第6期。
⑥《二十五别史》第6册《越绝书》卷一一,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第59页。
⑦《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4月版,第59页。
⑧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16页,第110页。
⑩《二十五史》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368页。
(11)转引自《李白全集》“古风五十九首注”,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
(12)《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
(13)《苏轼文集·佚文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16页
(14)参见拙著《中国武侠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04—106页。
(15)金庸:《侠客行》附录,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663页。
(16)(25)(32)(33)(34)《七剑十三侠》,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第4页,第299页,第326页。
(17)高奇生注译《周易》,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8)《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7页。
(20)《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页。
(22)(27)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7页,第156页。
(23)(31)转引自刘荫柏《中国武侠小说史》,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龙辅《女红余志》),第213页(邹之麟《女侠传》卷首“剑侠”)。
(24)(25)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第72页。
(26)《剑侠图传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28)(2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第163页。
【原载】 《文艺研究》 2007年第12期
下一篇: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