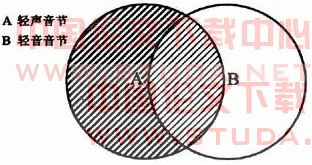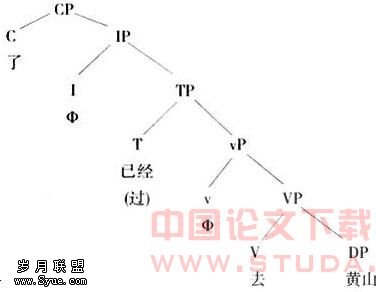清末民初日文中译与转贩西学问题研究
翻译作为文化植入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整个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以甲午中日战争为分界线,可以划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甲午中日战争前,西学传播以西书中译为主;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比较注重日文中译,并逐渐形成西学传播以日文中译为主的局面。本文拟就清末民初西学传播与日文中译的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日文中译是西学传播的一种捷径
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利用西书中译传播西学,没有使清政府走上“中兴”之路。对前期西学传播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和检讨,以利于更好地使西学传播为我所用,成为甲午战后知识界关注的一个新问题。这时,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识到,在甲午战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救亡图存、使国家强大,就必须选择符合新兴资产阶级斗争需要的新式西学加以汲取。于是,知识界以甲午战争前西学传播的失败为教训,借鉴近代日本成功汲取西学而强大的经验,确定了未来西学传播要学习和借鉴东邻日本传播西学的经验和成果、从日本转贩西学的新的模式。
日本从学习“兰学”开始,对西学进行了学习和模仿。早期在日本传播的近代西学被称为“兰学”。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弛禁”。此前,荷兰是和日本惟一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西方文明的信息是由荷兰人传播而来的,所以把西洋学问一般称之为“兰学”。1774年,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被译成日文,标志着“兰学”在日本的形成。随着时代的,兰学家们对西学的认识和传播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明治时代,以横井小楠、桥本佐内为代表的洋学家们,在思想上主张“以夷之术防夷”、“东洋道德西洋艺”,在传播西学方面注重翻译技艺方面的西书。至19世纪20-30年代,以家西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由平等的思想原则。在此思想原则的影响下,近代西学的传播开始注重适应日本国情和时务的时政方面西书,成功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近代、社会科学,甚至连西方的生活文化,都成功地服务于自己的近代化建设需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化经营,日本终于成为亚洲强国,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胜了腐败的清政府。
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对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心理上震动最大。早在戊戌维新前夕,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的这一思想群体已经明确意识到并提出了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的经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在当时的条件下把目光转向日本也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对西文比较陌生,要人人都学习西文是不可能的,而如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西书、西文在19世纪末通行世界的说法也是不切实际的。而要等到中国人学好西文之后,再去翻译西书接受西学,又是与急于为变法维新服务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宗旨不相适应的。时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一种传播西学的捷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翻译的西学书籍多不是切合时务的图书,康有为论述上海制造局及天津、福建、广州所译西书,“其途至难,成书至少;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糜巨款而已”[2]。与日本进行对比,日本原来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它能够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在于它早变法、早一步学习西方政治、工艺、文学等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亟变法,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速倍过于日本也”[2]。因此,以日本学习的态度,借鉴它汲取西学翻译西书的成功之处,提倡日文中译,不仅可使落后的中国免去直接接触西文书籍的繁琐,节省了对西书筛选的手续,而且还可加快传播西学的速度。就连清政府官僚张之洞也在其《劝学篇》中指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劝学篇》中亦大力提倡东书之益:“大率商贾市井,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可见,甲午中日战争后不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清政府官僚,都认识到取经东洋、翻译西书是一种省工省时省费的捷径。
二、日文中译的便利条件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凭着便利的地理条件,历史上就有频繁的文化交流。近代取经东洋、转贩西学,也同样有诸多有利的条件。
从语言学习方面来看,中日同文同种,为日文中译提供了良好的语言条件。从日本语发展历史本身来考察,在明治、大正年间,日本语当中用汉字比现代日本语要多。在一些近代中日关系中,甚至有的书本有整段的汉语原文。如康有为称“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2],似不为过。既然同文,那么中国人学习日文就比较容易。据说,梁启超初次去日本是利用途中时间修通日语,缘于此有人还创立了“一盏灯日语”。其实这是被夸张的结果。中日语虽同文,但是作为一门外语要学好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梁启超也认为:学习日本文,数月可以小成。但是,“东语虽较易于西语,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岁余之功细之不能。”就是以简便速成之法,仅仅以求其书,“则慧者一旬,鲁者二月”。[3](P93)然而对于日文中译而言,则不仅仅要能读其书,而且要能通其学。梁启超认为治东学者,如果中国文学已经深通,则有一年之功,就可以尽读日本书而没有隔阂。比较日文和西文,欲读西方政治、、等书并且一一诠解,最快也得五、六年的功夫。如果从智力未开的幼童算起,“循小学校一定之学级以上进,则尤非十余年不可”。[3](P93)语言学习时间长,翻译西学书籍的速度就慢。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4]可见他们所主张的学东文译日文书,相对于学西文译西书传播西学来讲,重要的一点在于追求一个“速”字,这也是日文中译的特点之一。
提倡日文中译,重要的莫过于要有翻译人才。为解决中国翻译人才缺乏的矛盾,必须重视对翻译人才的培养。国内培养和赴日留学是其两个基本途径。
在国内培养翻译人才问题上,康有为思想比较敏锐,他主张在中国设立译书局,妙选通人主持,收罗培养有志之士。但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人的功名思想比较重,怎样利用这一点呢?康有为指出:“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仅以策论取之,亦奚益哉。臣愚请下令,士人能译日本书者,皆大赉之,若童生译日本书一种、五万字以上者,若视其学论通者,给附生。附生增生译日本书三万字以上试论通,皆给廪生。廪生则给贡生。凡诸生译日本书过十万字以上者,试其学论通者,给举人。举人给进士。进士给翰林。庶官皆进一秩。应译之书,月由京师译书局分科布告书目,以省重复。”虽然鼓励激发科举之士学习日文、翻译日本书,是康有为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思维模式,但是对培养翻译人才来讲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则“以吾国百万之童生、二十万之诸生、一万之举人、数千之散僚,必皆竭力从事于译日本书矣。若此,则不费国帑,而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2]结果必然是日本化的西学尽为我国所掌握。戊戌维新前后,日本人利用中国人倾心西学、学习日文的急迫心情,先后在中国开办了多所学校,如1898年的杭州日文学堂、1899年的天津东文学堂、1901年的北京东文学社、1900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1900年5月成立南京同文书院,同年8月迁往上海并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开设其他课程。这些学校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日语人才。
在国内大量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又广泛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赴日,开始了近代中国对日留学的历史。中国近代日本留学史在1901年至1906年间形成一个高潮,五、六年间留日学生达一万多人。[5]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为这一时期日文中译书籍的出版奠定了人才基础。如:戢翼晕、杨荫杭、杨廷栋、吴振麟、章宗祥、周祖培、章太炎等人都是通过游学日本而成为优秀的翻译家。戢翼晕译巳小二郎的《万国公法比较》、杨荫杭翻译的《物竞论》、章太炎翻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译本在当时中国社会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书籍的翻译还不能代表完全接受了西学,特别是“物质之学”是不可能靠译书所掌握的。考察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人的人才观,几乎都主张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都认为日本距中国近,路近费省文同,因而鼓励中国人自费留学,国家也可以相应减少官费数目。政府派遣留学生应多选择欧美各国,原因是欧美昌盛在于物质之学,不是可以译书得到的。可见,当时鼓励赴日留学旨在培养日文中译的速成人才和通过日文翻译西学,这也是对日留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日文中译转贩西学的成就
传统西学以语言文字为门径,但不以语言文字为极功。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中译西书中,1890年出版、王韬译辑的《(重订)法国志略》和林廷玉翻译日本井上圆了著《欧美各国政教日记》,为国内最早通过日文著作传播西学的两本汉文译作。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学界以日文为捷径,日文中译提倡于前,汉译日书出版于后,广泛传播西学。在甲午中日战争至戊戌变法之间的四、五年时间里,通过提倡学习日文、日文中译思想的酝酿,日文中译作品进入初步出版发行时期。1895年上海读有用书斋翻印出版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这是甲午战争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日文中译作品。1896年,湖南新学书局又翻译出版了冈千仞和河野通之的《翻译米利坚志》。在戊戌变法时期及20世纪初,日文新书新作被大量出版发行。诸宗元、顾燮光1904年《译书经眼录序例》中描写道:“日本之译本,遂充斥于市,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寝成风尚。”[6](P95)日文中译新书新作“充斥于市”,人人争相购而读之,使西学传播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和西文中译相比,为什么日文中译作品能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日文中译新作其内容比较符合时代潮流、符合读者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急切需要传播西学以唤起民智。至于西学之精华,“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日文即可博览西文书籍”[7](P53)。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认识到,通过翻译日文来传播西学完全能够满足社会对西学的需求。梁启超等人“联合同志”,于1897年创设上海大同译书局,作为维新派的翻译机构,主要翻译日文作品,不久就出版了《俄土战纪》、《意大利兴国侠士传》、《瑞士变政记》等十多部译作。1897年,梁启超还设立了译书公会,同年就翻译有十多册西学新书。作为维新派文化出版事业机构之一的广智书局,在其创立一年内(1901年)所译印的书籍主要有:
类别 原作者 译书
(日)市岛谦洁 政治原论
(日)小野梓 国宪泛论
(日)松平康国 英国宪法史
政治类 (日)峙地六三郎 东西将来大势论
(日)伯伦知理 国家学纲要
(日)灵绶 19世纪世界之政治
(日)有贺长雄 社会进化论
社会类 (日)岸本能武太 群学
财政类 (日)小林丑三郎 欧洲财政史
(日)铃木喜一郎 法学通论
类 (日)小河滋次郎 监狱学
不详 国际公法志
(日)柴四郎 埃及近世史
(日)松平康国 世界近世史
历史类 (日)山本利喜雄 俄罗斯史
(美)威尔逊 历史哲学
其次,日文中译新作读者市场广阔,出版机构为追求利润,也推波助澜大量出版。由于出版日文西书有利可图,各种译书出版机构总是想方设法搜罗日文西书翻译出版。近人著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看到译印书刊有利可图时,就专门设立了“编译所”并请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担任所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教科书的编译为出发点,学习日本编印西学教科书的经验,翻译出版了多种日本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印教科书以应清末设立新式学校之急需,也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后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以编印教科书为主的重要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除了教科书的编译外,另外在社会其他学科日文书籍的翻译出版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896年至1911年间,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的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国内外机构有95家之多。[8](P651-656)可见,这么多的出版机构纷纷选择日文西书翻译出版,其对日文中译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再次,日文中译出版事业的繁荣与留日学生的翻译出版活动有密切关系。留学生翻译出版日文西书始于1898年。1900年,作为留学生译书出版事业机构的译书汇编社成立,并出版有《译书汇编》杂志,连载日文中译作品。《译书汇编》创刊号刊载有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美国伯盖斯的《学》、法国伊耶凌的《权利竞争论》等十余种著名的西学著作。从《译书汇编》第1、2、7、8期四期刊出的译文及已译未刊的108种书籍目录看,有卢梭著《教育论》、斯宾塞尔《政治进化论》、《社会平权论》等。其中很多西学著作作为日文中译作品,由译书汇编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发行。[9]译书汇编社所编译的日文西学读物,发行范围遍及中国大陆、日本、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该所翻译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尔等人西学名著的出版,对“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10](P283)此外,教科书译辑社、《游学译编》等机构和刊物积极参与日文中译事业,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西学书籍。留日学生还积极参与了国内的日文翻译活动,或在国内创立机构、或受聘参与编译,对传播西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香港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有关1896年到1911年整个时期日文中译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一时期中译日书共958种。其中社会科学类最多达366种,占整个译书总量的38%;世界史地有175种,占18%;语言类133种,占13%;其他科技类译书仅近百种。[11]政治、法律、、经济、思想道德、民权宪法等社会科学书籍的大量翻译,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日文中译传播西学、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政治方面的译作注重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的宣传,对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欧洲的多党政治、西方的议会制度都进行了有效的介绍。在哲学社会学知识的翻译和传播方面,中心突出了对近代西方进化思想的传播。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的传播除严复译《天演论》外,留日学生杨荫杭翻译加藤弘之著的《物竞论》、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及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的出版,在留学生中及国内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出了激发国人发愤图强积极进取的爱国主义主题。日文中译史地、新政、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方面书籍的大量译介出版,如《法兰西革命史》、《人权宣言》、《美国独立战史》等书的出版,激励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于近代资产阶级维新与革命的运动。日文中译作为一种文化运动,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历史的贡献。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村井知至《社会主义》等书的翻译出版,向中国传播了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见,以日文中译传播西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革命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的变化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
四、日文中译存在的不足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通过日文中译传播西学事业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再进一步对日文中译的形式与方式、一些机构的译书目的等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首先,翻译内容不具,种类繁多,日文中译事业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混乱性局面。近代通过外文翻译传播西学事业进入日文中译时代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繁荣”局面。在翻译出版的日文西书中,除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主流科目外,地理、理工农医等多种知识都成为译书出版传播的对象,可以说是种类繁多,无所不包。日文中译的对象是内容不具、毫无选择性,也就是常说的“梁启超式”的翻译,无组织无选择,惟“以多为贵”。日文中译的无选择性,使西学的传播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错位:在转贩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立宪保皇思想;在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甚至连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西方堕落生活方式书籍也有所翻译出版。无政府主义在欧美日本影响比较大,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从1906年1月发行第2号起,不断刊载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译文。从1907年下半年起一段时间内,该报又大肆宣扬虚无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翻译的形式与方式具有较强的急功近利特点,没有形成成熟的翻译理论以及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翻译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文中译高潮的形成,主要是适应了同文同种、速效费省及利于西学转贩的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社会进入由传统向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各个社会思想派别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宣扬自己的学说。在传播西学的日文中译活动过程中,不同的思想派别总是不遗余力地迅速译介相关西学知识,为自己派别的主张服务。改良派急于介绍西方立宪理论,如1901年康有为翻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是为资产阶级立宪保皇运动服务的;革命派热衷传播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是为了从理论上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作理论准备。在通过日文中译事业转贩西学的过程中,各个派别利用一些有翻译才能的人翻译日文西书西文,为其翻译出版及西学传播事业服务。在所利用翻译人才结构上,主要有机构聘请的日本人、留日学生、国内学习过日语的人才等不同层次。由于日文中译的风起云涌,日语翻译人才总量和水平是有限的,对日文中译人才的要求就有所放松。在章锡琛对当时参加翻译活动时的回忆中就曾经谈到,受《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之邀,为杂志翻译文章。当“我去见亚泉先生的时候,他就问我是否懂得一点日文,我回答说,虽然从前学过一点,却没有学好,而荒疏日久,也多忘记了。不料进馆之后,他第一件给我的工作,就是从一本日文杂志,叫我翻译一篇镭锭发明者居里夫人的传记。”[12](P100-101)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第8卷11号的《东方杂志》上,以后又接连翻译了几篇。由此可以看出日文中译对人才水平要求的宽松,翻译作品也就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及专业名词术语的千差万别。日文中译时代译界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人才,如杨荫杭、杨廷栋、戢翼晕、赵必振等。这些人才群体对日文中译转贩西学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没有形成成熟和系统的翻译理论,其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贡献却不像同时代西文翻译界人才严复、林纾那样有自己特点并且成熟的翻译理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西学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错误,使部分西学知识失真。如1902年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一本《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是以俄文翻译成日文,再由日文译成中文。中译日文读物其文本几经转译,就缺乏对一些关键词汇的准确把握,造成西学内容的失真。
其三,一些译书机构商业色彩浓厚。近代上海受欧风美雨沐浴,商业气息浓厚,文化出版界一些近代新式经营性层出不穷,推进了上海都市文化近代化的进程。商业利益驱动是活力的源泉,但将日文中译转贩西学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进步联系在一起考察,日文中译出版机构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商业经营性企业看到出版日文译书及载有翻译文章的报刊有利可图,就纷纷加入日文中译活动,出版新书、创办新的报刊,使译文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商业企业一般是尽力刊行那些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卖点比较好的作品,所以投机性很强。当清政府准备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译介日本教科书就成为一个赚钱的机会。1912年清政府颁发“壬寅学制”,客观上为编译近代教科书开辟了巨大的市场,商务印书馆于1902年成立编译所,之后一段时间先后刊行数量众多的教科书。此外,还有文明书局、乐群图书编译局等出版机构对教科书的编译也付出较多努力,取得不小的收获。日文中译的类似情况比较多,当社会谈地方自治时,有一系列地方自治的书刊出版;当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占上风时,有大批西方革命学说论著刊行;当文学革命运动高涨时,欧美日本等国小说就会被广泛翻译。翻译出版活动中存在的局部商业趋利性特点,使得日文中译转贩西学事业在一定时期形成若干个竞争激烈的热点版块,市场竞争加剧,削弱了西学传播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大量日文中译书籍的重复印刷,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日文中译时代西学作品的重复刊印情况比较严重,其中主要是那些销售量大、社会影响大、阅读范围广的社会评论、政治小说等类作品。这对近代相对落后的文化出版业来说,是一种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最后,从日文中译西学作品向中国输入大量的新名词来讲,说明日文中译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但同时也表明日文中译转贩西学事业缺乏必要的创新。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很深,日本语里有很多当用汉字是从汉语发展而来的。在日文中译活动中,许多中国人翻译日文时对有关当用汉字就没有转译,而是原样照搬。这样,就使日语当用汉字作为专用术语输入中国,对中国汉语及各学科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以教科书的翻译出版为例,许多日文中译教科书原封不动或依据日文书籍原有框架略加修改就在学校里使用,对初次接触西学知识的中国学生影响深远。日文中译的照抄照搬,对所介绍西学内容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创新发展,制约了所转贩西学理论与中国现实实践的密切结合并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更有甚者,对近代日本蔑称中国的“支那”等词汇也未作任何变动而加以翻译,先后刊印了《支那国际论》、《支那化成论》、《二十世纪之支那》等书刊,表明翻译者对此问题的疏忽和思想认识上的不重视。所以,如果在日语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再进行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等方面的创新,会有助于西学知识更广泛的传播。
【】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梁启超.东籍月旦叙论[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Z].北京:群联出版社,1954.
[4]张之洞.劝学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6]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Z].北京:群联出版社,1954.
[7]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7.
[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9]吴湘湘编.译书汇编[Z].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10]冯自由.革命逸史[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Z].北京:群联出版社,1954.
[11] 张承谟.近三百余年中日图书互译概况——兼评两本中日译书综合目录[J].世界图书,1989,(5).
[12]从商人到商人.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