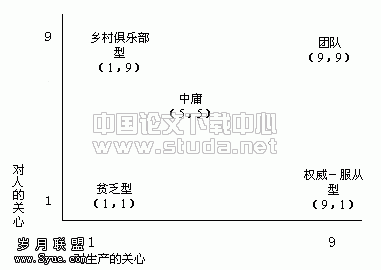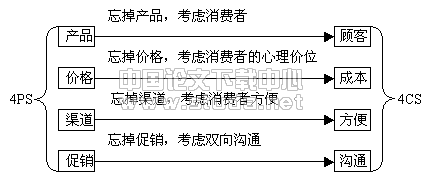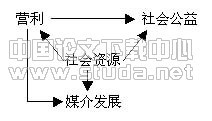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
[内容摘要] 在纪录片面临内容和主题的深化、表现手法的更新之际,人类学纪录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国内的一些先行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那么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又有几种类型?请参阅本文。
[关键词] 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文化
“人类学纪录片”顾名思义,它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人类学和纪录片,两者密不可分。但它既不等于人类学的传统文字表达方式,也不等同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纪录片。就内容而言,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的、理性的,属学术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等同,而与一般纪录片有异。从表述形式来看,人类学纪录片则又是鲜活的、形象的,与人类学书面著作的表述方式完全不同,而与一般纪录片相同。由此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是成果与形式的完善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类特殊类型。“人类学”和“人类学纪录片”都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人类学”较早,本世纪初就已传入我国,而“人类学纪录片”就很晚了,直到“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Asen Balikci)来我国访问,这个片种才被介绍到我国”。①
在里,西方国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有若干种不同的称呼。一般称为Anthropologic Documentary(人类学纪录片),或Ethnologic Documentary(民族学纪录片)。也有的人把其中单纯记录某一民族的文化现象,但很少或不加任何解释和评价的影片称之为Ethnographic Documentary(民族志纪录片)。这些不同的命名多少有些差异,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兼容,这主要是在人类学界使用。而影视圈内,一般把这类影片通通归于纪录片,仅仅认为它是纪录片中的一类,并没有赋予它比一般纪录片更多的含义。
当今世界,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可以把不同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促使人们开展对话,让人们分享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从而唤起人类对自身深刻而积极的感受。在世界人类学第9届大会上,与会人类学家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②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一、 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
人类学纪录片是随着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据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保罗·霍金斯(美国)的文章称,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人是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他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第一部民族志电影”。
最初,人类学纪录片在人类学界不受重视,它只不过是作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附带产物,而并没有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中用以引用的重要部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格利哥利·本特森(Gregory Bateson)和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将人类学和电影结合到一起。
本特森曾在新几内亚东北部的色皮克河沿岸的雅特木耳人中间进行过田野调查工作,并写了本题为《耐温》(1936年)的专著。米德则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他曾写过大量的专著和文章,并早已由于他的人类学著名通俗易懂而著称于世。本特森和米德于1936年—1939年在一个巴厘人的小村庄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这一项研究对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一起。他们用摄影手段来弥补早期各自工作中的不足,例如生动的可视性图像可以使本特森非人格化的抽象分析更加丰满;再比如纪实性的纪录片可以使米德对人类行为的广泛描写更加生动和深刻,纪录片就像他们的人类学著作一样,描写了人们的行为,并展示了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在纪录片的“许多地方集中表现了小孩儿之间以及小孩儿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譬如他们在影片中表现了巴厘人挑逗小孩儿的这样一种行为:用手触摸刺激婴儿,使他达到近乎兴奋最高点时,突然停止与婴儿的接触,这对研究成年的巴厘人没有高兴奋点的‘稳定状态’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也以生动的形象表明,这一点在纪录片中可以很好地被表现出来。”③
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他们结合25000幅照片在1932年出版了两部著作。另一方面,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纪录片,于1950年发行。在本特森和米德的系列片中,他们有一部影片纵向地研究了一个叫卡贝的小男孩,从7个月开始一直到3岁,以他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儿童早期成长的几个关键发育期。本特森和米德有意识地把电影用于人类学研究,用电影来表现形象化的运动,并从整体上表现复杂的场景间各种相互关系,这种运动和关系在电影中比在纯文字中要好表现得多。这样,他们对电影的运用就成了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弥补了文字材料的不足。
本特森和米德将纪录片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的方式,为后来的人类学家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们的文字报告加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方式,也为人类学界认同,一本书再加上一部人类学纪录片成为后来人类学研究最佳的成果表述方式。
二、 人类学纪录片的表现对象
人类学纪录片表现的对象同人类学一致,是人类的文化和“向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们解释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的行为”。④
“德国的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是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⑤,以下我们试列出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保存的德国和丹麦拍摄的部分人类学纪录片,从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学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摘自德国格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电影百科档案人类学片目录和内容简介,欧洲专册》)
《在黑林山开垦地》——火烧开垦土地并平整(E496,1937,“E”为科影所存影片编号,后为年代,下同——引者注)
《在巴登外勒榨油》——300年前的水动榨油机结构(E1965,1972)
《布勒特璃的金线刺绣》(E983,1965)
《符腾堡的土法烧炭》(E651,1959)
《水力锻造作坊》(E658, 1963)
《镰刀割黑麦》(E927,1951)
《式烤制面包》(E931,1950)
《抄网冰上捕鱼》(E930,1947)
《蓝靛染房》(E928,1948)
《纷法诺人戴头饰》(E929,1951)
……
我们统计了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40部人类学纪录片,像《符腾堡的土法烧炭》、《镰刀割黑麦》这种表现欧洲各国残存的,而现在许多已消失的传统物质生产流程内容的纪录片,占绝大多数,共有25部,占全部纪录片的60%强;其次是类似《黑林山复活节举火活动》、《圣灵降临节》这种具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民间宗教节目活动,共7部;此外还有表现民间娱乐活动的纪录片4部,表现民间生活的纪录片3部;还有利用影片形式,对比研究实现伦理道德观念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
三、 人类学纪录片的作用
关于人类学纪录片具体的作用,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在他的“影视人类学史”⑥中列出以下3条:
1. 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2. 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也就是说,首先,当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使用常规记录方式或观察方式无法把握时,它是人类学家辅助记录的工具。
例如对于民间舞蹈和巫术等的记录。影视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意)指出:“如果没有影视记录,对舞蹈和体态变化等文化现象的分析将十分困难(并且肯定不够完善)”。
其次,人类学纪录片也作为抢救人类文化的工具而存在,即前边所提到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民族志纪录片”,世界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社会文化急速变革,大量传统文化形式来不及保存下来,更来不及仔细研究,转眼便消失。文化的消失具有不可复得的特征,人们急切地感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使之得以保存,人类将失去大批宝贵财富,同样对发展新文化也十分不利。这种紧迫的形势给人类学纪录片带来了发展转机。因为形势紧迫,许多从前不关注,甚至不愿意使用影视手段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影视手段具有许多为传统研究手段所不具备的长处:它能够在比传统的笔录方式短得多的时间内收集到比笔录多得多的原始资料,而且这样的资料生动、形象,真实可信,并且可以重复放映,反复观察研究。他们意识到把电影电视这种化手段与传统手段结合起来,对于人类学研究大有裨益,于是,把眼光投向人类学纪录片,用影视手段来“抢救”人类即将消失的文化。
对于民族志纪录片,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指出:“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⑦
此外,人类学家利用人类学纪录片的直观可视形象性,将它用于横向的同时性跨文化对比,或纵向的性的文化变迁研究。这是一项真正的性的研究过程,就像以上片目中的《四个家庭——印度、日本、加拿大和法国农民家庭的比较研究》一片,将这4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对比研究。另外,像本特森和米德最初做的那样,他们在《巴厘和新几内亚儿童的竞争》一片中,将巴厘人和雅特穆尔人的文化背景和行为进行了对比。该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以影片的形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尝试,它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可比性。影片表现了不同地域的两个种族内发生的同类事象,例如耳朵的灵敏度,经验知识或创造性才能,还有像给儿童一个玩偶以引起竞争反应等等,将巴厘人和新几内亚塞皮克流域雅特穆尔人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比较。
四、 人类学纪录片的意义
以上我们谈及了人类学纪录片的起源、性质、表现对象、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同文字表述方式的区别,在此我们应该对人类学纪录片进行初步的界定,下一个定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这个问题:
“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
这个定义包含3层含义:其一是目的的表述,是为了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本质,研究是出发点,研究指导拍摄。其二是运用影视手段,影视手段是工具,是表达人类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媒体。其三是内容的表述,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是人类学研究和人类文化研究,它包括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种繁衍、组织规则、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等。
五、 人类学纪录片的分类
按照影视人类学家格瑞欧(Griaule)的分类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3类:
1. 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
2. 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
3. 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
其中第一类,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数量最大,也最珍贵。它包括只用一个镜头拍摄的一个完整过程,像制陶、打制器具、舞蹈等,也包括人类学家利用较长时间,对研究对象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记录。这些素材,可以提供给人类学家研究,更重要的是保存下来留给后来人。目前世界三大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就建立了人类学大百科全书影视卷,收集全世界各类民族的影视素材。
人类学素材片的价值在于,首先,它没有拍摄者的主观介入,没有像片似的主观设计。其次,它充分保存了现场的原始状态,没有把当时拍摄者尚不理解,或用当时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信息过滤掉,完整而全面地保存客观事物的原貌,因此,后人可以从中读解到更多的信息,有利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此类人类学素材一向很受重视,具有永恒的难以估量的价值。
第二类,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一般是那种只剪去素材中冗杂的部分,经过粗编后的纪录片。有的加解说;有的则不加解说,附有文字说明。这类纪录片虽对素材经过剪辑加工,但依然保留着原始资料的性质,未提供摄制者的任何见解。“美国人类学纪录片制作者保罗·霍金斯(Paul Hockings)1968年在爱尔兰摄制的《村庄》就属于这种类型。该片长70分钟,虽然只使用了原始素材的1/13,但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仍然是没有摄制者观点介入的当地生活实景写照。全片没有解说,只有少量字幕,用来翻译片中人物说的爱尔兰语。”⑧此外,像美国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G·Helder)摄制的《达尼人的房屋》表现了两类不同达尼人房屋的建筑过程;英国人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摄制的《昆布须·曼的仪式舞》展示了卡拉哈里布须曼人原始的医疗仪式,也属于这类教学用的人类学纪录片。
第三类,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用的人类学教学片是供大众观看的。“这类人类学纪录片加入了制作者的观点,是制作者按照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对素材进行剪辑和加工而成的,剪辑得比较细致,结构较完整。一定程度上说,这一类人类学纪录片是摄制者对所拍摄的文化事象所做诠释的结构性再现,或者说是摄制者对所反映的客观文化的主观再现。在这类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中,运用相同素材,根据不同的需要,常可以成功地剪辑出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纪录片。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最后的山神》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最后的萨满》这两部纪录片,前期拍摄在一起进行,所获素材相同,后期制作是从完全相同的素材中剪辑出来的。前者按照制作者自己对鄂伦春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衰落及其残存影响的感受和理解,用影片表现了萨满教在鄂伦春族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在鄂伦春族群众心理上的历史积淀,生动真实而富人情味,在1993年亚广联年会上获奖,后者则详尽、客观地展示了萨满祭祀仪式,包括萨满所穿法衣,使用的法器,祭祀程序和活动细节等完整段落,为研究鄂伦春萨满教的现状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1994年获选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萨满教学术讨论会。”⑨
注释:
①、⑤、⑧、⑨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美]保罗·霍金斯主编:《影视人类学原理》,伊利诺伊州荧加哥阿尔丹公司,1975年
③ [美]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④ [美]沃尔特·戈德施莱特《民族志电影:定义和解释》,收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保罗·霍金斯教授集《影视人类学原理》,1975年
⑥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著,邓卫荣译《影视人类学史》,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影视人类学通讯》
⑦ [意]保罗·基奥齐文,梦兰译:《民族志影片的功能和战略》,载《民族译丛》1994年2期,原载美国《影视人类学》杂志1980年2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