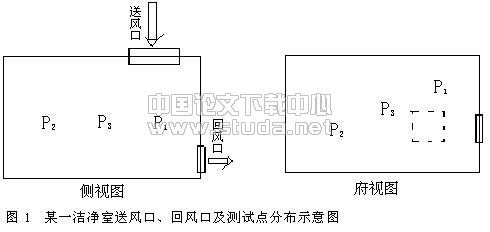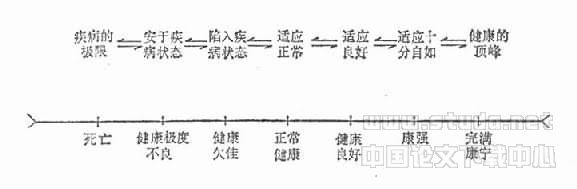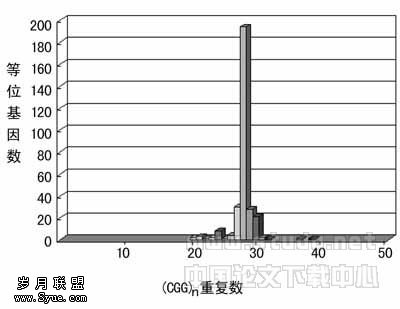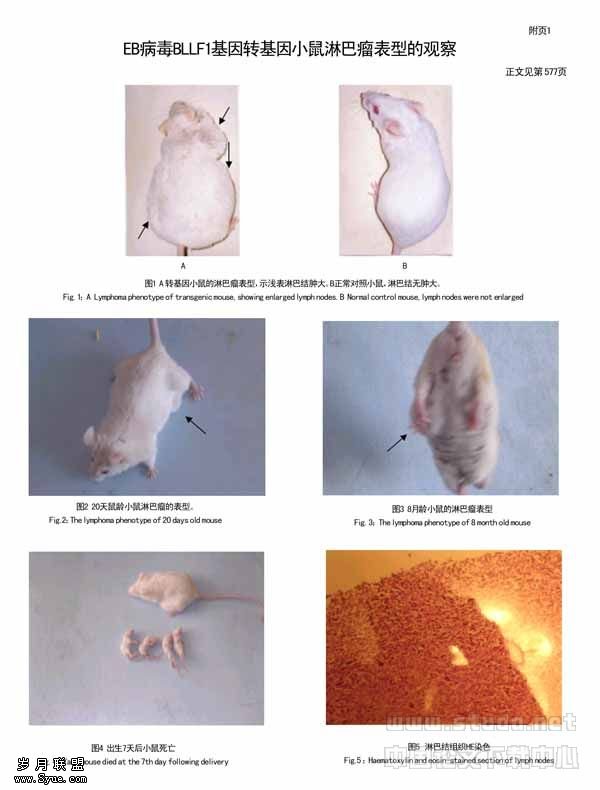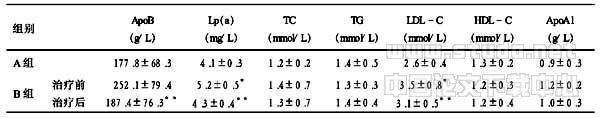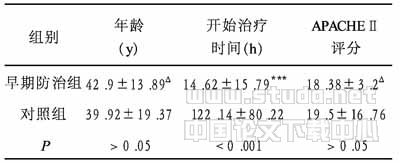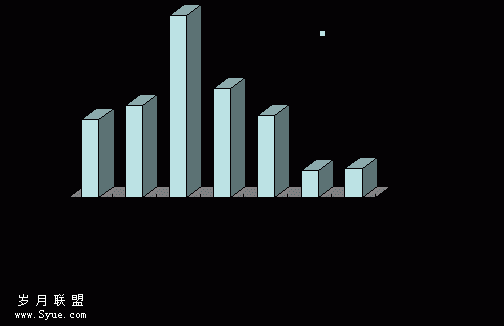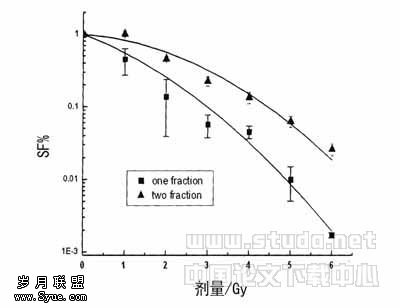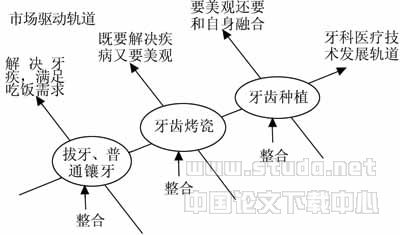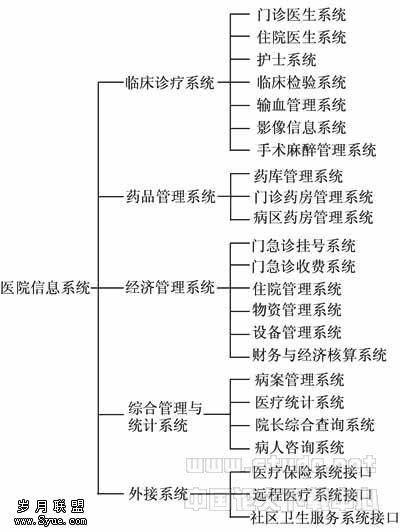试述《松峰说疫》诊治疫病特色
【摘要】 《松峰说疫》为清代著名医家刘奎所撰,该书在继承《温疫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三疫”说、创“瘟疫统治八法”和“瘟疫六经治法” ,了疫病的诊断、和预防方法,研究其中的治法和方药,对于疫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刘奎 《松峰说疫》 疫病
《松峰说疫》为清代刘奎所著。刘奎,字文甫,号松峰,清代山东诸城人。刘奎自幼受父亲影响,且因自身患病,而发愤学医,并曾去北京跟随郭右陶学医,对《内经》《难经》研究精深,旁及金元四家及张景岳等医家的思想,特别推崇吴又可的《温疫论》,勇于探索,在继承吴又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补充,在治疗瘟疫症方面独树一帜,具有相当贡献。除《松峰说疫》外,刘奎还著有《濯西救急简方》《松峰医话》《景岳全书节文》《四大家医粹》《瘟疫论类编》等书。
刘奎有感于当时论述疫病书籍较少,以致时医多以伤寒法治疗疫病的弊端而著成此书。《松峰说疫》共分6卷,该书上承《内经》五运六气学说,下承《温疫论》等疫病名著,将疫病分为瘟疫、寒疫、杂疫,在书中论述了瘟疫、寒疫、杂疫的病因和临床表现,提出治疗疫病最宜通变,首创了“瘟疫统治八法”,载病症一百四十余种、方剂二百多个,治疗方药每有新意[1]。
1 提出“三疫”学说
刘奎在继承吴又可理论的基础上,独抒心得,在瘟疫之外,又增加了寒疫、杂疫。刘奎认为,疫病一症所概甚广,瘟疫不过疫中之一症,始终感温热之疠气而发;并认为瘟疫一症,非他症可比,不能缓为调理,须在一二剂之内见效,三五日之间痊愈。
书中详细论述了瘟疫、杂疫、寒疫的病因和临床表现之不同。认为寒疫,无论春夏秋冬皆可发病,感受风寒之邪突然发病,出现头痛、身热、脊强,感于风者有汗,感于寒者无汗,且冬月也可发疹,轻者可自愈。也有发于夏秋之间,症状与瘟疫相似,不可用凉药,不能一汗而解,需多日才能痊愈。对寒疫的症状和治疗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杂疫则千奇百怪,其病则寒热皆有,众人所患皆同,皆有疠气以行乎其间。以平素治法则不应者皆为杂疫,较之瘟疫更难揣摩。杂疫的归类虽然不太确切,但刘氏提出杂疫的诊断和治疗较复杂等认识较为实际。这些观点较吴又可的认识更为全面。
同时,刘奎还强调将瘟疫和非瘟疫性疾病区别开来。《松峰说疫·辨疑》针对《景岳全书》“瘟疫本即伤寒”的观点,提出“第伤寒为寒所伤……以致头痛憎寒,皮肤壮热,病只一人而止,而众人不然也。至于温病决无诸项感触,而抖然患病,且非一人,乡邑,闾里动皆相似,其症虽有头痛身热,脊强多汗,始终一于为热[2]。”
2 创“瘟疫统治八法”
对于瘟疫的治疗:古代医家认为“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刘氏取前辈医家之长,指出瘟疫是在兵荒、饥饿的社会背景下,又遇五运六气之乖候,以及人事悖逆交织而成,尽管四时气候、五运六气之因皆相同,但人事悖逆则可能不同,“七情之有偏注,六欲之有慝情,或老少强弱之异质,或富贵贫贱之殊途[2]”,因此即使都是瘟疫,治法必有差异,同一种治法,可能有效可能不效,或施之此人有效,施之彼人又不效,或初施之有效,再施之不效。如用一方一法治疗,则会导致失败,正如刘奎在《松峰说疫》“治疫病最宜变通论”中所言:“惟至于疫,变化莫测,为症多端,如神龙不可方物。临证施治者,最不宜忽也[2]。”据此提出解毒、针刮、涌吐、罨熨、助汗、除秽、宜忌、符咒之“瘟疫统治八法”。纵观其治法,其中皆治疗和调护方法并用,颇有特色。有针对三阴三阳之传变的各种方药,既有前人方药的继承,又有刘氏自己的心得,包括药物疗法,和外治方法。
八法中,刘氏首列解毒法,认为人所患疫,是有“毒气以行乎间”,无毒不成疫,这种毒气区别于一般的阴毒和阳毒,“未病之先,已中毒气,第伏而不觉,既病之时,毒气勃发,故有变先诸恶候[1]”。故毒气与瘟疫相为终始。这就是导致瘟疫的毒气,在未病之时,已藏于体内,故治疗就要解除疫毒——“除秽”,自拟金豆解毒煎,皆为清热解毒之轻剂。
对于汗、吐、下的逐邪方法,刘氏也作了分析,如吐法吴又可认为邪在胸膈,欲吐不吐者,可用此法。而刘氏则认为瘟疫不论病发几日,大吐则为吉兆,“将欲汗解也。”因吐法含有发散之意,吐法“尚能发瘟疫之汗”。认为吐法使用较少,但其确有效。
刘奎论及“助汗”时说:“瘟疫虽不宜强发其汗,但有时伏邪中溃,欲作汗解,或其人秉赋充盛,阳气冲激,不能顿开者,得取汗之方以接济之,则汗易出,而邪易散矣。”还提出“汗无太速,下无太迟”之说,以及其提到的针刮、罨之法,无不促邪排毒,且给以开门之便。刘奎于治疗湿温时指出:“瘟疫始终不宜发汗,虽兼之中湿,而尚有瘟疫作祟,是又当以瘟疫为重,而中湿为轻,自不宜发汗,当用和解疏利之法,先治其瘟,俟其汗出,则湿随其汗,而与瘟并解矣”[2]。并自定新方除湿达原饮以调理气机,疏通表里。
刘奎因跟随郭右陶而擅长针刮疗法,在卷二“论治”中记载:“针法有二,用针直入肉中曰刺。将针尖斜入皮肤向上一拨,随以手摄出恶血曰挑。刮法有四,有用蛤壳者,有用瓷盅者,有用麻蒜者,有用铜钱者”。在卷三“杂疫”七十余例中用到多种针法、刮法。其中关于痧症治疗,大多出自《痧胀玉衡》,如放痧法、刮痧法、新定刮痧法,放痧十则,治痧三法等。这些方法皆为针刮疗法的具体应用。而且载录的这些方法皆加了按语,放痧十则中提出了十处放痧的部位。刘氏按语:“以上但直刺”。治痧三法中归纳了肌肤痧用盐水刮、血肉痧用刺法,而内形痧则须辨证用药。在“宜识痧筋”中提到“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现于一处,必用针去其毒血,然后据症用药”,并加按语:轻者针即见效,不用服药。如对于瘟症传里导致神昏谵语者,刘奎提出刮痧和针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
3 “瘟疫六经治法”
刘奎了仲景《伤寒论》六经证治学说,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瘟疫六经治法。同时主张瘟疫应早期治疗,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主张抓紧时机,早期治疗。故刘奎也提出 “真知其邪在某处,单刀直入批隙导裒”的截断病源之说,将卫气营血辨证施治和截断病源辨病用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逐邪作为治疗疫病的第一要义,提倡“重用清热解毒”“早用苦寒泄下”“不失时机地清营凉血”,认为对于瘟病(泛指各种传染病),必须抓住早期治疗,必要时可以早期截断卫-气-营-血的传变。
在具体用药上,刘奎不拘于张景岳、吴又可、郭志邃等前辈医家的理论,历代医家认为瘟疫属热者多,治尚寒凉,而他却施以温药。同时提出慎用大寒之剂,但又不排斥用大黄、石膏、芒硝。他说:“或曰:大苦大寒之剂既在禁例,而治瘟疫顾用三承气、白虎何也?答曰:石膏虽大寒,但阴中有阳。其性虽凉而能散,辛能出汗解肌,最逐温暑烦热,生津止渴,甘能缓脾,善祛肺与三焦之火,而尤为阳明经之要药。……大黄虽大寒有毒,然能推陈致新,走而不守。瘟疫阳狂、斑黄、谵语、燥结、血郁,非此不除。生恐峻猛,熟用为佳。至于芒硝,虽属劫剂,但本草尚称其有却热疫之长,而软坚破结非此不可,……此治瘟疫者之所不可阙也欤[1]”。
4 提出温疫防疫措施[2]
对于疫病,刘奎提出具体防疫措施,如“凡有疫之家,不得以衣服、饮食、器皿送于无疫之家,而无疫之家亦不得受有疫之家之衣服、饮食、器皿”,“将初病人贴身衣服,甑上蒸过,合家不染”,“入病家不染:用舌顶上额,努力闭气一口,使气充满毛窍,则不染。”入病家不染方, 香油和雄黄, 苍术末, 涂鼻孔。既出, 纸条探嚏。
刘奎还提出“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秽恶之气,……入瘟疫之乡,是处动有青蝇”,说明苍蝇是传播疫病的重要媒介,因此相应提出了“逐蝇祛疫法”,以及用屠苏酒方、麻豆投井方、苍术、贯众、赤小豆等进行饮用水的消毒。
《松峰说疫·避瘟方》共载65方,用法有内服、纳鼻、取嚏、嗅鼻、探吐、佩带、悬挂、药浴、熏烧等多种。其中以使用内服、熏烧、佩带、放于水缸及井中法、挂于庭帐频率最高。尽管《说疫》所列的使用方法较为古老且繁杂,但其中数法仍具现实意义。如佩带方、悬挂方可制成装饰品使用;熏烧方可制成熏香、蚊香使用;沐浴方可制成浴液使用;置于水井水缸中诸方可配合饮用水净化或代茶饮中使用等等。可见刘奎当时已对传染病之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重视隔离与祛邪消毒,易感人群,包括医护人员的保护都已有了创见性的措施和认识,对后世医家预防治疗疫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
《松峰说疫·善后》篇中也论述到疫病后期的调养:“瘟疫愈后,调养之方,往往不讲,而抑知此乃后一段工夫,所关甚巨也。”并总结了疫病复发的三个因素:一曰淫欲;一曰劳复;一曰食复。强调应重视后期调养。
《松峰说疫》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疫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研究其中的治法和方药,对于疫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
[1] 宋乃光.《松峰说疫》温疫观析[J].中医药学报,1988,4:52.
[2] 清·刘奎著,海陵,李顺保校注.松峰说疫,第一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19,128,127,130,134,126,23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