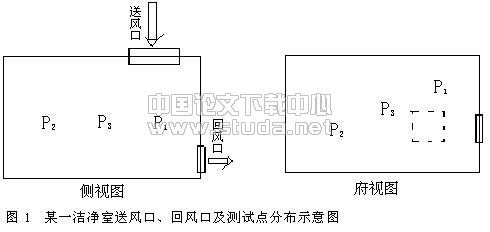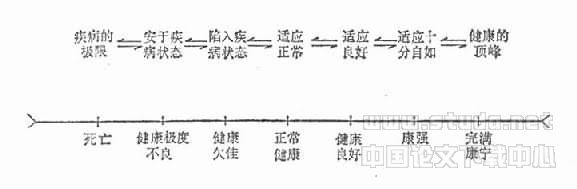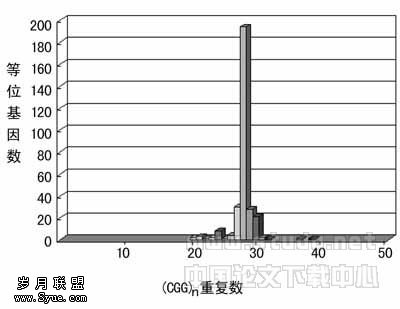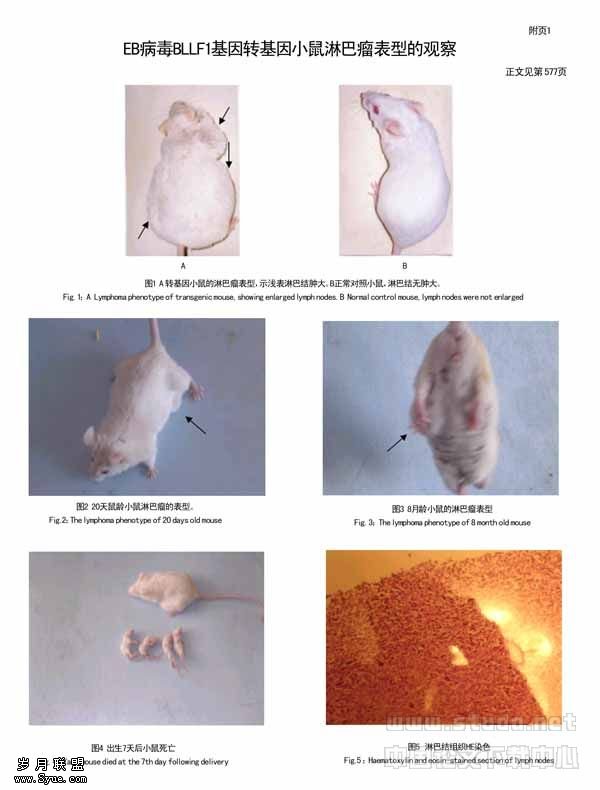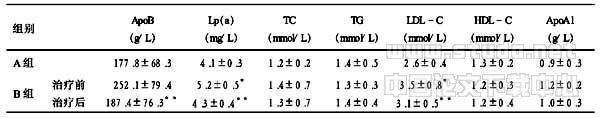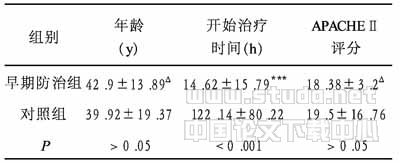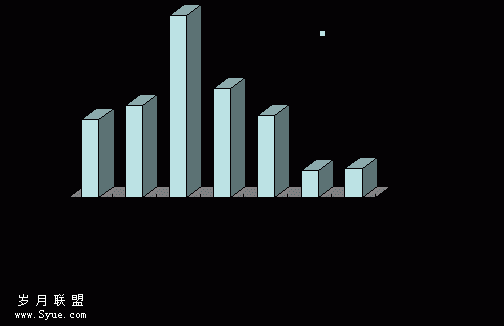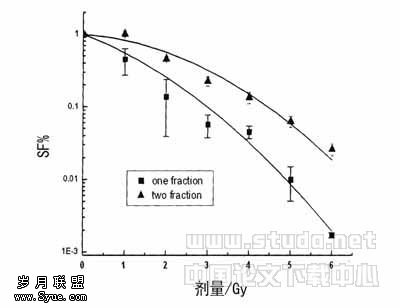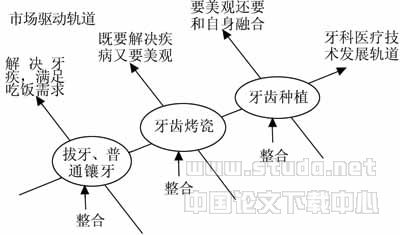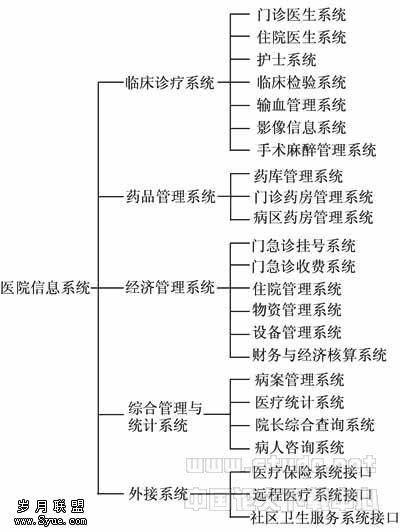从“薄厥”的不同解释看神明问题
【摘要】 “薄厥”是《内经》明文记载的由情志刺激引发的一种疾病。历代注家对“薄厥”的病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解释的分析表明,解释者对待“神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有可能是导致对“薄厥”的不同解释的一个主要原因。张山雷对“薄厥”的失误解释分析表明,中西医在“薄厥”(中风)的病理解释问题上的异同需要被极为谨慎地处理。这对中医情志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 薄厥; 黄帝内经; 神
Abstract:Sudden reversal is a kind of disease originates from affect-mind stimulation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Study on various explanations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sudden reversal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spirit and mental disorder lead to the variety of its explanation. Especially,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between west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topic should be treated with much cau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explanation of sudden reversal from ZhangShanlei.
Key words:sudden reversal;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Spirit
情志致病学说是《内经》的重要内容。情志刺激所致疾病,既包括躯体症状,也包括情志、神志方面的障碍。本文尝试通过对“大怒”引起的一种疾病——“薄厥”的分析,探讨不同注家在“神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如何导致其作出对“薄厥”的不同解释。
1 杨上善的解释
“大怒”导致神志障碍,在《灵枢·本神》有明确记载:“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张介宾归因于“大怒”对人体气机的强烈扰乱:“怒则气逆,甚者必乱,故致昏迷皇惑而不治[1]。”但是,气机逆乱为什么会引起神志障碍?张介宾没有细说。我们通过“薄厥”病机的分析来补全答案。“薄厥”一病见载于《素问·生气通天论》,它既源自情志刺激(“大怒”),又主要表现为神志症状:“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杨上善认为,“薄厥”的病机是气血上冲于头:“阴并于阳,盛怒则卫气壅绝,血之宛陈,上并于头,使人有仆[2]。”“薄厥”与《素问·举痛论》的“呕血”“飧泄”一样,属发怒所致病症;“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实即“怒则气上”的另一种表述。杨注释“薄厥”病机为气血上冲,积于头部,亦即释“怒则气上”之“上”为头。杨上善对“薄厥”的这种理解,与王冰对《素问·举痛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的理解遥遥相应。《素问·举痛论》王注:“怒则阳气逆上而肝气乘脾,故甚则呕血及飧泄也。何以明其然?怒则面赤,甚则色苍[2]。”
王冰举发怒时的面色变更作为“阳气逆上”的证据,这使我们了解到,此处他理解的“怒则气上”,乃气上及头面之义。但王冰对“薄厥”一病的解释,却与杨上善大不同。
2 王冰的解释
《素问·生气通天论》王注:“大怒则气逆而阳不下行,阳逆故血积于心胸之内矣。上,谓心胸也[2]。”
“心胸”“胸中”同义。王冰认为“薄厥”不是气血上冲,积于头部,而是气血上冲,积于心胸。这和《灵枢·五变》对“消瘅”病机的论述(“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很接近。然而,和“消瘅”不同,“薄厥”是以神志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急性发作性疾病。王冰释“薄厥”为血气冲胸而不是血气上头,有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既然“薄厥”的主要表现是神志症状,那么对其病机的解释就必须围绕神志这一主题来进行。心藏神,位居胸中。释“薄厥”为血气冲胸,显然比释“薄厥”为血气上头更为切题。
由日本江户时代医家森立之对“薄厥”的解释,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对“薄厥”病机的理解是如何与“神明”问题相互联系的。森立之《素问考注》:“薄厥者,谓血薄于上而四末厥逆也。此证乃狂癫之渐也。凡气血奔迫于心肝,则发狂证[4]。”
森立之认为“薄厥”与“狂癫”同类。这种认识依据五神藏学说。气血冲击心肝,则心肝不宁,心肝不宁则神不清明,所以,“薄厥”与“狂癫”均属以心为首的五藏受扰所致的神志疾病,唯病情有浅深之别。从这一立场出发,《素问·生气通天论》“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之“上”,只能被解释为心肝等藏所在位置、例如“心胸”,而绝无可能被解释为头。
3 张山雷的解释
王冰对“薄厥”的解释可能部分地出于他对“神明”问题的敏感和自觉,这种自觉也体现于清末民初医家张山雷对“薄厥”的解释。后者与杨上善对“薄厥”的解释有外表上的相似。
比起森立之的从容意态,张山雷的见解带有明显的攻防意味。近代以降,随着西医影响流布,中医界“舍其田而芸(耘)人之田”之风日长,即使笃信中医者如张山雷,也必须谨慎处理西医知识与中医论断的差异。张山雷对“薄厥”的解释就是针对“西学家脑病之说”而发。西医认为,中风是脑部病变,这与杨上善以“薄厥”为气血上并于头的看法,在病位认识方面颇为相似。但张山雷认为西医的看法乃皮相之见:“迩来西医学说日以洋溢,内风昏瞀之病属于脑经已无疑义,即素习国医而兼有新智慧者亦莫不以西学家脑病之说为是。然须知此病发见之时,脑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酿病之本源。病源为何?则肝阳不靖,气火生风,激其气血上冲犯脑而震扰脑之神经耳。”[5]
张山雷认为“薄厥”“大厥”等“内风昏瞀之病”,病机是“怒则气火俱升”[5],迫血上涌而伤脑,其病标在脑(头),其病本则在于肝。把“西学家脑病之说”说成是《内经》已有之义,不但使中医理论体系免受西医逼迫,而且把外来的威胁转化为有利于己的证据,这种防守反击战术颇能夺人耳目。但其心可鉴,其论却大可商榷。更准确地说,缺陷不在其论点,而在其论证:西医对中风的病理研究集中于大脑局部的器质性病理改变,这种做法尽管被张山雷贬为无识,但在其设定的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法之内,西医对中风的病理机制是可以说清、而且已经说清了的。相反,张山雷虽然提出了见解,却拿不出任何超出西医中风研究成果的、得自实证研究的证据。如果说这一缺失尚能被勉强解释为中西医学体系的异质性,那么另一方面,“肝阳不靖,气火生风”之类陈言则说明,张山雷只是片面地引用《内经》的个别词句来比附西医对中风的病理解释;对包括“薄厥”病机问题在内的“怒则气上”机制问题,实无系统的周密的思考和研究。这种把《内经》公理化、教条化的做法,看似是对《内经》的坚定维护,实则是一种“学而不思”的表现。不求甚解、急于求成,不但有悖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而且对中医和中医研究都有极坏的影响。实证研究和理论依据两方面都立足不稳,使得张山雷的声音在西医尚未涉足、《内经》隐而不彰的领域,显得格外空洞。
另一方面,张山雷虽把脑由“酿病之本源”降为“受病之部位”,但对西医以脑(神经)为“神明”之主的立场却没有异议,说明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薄厥”(中风)的病理解释这一局部战场,对中西医的深层分歧、亦即“神明”问题上的对立尚无意识。这种态度既不同于杨上善对“薄厥”与“神明”问题的关系的懵懂,又不同于森立之论及神志疾患时的理论自觉,也迥异于同时代中西医汇通派医家张锡纯在“神明”问题上的调和论倾向。张山雷的见解包含了太多仓猝与惘然。
解释反映解释者的认知模式和偏好,也折射出解释者的处境。“薄厥”的不同解释的得失,提示我们对《内经》情志致病学说作更具体、更审慎的研讨。
【】
[1] 张介宾.类经,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51.
[2] 王洪图,李 云.黄帝内经太素,第2版[M].北京: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71.
[3] 王 冰.黄帝内经素问,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85,12.
[4] (日)森立之撰;郭秀梅,(日)冈田研吉校点.素问考注,第1版[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75.
[5] 张山雷.中风斠诠,新1版[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8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