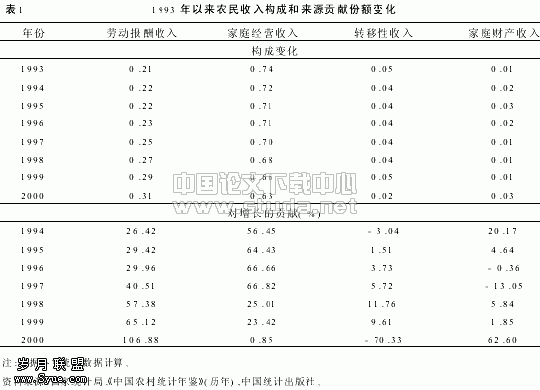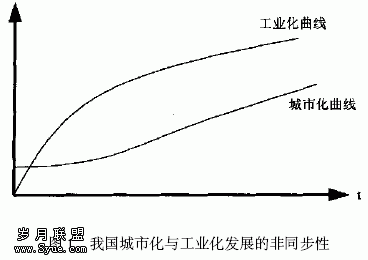1949年—1956年中国农民的心理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关键词:中国农民;心理;求富;均平;个体经济;合作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所养成的社会心理既不同于工人阶级,也不同于其他阶级阶层,如保守、勤俭、安分守己、自私自利、平均与等级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6年。农民的心理变迁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 谁养活谁
这是土地改革中遇到的第一个观念上的问题。按理说,农民对土地的盼望是最为迫切的。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压迫而导致生活困苦,最后无衣无食。揭竿而起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分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陈胜、吴广起义始,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止,这一点贯穿始终。农民起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其《天朝田亩制度》中给农民画的蓝图其中就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1](p530)
但是,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却也使农民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即等级观念。这样,一些农民甚至觉得地主的田地养活了农民。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又是事实。当时参加土地改革的许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如冯友兰回忆:“在这次土改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养活谁’。”地主认为,地主有地,农民有劳动力,农民种地主的地,是互惠的关系,公平合理。并且,土地有限、劳力剩余,地主可以选择佃户,地主选谁,是对谁“恩赐”、“赏饭吃”。这种观点,也在农民心里有同样的反映。“这本来是地主阶级用以欺骗和麻痹农民的思想,可是沿袭久了,有些农民果然就为这些思想所欺骗、所麻醉,觉得打倒地主阶级似乎不很‘合理’,
觉得‘理不直,气不壮’。”[2](P127)土地改革初期,许多地方土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农民发动不起来,甚至出现农民将分得的财物悄悄地送还地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农民没有解决“谁养活谁”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工作组在土改开始时,反复宣传: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四川农民有歌谣唱这件事。
谁养活谁呀,大家看一看;
没有我们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我们下力干。
脸朝地,背朝天,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我们劳动,棉花怎能结成桃!
纺纱织布,没有我们就作不了!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我们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屋,全是我们下力干,
新衣褂、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二 求富与均平
求富是中国农民的特点之一,也是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求富”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家庭。这也是小农社会中的“家”为单位生产、生活而成的一种社会心理。在建国初期,人们对于富的理解,首先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认为这是农民保守的体现,但我以为并不能简单地如此分析。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多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尤其是贫雇农无地或少地。这样,追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就成为农民的首要追求。所谓“三十亩地”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在东北不仅30亩,在南方达不到30亩,而是说农民对土地的向往和感情。在当时,追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正是“求富”的首要目标和基础。这也是农民在被发动起来后,积极参加土改的原因。在土改中,人们对于土地的计较,包括在合作化时期对于入社的计较,都有求富的因素在其中。
土地改革对于农民来说,获得了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求富的基础打下了,接下来的就是在这个基础进一步追求富裕了。这种心态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改革后中农化趋势。这种状况在全国都如此。据1951年东北的统计这一时期富农上升很快,白城3个村有中农212户(其中富裕中农32户),占总户数的63.85%;蛟河荒沟有中农186户。占总户数的58%;磐石团结村,有中农156户(其中富裕中农15户),占总户数的70.59%;凤城西小堡有中农43户(其中富裕中农3户,占总户数的51.2%),舒兰3个村中农581户(其中富裕中农59户),占总户数的73.10%;肇州发展村中农239户(其中富裕中农12户),占总户数的70.5%。[4]
四川资中县长山村,村“大多数农民均以上升为中农,有一部分上升为富裕中农。”中农74户,占总户数的71.84%。除老中农29户外,佃富农变为中农1户,新中农44户,计雇农上升10户,贫农上升33户,手上升1户。[5](P220)
在中农化趋势的同时,两极分化也出现了,这就是土地开始集中。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再生产,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集中最能反映贫富分化。山西武乡在1948年和1949年,出卖土地户数共139户,其中“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村出卖土地的百分之三七点一)。”[6](P238)山西忻县土改后,1949年以来,“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亩,出卖房屋五千一百六十二间。”[7](P251)能卖出必有买进者,而买进者就是为了求富。这一点,文学作品中有更深入细致的描写:如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是当时有影响的小说,其原因就在于小说刻画了贫农宋老定想买贫农张栓的地发财致富,最后在大家帮助下,认识到不能走地主买穷人的土地的路。宋老定的话很有代表性:“做庄稼人啥贵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8](P3)
在农民依靠土地发家致富的同时,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考虑用其他方式发财致富。这种情况亦在全国都有。如在东北,“肇州发展村农民张如富说:光种点地不行,非想其他来钱道不可”。宾县民强村公正屯劳动模范王富海说:“你看我除有五.三亩地而外,还有什么发财路呢?”[4]为了致富,有的农民把余粮用到放利上去,“不干别的啦,光得利我的日子就不离了”。“用粮放利比种地省心,不费力”。有人投向商业。辽宁凤城小堡村中农杨恒春,1950年春投一半股份开药铺。“另外有三个党员干部卖了耕牛,亦计划和两个农民开制米所,因钱少没有开起来;另有两户到林口去卖花生。”“中农制办胶皮车劲大,这是普遍情绪,用以拉脚赚钱。”[4]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后来认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当时的农民是绝不会想到的,并且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程度。从当时农民的心理看,就是“发财致富”。否则,在土地改革大潮刚刚过去后,农民是不会冒险向资本主义路上前进的。
“均平”是小农社会的特征之一。历代农民战争都把“均平”放在口号上或行动上。农民起义中的“太平”就含有平均的意思。太平者,大平均也。在论述“太平”的《太平经》中,对“太平”的解释是:“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农民对太平的理解,往往和平均是联系在一起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说:“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P534)农民在追求这种思想几千年而不得后,其愿望非但不稍减,反而愈加强烈。所以一旦获得实现这种理想的机会后,就不肯放过。这在土地改革中看得十分清楚。在土地改革中,不仅分到土地的农民兴高采烈,就是走出农村在城镇从事各种职业者,也想到农村去获得一份土地。在费孝通的调查中,1949—1979年的30年间,苏南城镇人口的下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 1950年的土改前后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江浙两地,因为分得田地,许多原先已经脱离土地,以工商手工业为生的家庭又重返家乡,分得一块田地。”江苏昆山市周庄附近的铜罗镇,“1951年土改时为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下乡务农。”[9](P161-162) 这种行为,除了说明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外,也说明农民想和别人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是均平的心理。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满足了农民这种均平的心理。
对于农民来说,“均平”和“求富”有时是矛盾的。“均平”是将别人的拿来均分,而“求富”是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一旦自己不如人或无法满足自己“求富”的心理后,他们最希望的是“均平”。这一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凸现得更加清楚。从农民自身来说,合作化比较积极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中经济状况不如人者居多。这是由于土地改革虽然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如前所述,这种状况还有所发展。这样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就把合作化当成重新分配资源的手段。黄宗智对松江县薛家埭村的研究发现,土改时分得了一些远离水道的零星土地的农民,合作化的积极性比其他人要高。[10] (P169-170) 东北局在1950年1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经济条件较差的,仍有农业社会主义平均思想,有的人欠了别人600斤粮食,还说:我虽欠你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走入‘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买马,他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11](P23)表现出对“均平”向往的心理。山西忻县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12](P107)薄一波后来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13](P119)三 个体与参加互助合作
这是一对矛盾。当时的农民的确存在着这样两种心理,而这两种心理存在于不同的农民群体中。从总的情况来看,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占主导地位。
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是与发财求富联系在一起的。东北局在195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这种状况:“在农民群众中:少数经济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11]报告将这种现象说得很清楚。但是笔者以为,有一点不很准确。那就是报告中说少数人要求单干。实际上,中农以上者多数都要求单干以发家,而东北的情况到1951年中农占了多数,所以是多数人要求单干。就是贫农中的一些人,也是愿意单干的。这就出现了在互助合作的初期的强迫成立的互助组一有适当条件就解散的事。中共山西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甚至导致中央上层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意见中,对于山西的情况作了说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14](P4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几十年后,薄一波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土地改革后,“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为数当时并不很多,而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13](P365)
互助合作也是部分农民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农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然后再单干。有些人愿意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地就种不上。但他们有些人希望在变工组把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现单干”。[11]另一类是由于贫困,坚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除去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外,有互助合作的人都是土地改革后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曾被毛泽东称为“五亿农民的方向”的河北省平安县南王庄贫农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入社的原因都是因为贫困。王玉坤在解放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农,土地改革后,有十几亩地,可是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也只有半头,生产搞不好,生活不富裕。王小其土改后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呢,只有一条牛腿。他年纪又小,不会种地,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王小庞在土地改革后因为缺这少那,经营不好。所以他们坚决要求互助合作。[15]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入社农民的状况,及其入社的心理原因。
那么,曾经被党和政府估计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以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互助合作。这种状态就是互助组阶段。因为互助组既保证了农民的个体经济,又可以使农民互相调剂,互相帮助。并且这种互助组是自愿参加,不是强迫,农民有互助的自由,也有不互助的自由。这就满足了农民两方面的要求。不急于过渡到初级社、高级社,情况会好一些。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6](P316)
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裹进了公有制的行列。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并非出于自愿。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反抗,甚至没起什么波澜,怎样理解农民的这种状况呢?
第一,农民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心理而加入合作社。如前所述,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尤其是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与拥护。虽然农民对基层干部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是信任的,对于党的指示,他们是执行的。正如有的农民说的:“毛主席总冒哄过人,这回叫走新道路也冒得错,走就走吧!”[17]有的干部也注意到这一点:“只要打起毛主席的旗帜,一切都会顺利”。[18](P230)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大发展,又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农民听到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来,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话没错’”。[19](P340)
第二,经济的动机使部分人愿意参加合作组织。这就是前面说的部分及经济状况不佳者想利用互助合作再一次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是“均平”心理的作用。
第三,政策和措施上的导向。如在东北,1950年春高岗就宣布5条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也是歧视单干的政策,在农贷、新式农具、良种及劳模奖励的发放和购买一律优待变工组,松江省的一些地区规定对单干户不贷款、不贷粮、不贷农具,合作社也不卖给东西。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在征粮方面制定不利于单干户的政策。在浙江农村,干部们为了鼓励农民入社,公开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而邓子恢当年就知道中农哭哭啼啼要求入社是为了少卖粮,而不是出于什么“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3](P331)基层组织有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有的组织开会,“不报名不散会”,有的采取“订合同按指印”的办法,限制农民退社,有的说“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有的威胁退社的农民:“你退社影响别人,咱村办不起社责任放在你头上”。[20](P202)
第四,上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上层。土地改革时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已经使富农甚至中农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了,而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时,又强调“树立贫农的优势”,与地主富农斗争,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按语中,又说:“在富裕中农的后边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而贫苦农民和富裕中农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21](P525)斗争地主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中农岂敢抗拒入社。“至于原本已经威风扫地的地主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富农,能同意他们入社就是一种政治待遇,岂能再有讨价还价之理?”[9](P170)
农民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不能忽视农民,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的心理。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和农民的心理相吻合的。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则和农民的心理不完全一致。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是信赖的,对社会主义是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的,同时又对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家致富有着更迫切的要求与愿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考虑农民的这种心理,从而制定出既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同时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措施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速度、模式等问题上对农民心理的考虑是不够的,是有教训的。
[1]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东北农村经济的新情况》,《人民日报》[N]1951年3月21日。
[5]《四川省资中县长山村经济发展和阶级变化情况调查》,《当代农业合作化》编辑室: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6]《山西武乡农村考察》,见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陈和平、李景岗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
[7]《山西省忻县地委关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的调查报告(摘要)》,史敬棠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Z]。
[8]李准小说集:《李双双小传》[Z],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9]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162页。
[1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M],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9-170页。
[11]《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节选)》,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第23页。
[12]《山西忻县地委关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的调查报告》,《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第107页。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14]《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
[15] 李凯、庆琛:《五亿农民的方向》,《人民日报》[N],1955年11月28日。
[16]《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农村工作通讯》[J],1954年第9期。
[18]《广西省委统战部关于三江侗族自治区目前互助合作运动与今后工作的意见》,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
[19]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史敬棠等主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Z]。
[20]《中共长治地委农村工作报告》,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Z]。
[21]《〈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
下一篇:当代中国农民身份制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