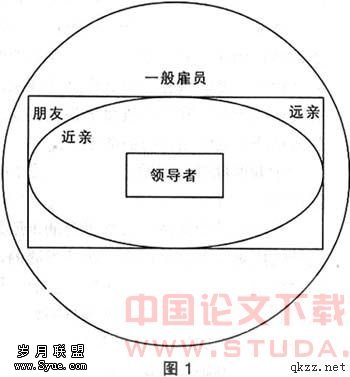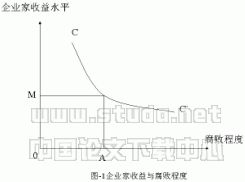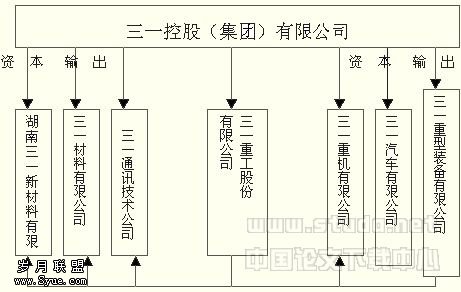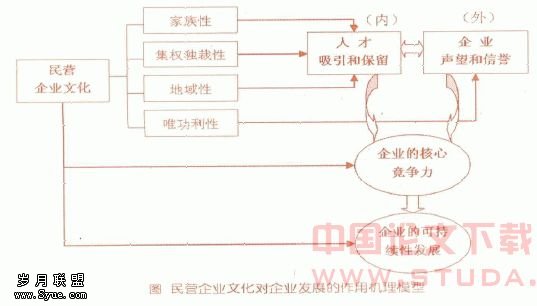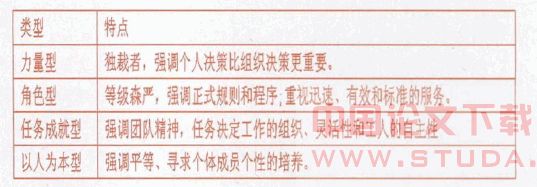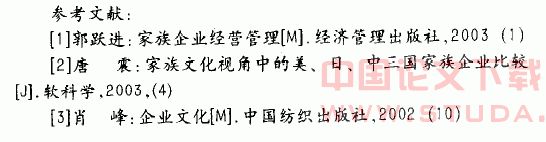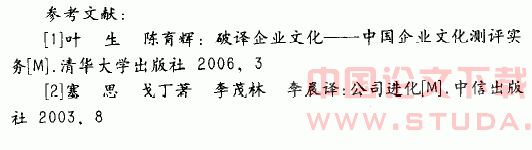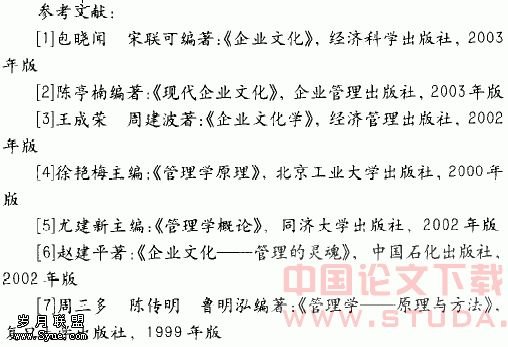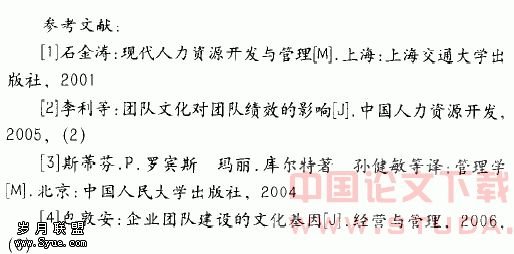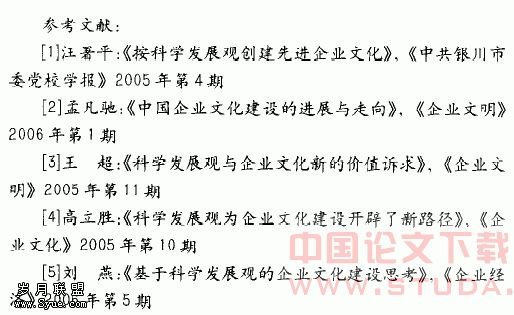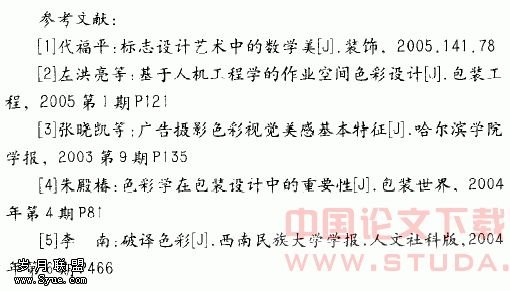高考,精英摆脱身份忧虑的需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30
[关健词]高考需要 精英 身份忧虑
教育是人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从农业社会的男耕女织到知识时代的电脑培训,人们在不同生理阶段通过理解各种教育性符号,如语言、行为、规则、理念,增强自身生存能力的同时推动着社会的,政府、、家庭等诸多社会单元也在这一过程中的逐渐完善。如此,“受教育”成为社会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的需要在精英导向的社会应当是可以解释的。以高级人才选拔制度为看精英的需要,当20世纪50、60年代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区别对待”体系在世界范围高等教育民主化运动中建立并开始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升入大学的竞争中有了优先权,即使他们的正式资格不如非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1949年之前的中国,绝大多数高校学生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和富裕家庭,1952年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达到20.5%;1958年55.28%;1965年则为71.2%。其次是改革前的农民问题,社会分层在再分配体制基础上建构,社会成员首先被划归为农与非农两种身份,其本质是国家依靠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来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于两种身份群体之间存在商品粮供应、正式工作、稳定收入以及相应一整套福利政策的天壤之别,这种分层机制下的高等教育,对于农业人口来说,是其能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机会,只要能升学,就意味着身份的质变。再者看文革后的高考人员组成,报道指出“就社会阶层而言,高考对于文革中失去权力的干部阶层和几十年来被出身成份压在底层的家庭更有一种解放感。考生们怀着一种奇特的感恩意识,大多数考生对能否考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首先在意的是自己终于得到了参加竞争的资格,这种心态为后人所难以想象……”最后,比较近的,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2004年的统计资料,43所重点高校若干阶层子女的分布如下:干部、管理人员15.3%;专业技术人员16.6%;工人13.4%;农民27.3%。出身于工农家庭的高校学生逐渐减少,各种上层社会集团子弟大量挤占了高等教育的名额,社会资本分配对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可见一斑。在精英政治深刻干预下的中国社会,精英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要现实存在,并且这种需要不仅体现在高考资格上更表现于对高考选拔中选择权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高考需要呢?我国高考与身份悠远的紧密联系作用匪浅。?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对教育成果尤其是对人的教育评价仍处在德才兼备的框架中,孔子关于庸人、士、君子、贤才、大圣的五等人体系依然潜移默化地指导着育人的具体行为。“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孔子的贤能标准是品德与才能的结合,缺一不可。配套官吏人才的选拔制度,“德才兼备”更是古今荐拔人才的统一标准和基本原则。在中国人才选拔史上举足轻重的科举,对“德”的考查主要考核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伴随着封建等级意识在封建统治下植入中国社会,读书敛“才”做“德才兼备的人”成为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有效途径,“八股文”时期尤为如此。两套系统交互作用,无形与有形相辅相成,在“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案例中比比皆是。贤者的才学当为社会做出贡献,一在本身具备这样的贡献资源,二在这种贡献本身已被视为一种大义处在个人需要的高层。把“出仕”作为义务来执行,改变身价更要接受评价才符合社会对贤者的期待。
其实,这样的社会流动理论上并不存在越轨类问题,但实际操作中“不正常高考”的事件却屡屡发生。自199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战略调整,至2002年,我国各类高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而这个数据在2000年还是1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3)与此同时,仍有92.8%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44%的家长还希望孩子读博士,高校人数增加过快正映射了高考选拔的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以杨东平教授在北京理工大学的调查为例,2003级本科生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占41.6%,农民家庭10.6%、工人18.1%,对比研究生阶段前者占41.6%和博士生阶段41.3%,我们看到,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在获得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仍保持着高度的“受教育”热情,并不可避免地负面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种由上层主导、持续积累的社会流动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身份忧虑。何谓身份忧虑?即由于社会分层不稳定或存在社会理解中的分层不稳定,造成人们对于现有身份的不确定以及对已有身份固定性的担忧。比较普遍的表现是社会流动上行拥挤。原因何在?首先从文化层面解释,这样的身份忧虑源于对身份评价体系历史变革的不适应,这有中国特色的体现但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俄国等曾经接受血统制统治而在今天建立起新型体系的国家都存在这样的社会流动问题。以美国为参照,无论是被当作老牌WASP贵族的五月花号清教徒后代,还是关于肯尼迪家族童话般的贵族渲染,都体现了形式上已经脱离女王统治的美国人心理上对于身份排列的忧虑。人人都想往上爬,急于在各种社会变革中找到处于“最高位的人”好顺次排列等级,各式符合了小众社会心理的“俱乐部”,知识性、性、情趣性的等等,更多带给忧虑中美国人的是相对固定的暂时身份。比起至今只有200年历史的美国人,经历了上千年血统制排位的中国人现也在不同程度上寻找或建立着固定身份的支架,面对瞬息万变的评价标准,产生身份忧虑不是偶然的,并且也不是可以超越历史而能克服的,它有缓慢发展的过程。其次,从角度解释,这样的身份忧虑也是经济分配不规则循环的衍生物。附着在身份标志上的社会资源随着身份变化而分流,人格化体制对于人格魅力的强调也引发了评价魅力和运用魅力的问题,魅力直接决定着经济生活质量,经济生活条件又反过来影响魅力的持久性,这在政治领导体系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样也是国际性的问题,如美国的总统选举和中国的村官问题。而高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级人才评价体系无论在合法性还是社会认可度上对于缓解这种身份忧虑都有着深刻的历史优势,高等教育背景中的身份被固定在了继成制度和社会评价上。
而为什么精英会有更多高考需要呢?客观上是精英政治下的话语权和利益链条决定的,精英更有可能在既有体制中表达和综合这种教育需要;主观上中国精英特殊的使命感,即一种为民请命的大义,综合了精英的身份忧虑推动了精英队伍的“高考”步伐,具体的讲,就是渴望保持“精英”身份贡献社会,这与儒家的“出仕”精神如出一辙。精英通过高考摆脱身份忧虑,即时存在也可以为现实所解释,只是社会理解上仍有障碍,但随着身份忧虑问题越来越多地为社会所承认,精英影响社会公平的问题逐渐受到来自体制的控制,高考自身逐步改革,相信这种“摆脱”的心理会渐渐淡化,中国教育的本位之路也将渐行平坦。
上一篇:胜利油田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下一篇:浅谈如何开展和谐企业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