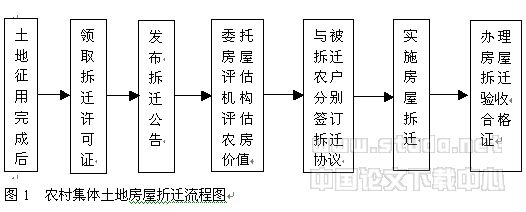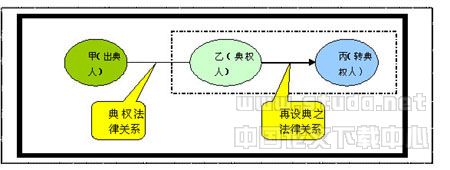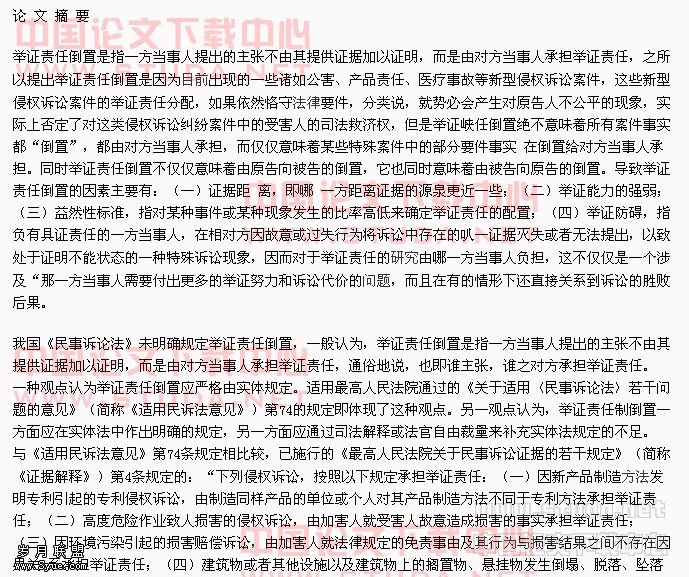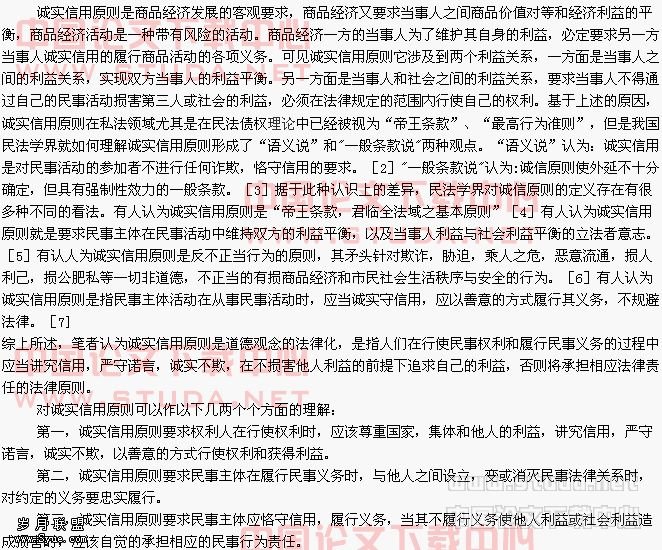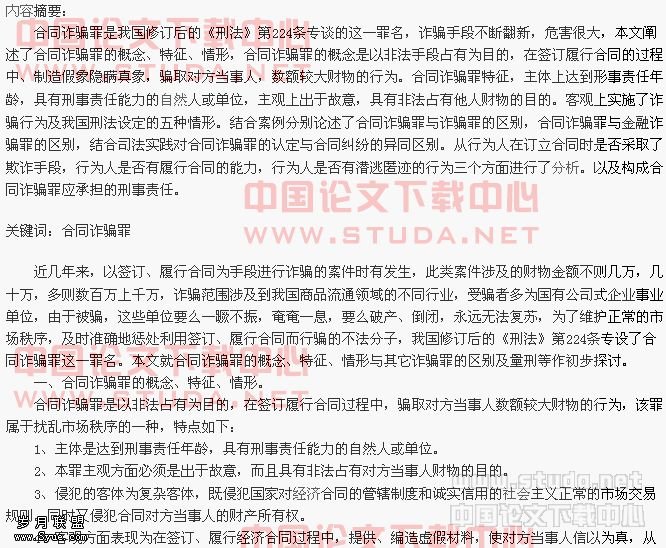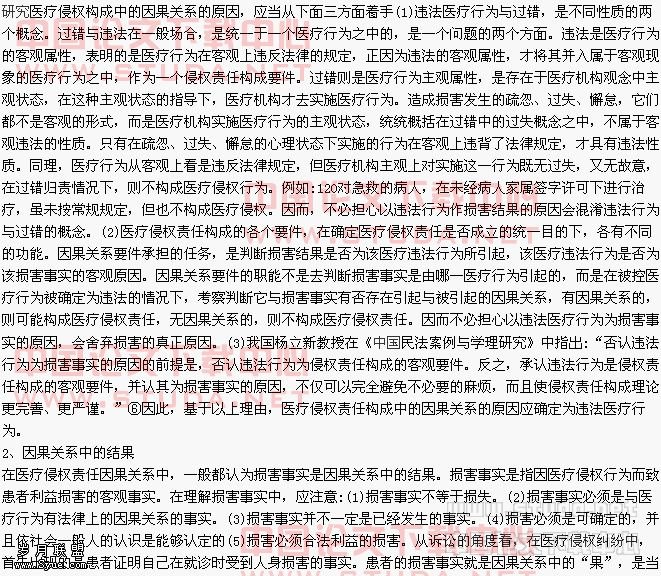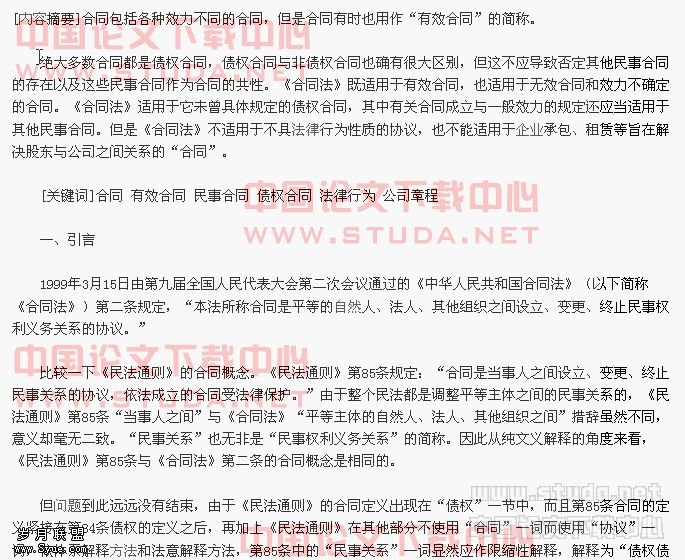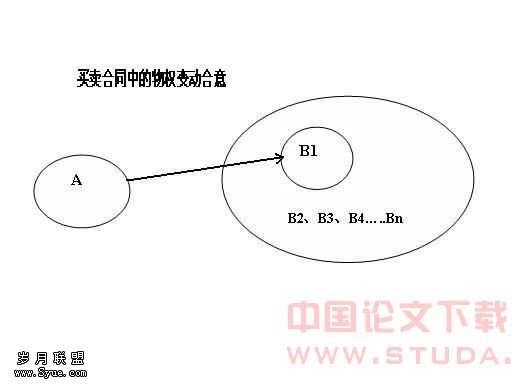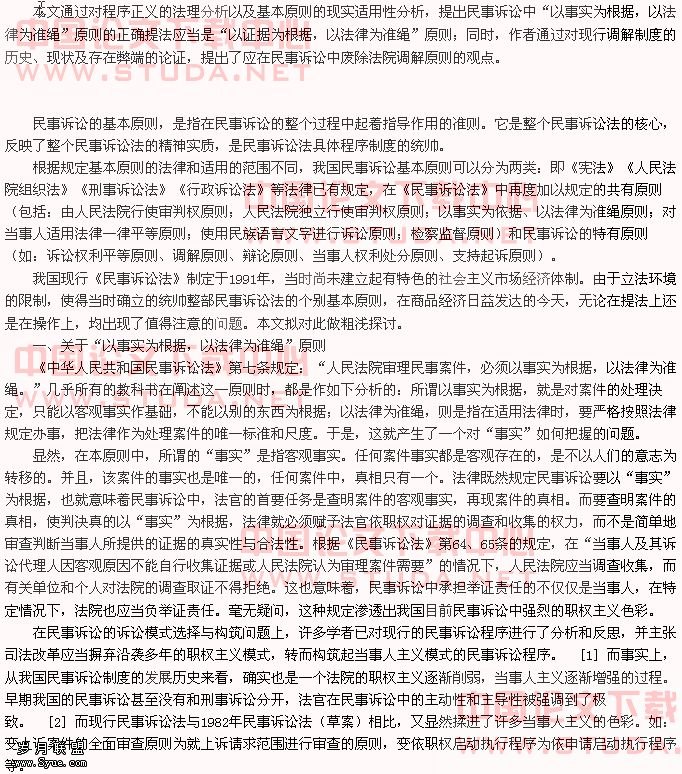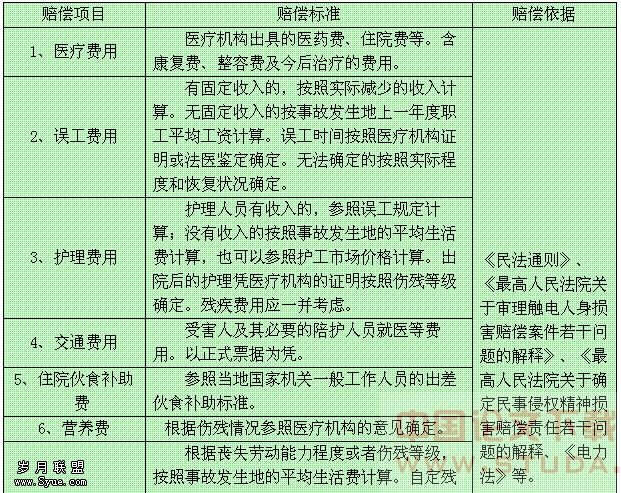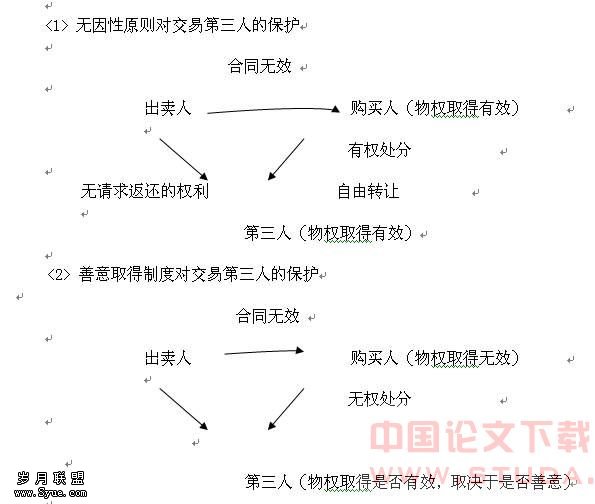事实编撰物著作权保护之实证分析
关键词: 著作权/事实编撰物/独创性/Feist 案
内容提要: 事实编撰物的著作权问题主要牵涉到对作品独创性的界定。美国Feist 案非常具有代表性。美国最高法院不仅强调了一般性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要求,而且强调了事实编撰物一类的事实性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要求。对事实性质作品著作权性质的否认表明了其对作者未来创作材料保障的关注。在事实编撰物这类案件中,法院需要解决的是对事实的编撰物中对于信息的保护和坚持信息是与其他作品相关的公共财产的观点之间的冲突。
在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中,事实编撰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对其独创性的认识和判断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议。本文拟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对事实编撰物著作权保护进行实证分析。
一、事实编撰物在司法实践中的概况
著作权法中公共领域在国外著作权司法判例中的发展经过了一个过程。在这些判例中,最明显的是法院逐渐否定了思想、方法、制度、普通的角色、情节和场面以及(有时) 事实的著作权保护,甚至这些东西是直接地从原告的作品中复制时,原因是如果对它们授予著作权的话将创制对创造性作品基本表达性材料的不适当垄断,并且人们不能接近构成社会大厦的基本的成分,表达自由将会受到威胁。
除了著作权法中作品中被表达的思想外,著作权法也充分考虑到上述方法、制度、普通的角色、情节和场面以及(有时) 事实,以及风格,或者任何“制造或者建构的方法和原理”成为公共领域。成为公共领域的因素在不同性质的作品中有不同的体现。以文学作品为例,这类作品的一些传统方面被否认著作权保护,如戏剧的场景、主题、通常发生的事件。当法院考虑到案件中原告的主张威胁到后续作者创作的原材料时,调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在确立著作权法的公共领域方面,对案件中牵涉到的事实不予著作权保护在判例法中的发展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1]。在今天的著作权理论和司法实践看来,作品中负载的“事实”没有著作权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在1919 年的Myers v. Mail & Express Co. ,36 C. O. Bull . 478 (S. D. N. Y. 1919) ;Kennerley v. Simonds , 247 F. 822 (S.D.N. Y. 1917) .案件判决之前,事实本身的著作权问题并没有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在该案中,Learned Hand 法官提出了以下观点:记录在历史作品中的事实被贡献给公众,并且可以被后来的作者自由地使用[2]。当然,在此之前,对于像新闻这类作品不给予著作权保护,无论是法院还是知识产权学者都存在一致的看法,主要是从新闻的公共领域地位来论证事实或者信息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的[3]。只是即使是在1919 年的上述判例产生后,对著作权名下事实保护问题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法院会高度重视创造性资料的公共领域资料的性质[4]。不仅如此,法院开始重视原告作为事实编撰物的作者在事实编撰物中付出的劳动,并主张禁止被告对该事实编撰物进行复制。例如,在Jewelers’Circular Publishing Co. v. Keystone Publishing Co. 案件中,Hand 法官在附带意见中指出,事实性质名录的作者无权从竞争性的名录中复制它的信息[5]。在该案件的上诉中,第二巡回法院认定从有著作权的名录中的复制本身是著作权侵权[6]。在1924 年的Produce ReporterCo. v. Fruit Produce Rating Agency 案[7]中,法院主张后来的编辑者被禁止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名录,他可以自由地编辑出版相同的事实编撰物的条件是他通过从已经存在的资源中第一个选择那些事实。可以认为,对于在编撰事实时付出了劳动的事实性质的作品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竞争观念的考虑。在这方面,十九世纪美国的很多判例遵循了英国判例的观点,即保护事实编撰物免受后来的竞争者使用,特别是在名录一类案件中,原告没有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情况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考虑事实不受保护。在名录案件中,法院主张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使用了原告的名录作为自己的最初的资源,法院将不需要考虑被复制材料的著作权性而直接认定被告构成了著作权侵权[8]。在这些案件中,作者主张在资料中的所有权,而他们并不能证明这些东西是他们最初的原创的,而只是能证明在编撰这些名录时投入了自己的劳动。法院考虑更多的是著作权表达的相似性而不是不受保护的情节、主题、场景或者事实[9]。
二、典型判例研讨:美国Feist 案
涉及到事实编撰物的著作权问题,美国Feist 案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下面不妨进一步做出分析。在Feist 案中,一定地区的所有电话按字母顺序的列表不被认为符合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的条件,尽管该作品具有商业上的重要性,并且在作品中投入了辛劳、投资和组织安排。该案件排除了仅通过选择编排构成独创性汇编作品的可能。换言之,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调用了平衡方法的观点,基于电话薄缺乏足够的独创性的理由而否认了对电话薄的著作权保护,认为电话薄中按照字母顺序组织人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没有著作权性,原因是生产者没有足够的创造性来使其成为原创的东西。该案基本案情如下:Feist 使用了乡村电话公司4935 条记录,其中相同复制的达到1309 条之多。另外,Feist 还复制了乡村电话服务公司设陷阱的条目中的4 个。这里的设陷阱条目是指原告为侦察未授权的侵权者而在电话薄中有意列举的一些错误的信息。这些错误信息具有设陷阱作用,它们被称为设陷阱条目。原告Rual 起诉被告Feist 侵权后,美国地区法院和第十巡回法院都认可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被最高法院推翻。最高法院判决表明了对独创性水平要求的提高,兼容了欧洲大陆法系的较高创造性标准——欧洲学者认为对编撰物的投资进行适当的鼓励是必要的,但著作权不能存在于电视节目表之类的列表中,因为它们是非秘密的、非革新的,它们仅仅是简单的信息组合。
在Feist Publications ,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案[10]中,美国最高法院不仅强调了一般性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要求,而且强调了事实编撰物一类的事实性作品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要求。
法院认为,事实不是起源于那些发现了它的人,因而本身不能满足独创性要求。事实是内在地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除了我们对关于事实的经验外,它是独立存在于世界的。事实性编撰物享有著作权的条件是在事实的选择或者编排上具有独创性, 而其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也限于实际的选择或编排。就该案所涉及的电话薄来说,由于它只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数据收集的产物,缺乏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要件,因而不能获得著作权。尽管法院承认将来事实编撰物性质的作品可以依“额头出汗”原则获得较弱的保护, 在该案中法院还是放弃了以“额头出汗”标准衡量作品的独创性,而是明确主张需要具有最低限度的受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水平。就该案来说,法院认为独创性只是需要作者独立地作出选择和安排,而这展示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创造性[11]。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原有判决的原因是,强调作品创作中投入的创造性劳动,而不拘泥于额头出汗原则。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著作权应当仅仅及于原创的作品,并且在思想的创造力中能够找到其存在的基础。被保护的创作物应当是智力劳动的果实⋯⋯[12]。在该案中,法官O’Connor 指出,“没有人能够对事实主张独创性这是因为事实不具有作品原创的特征。这种区别就像创造和发现的区别。第一个发现和报告一个事实的人没有创造一个事实。他只是发现了所存在的东西。他继续留意了公共领域,把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事实与像、历史和一天的新闻等没有著作权性的事实材料做了比较”。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决显然是认为原告作品缺乏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的独创性或者说原创性,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额头出汗原则方面的考虑而重视像投入了一定时间、辛劳和金钱而产生的电话号薄之类事实编撰物的社会价值。在该案中,法官引用了1879 年的案子来否认对未授权的编撰“事实”的使用构成著作权侵权,扩充到了整个财产制度的普通法基础。“事实不体现创作行为的最初来源。这种区别是在创造和发现之间的”。[13]法院强调事实没有著作权性是因为它们没有独创性。Feist 案在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与美国后来对数据库所有权的讨论相关。
Feist 案后,学者和实务界人士仍然热衷于就与该案件相关的著作权问题进行探讨。如有的学者从“作者推理”的角度分析,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是基于作者推理的原则判决该案件的,而这却会阻止该案件所建立的政策基础。如简单的功利主义分析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导致著作权保护的社会成本是否会被无效力地浪费了。然而,该案件的判决仅仅是基于作品受到著作权保护需要原创性,而电话薄没有。换言之,在将事实改造时,没有“作者”的渗入,只有进行劳动的编辑者。还有的评论人士认为:著作权意在鼓励创造,促进知识产品的繁荣,但有时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财产所有权对“原始资源”的贬低体现于: (1) 集中于作者所借用的先前的材料的独创性,而不是所有的原创作品受这种“原始资料”的影响的程度; (2) 允许这种原创作者就原始资料的加工获得财产权,这样一来可能否定后来的创造者对这种材料的接近。因此,随着有天份的创造者将“创造性的原创”渗入到编撰物到将纯粹的事实改造为著作权作品,就可以鼓励这种事实的其他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寻求一定的创造性的方式将自己改造为作者。[14]
还有的学者主张:美国最高法院的假定即授予思想的著作权保护将排除后续作者依赖于那些事实是错误的。著作权保护不应阻止后续的作者使用事实;它只是需要为了使用而应付费。可以在该案件中的事实表明,信息的保护确实导致了对于传播的限制,因为被告为了获得信息可能需要与原告谈判许可证事宜,而谈判有可能破裂。但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即使由于单边垄断问题而使得谈判破裂,它也不能为否认对事实的保护提供正当性,因为单边垄断总是对被著作权保护或者是其他形式保护的作品任何一方面的一种可能性。在对事实许可时谈判破裂有可能发生,它没有为区分事实与表达提供任何一个理由。尽管最高法院总是主张事实和思想是在同一水平上,并且事实是不能获得著作权的,在Feist案件以前的与事实中的著作权有关的是没有的。这可以通过这一事实加以说明,即Feist 看到谈判是合适的,并且在每十一个中有十个为使用信息而付费,根据最高法院的最后的判决,是能够自由地占有的。当法院的判决确实看起来是建立在创作的建筑材料理论而不是更一般的平衡理论上时,直觉认为基于平衡的方法,这一判决是不可辩护的。事实作品在自由搭便车方面也是值得怀疑的。单独表达的价值将允许在文学作品像小说的作者收回他的成本,这是似是而非的,而在事实作品中就不同了,因为事实作品的价值的很大的一部分将独立于作品中所包含的事实被表达的的方式。,事实的存在构成了作品价值的一部分,但与小说和戏剧相比,同一事实中的不同的表达可能是原创作品的几乎完全的替代品。
该学者还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很明显地不限于对事实作出判决,而是试图一般地适用到事实作品中。相关的问题是,不是著作权保护是否是在Feist 案件中的情况一样成为产生信息的一个必要手段,而是甚至在没有著作权保护的情况下是否能够为生产事实作品提供足够的激励。法院明显地将其看成是一个学理问题,因为在创造和发现之间没有提供一个政策界限。然而,它确实暗示了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在事实是世界中的客观的映象的层面上,一个特定的事实作品的独立创造是可能的。在其运用财产权分析方法所进行的讨论中,独立创造的可能性比起将事实和思想作为未来作品的建筑材料要相关得多。但当事实是在那一独立创造中的不可能的表达时,它们不可能是思想,这在于这种独立的创造更加容易地被证明,因为事实作品的创造需要提供充分证据的努力。只要能可靠地确认独立的创造,对事实而不是对原创性表达的负重损失的问题要小。抽象的问题,即证明相似性的困难,不是对于事实的关注,而是因为这种事实和区别至少是与不折不扣的表达一样所客观决定的。所以,在独立创造是可能的情况的含义上事实是原创的,财产权分析表明独创性只是为了方便证实复制的手段。相似性问题可能出现了,因为独立的创造没有为否认保护提供正当性——如果独立的创造通过直接的证据能够获得的话。这样,在财产权的分析中,Feist 案件的判决有误,并且更加关键的是Feist 案件确立了规则,原则上没有理由反对立法设计要将对事实延伸到著作权类型的保护[15]。
Feist 案将作者身份和原创性纳入到当代的著作权法,该案的焦点无疑集中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独创性要件及其界定问题。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虽然没有十分明确地提出著作权法中的公共领域问题,但对事实性质作品著作权性质的否认表明了其对作者未来创作材料保障的关注。最高法院尽管没有确认复杂的社会过程和环境使得“事实”能够被创造、流通、使用,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被重新使用,但它仍然充分认识到了在公有领域中未受到保护的事实作为未来的创造者的资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将电话薄的名单列为公有领域的东西。在该案后,在知识产权的其他领域,如专利权和商标权领域,对未被占有的原始资料与原创身份的关系的研究也不断受重视。但该案可能最终缩小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共领域的观点则似难以成立,因为该案对从公共领域进入私有领域的条件不是放松了而是从严了。
从Feist 案后的一些案件看,至少在媒体的传统形式上,法院对事实作品提出了一些最低限度保护水平的主张。如在Lipton v. Nature Co.[16]案中,法院肯定了对术语编撰物的著作权主张。在CCC Info.Servs. , Inc. v. Maclean Hunter Mkt . Reports[17]案中,法院裁决对与使用过的小车有关的信息进行编撰的事实性作品足以构成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独创性,并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Feist 案中提出的规则不是要为独创性要件构筑一个更高的门槛。还如Mason v. Montgomery Data , Inc. 案[18]牵涉到地图的独创性问题,法院认为地图具有足够的原创,因而受著作权保护[19]。法院在其他的地方指出了需要维持最低限制的保护的独创性的水平。
可以看出,在事实编撰物这类案件中,法院需要解决的是对事实的编撰物中对于信息的保护和坚持信息是与其他作品相关的公共财产的观点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像电话薄一类本身所包含的是没有被创造的事实、信息或资源,而不能被某一个人所垄断,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在形成事实编撰物这类特定的作品的过程中,创造者需要付出辛劳、投资与时间。为解决这一冲突,一些相关概念和原理被调用或提出来了。其中像“作者原创”、“作者推理”等概念或原理就是如此。
通过作者原创概念的引入,著作权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垄断与自由接近以及垄断与财产等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对于在更大的层面上解决对没有被占有的东西赋予财产权,作者原创的概念也能发挥作用。这里提到的作者原创与独创性意义是基本相同的。在作者原创的基础之上“, 作者推理”原理可以进一步用于说明事实编撰物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作者在多大的程度和怎样地将个人特性渗入到它们中的,以及他们是怎样将某种原材料性质的东西改造成独创性的东西,可以用于证明事实编撰物作者是否有足够的创造性因素的渗入。当认为这种渗入具有足够的创造性时,对事实编撰物倾向于授予著作权。进一步扩大“作者推理”原理,对那些其他方面的不能被个人占有或者没有被个人占有的公有领域的东西,越来越在人类社会中被私有化,如赋予人类基因以专利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作者推理的场合,通常存在一个假定前提,即赋予这些东西以专有权,有利于鼓励和报偿最初的创造者,从而最终有利于丰富不断增长的公共领域。
在当代,事实编撰物受到著作权保护已得到各国著作权立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肯定,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就是典型的例子。上面介绍与讨论的Feist 案,美国最高法院明确地裁决美国著作权法不保护包含在数据库本身中的信息。[20]但是,数据库本身中的信息不受保护并不意味着数据库作为一个整体不受著作权保护。实际上,数据库著作权保护已经形成一种国际通例。尽管在日内瓦的知识产权谈判中,没有达成有关数据库保护的条约,数据库应当给予什么样的保护水平也存在争论,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却是已达成共识的。在欧盟,根据欧盟关于数据库保护的指令的规定,数据库还可以受到特殊权利之保护。在美国,与数据库保护相关的法案也不少见。如信息收集反盗版法(CIAA)“禁止任何人抽取或者使用信息收集物中的全部或者实质性部分,如果该信息的收集或者维持需要实质性的金钱投资或者其他的资源,而使用将会对包含信息收集物的产品潜在或实际市场的损害的话”。当然,对于非营利性质的、和研究、新闻报道等目的利用数据库的行为,该法给予了一定便利。还如消费者和投资者接近信息法(H. R. 1858)规定的禁止范围比CIAA 明显要小。但总体上,试图通过某一类具体的案例为公共领域提供整体的原理比较困难。通常的模式是,当法院感到有必要保护被告代表的使用者利益时,会调用公共领域的概念。
确实,在考虑到对作为被告的使用者利益的合法保护时,法院需要重视作品中包含或体现的思想、主题、情节、事实,特别是其表达的思想。一般地说,很难确认作者创作灵感、思想的最初来源,也不可能证明在任何意义上的来源,也无力追踪和证明留存在公共领域中的思想的产生脉络。作者本人也很难确认其灵感的来源,而这与作品的创作具有必然联系。如果赋予作者对像思想、主题、情节、事实,特别是其表达的思想这样的创作的基本的建筑材料以专有权,那么该作者之后的所有作者接近这些基本的建筑材料都将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会使著作权法所要实现的宗旨受到严重损害。涉及到事实性质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可以认为原创作品的一些方面在忽略其来源的情况下被后来的作者所创作的作品所吸收和占有,而不必追踪其来源。思想、信息、简单的情节、简短的单词、主题、场景等都具有这一特征。事实上,要追踪其来源也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使我们在这种东西中授予专有权,而不要求权利人提供重要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所有权的主张。通过选择赋予著作权的形式,包含思想、信息、简单的情节、简短的单词、主题、场景等在内的作品被包容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专有权的范围之内,只是这些来自于公共领域的东西仍然处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即他人仍然可以自由地利用而不受专有权的控制。选择赋予著作权的形式不要求说明获得专有权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重视专有权而说明思想、信息、简单的情节、简短的单词、主题、场景等被赋予专有权提供证据是很难的。但是,为了使这样一种包含了他人的或公共领域素材的作品获得的著作权不被挑刺,我们留下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依赖于私人财产主张而可以被自由地吸收,甚至能够确定最初的来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当然,在不能够自由吸收的情况下,将著作权作品中受保护因素与不被保护的因素加以区分是缺乏充分理由的。
注释:
[1] 以下对关于“事实”著作权问题的分析,参看Jessica Litman , The Public Domain , 39 Emory L. J . 990291 (5) 。
[2] 后来在一个涉及到竞争性的珠宝商的名录案件中,Hand 法官重复了他的关于事实本身是公有财产的观点。参看Jewelers’CircularPublishing Co. v. Keystone Publishing Co. , 274 F. 932 , 935 (S. D. N. Y. 1921) , aff’d , 281 F. 83 (2d Cir. ) , cert . denied , 259 U. S. 581(1922) .
[3] American Trotting Register Ass’n v. Gocher , 70 F. 237 (C. C. N. D. Ohio 1895) ; List Publishing Co. v. Keller , 30 F. 772 (C. C. S. D. N. Y.1887) .
[4] Lurvey ,“Verifying”from Prior Directories ——“Fair Use”or Theft ?Delicate Distinctions in the Protection of Copyrighted Compilations , 13 BULL.COPYRIGHT SOC’YU. S. A. 271 , 282289 (1967) .
[5] Jewelers’, 274 F. at 935.
[6] Jewelers’, 281 F. at 92295.
[7] Produce Reporter Co. v. Fruit Produce Rating Agency , 1 F. 2d 58 (N. D. Ill . 1924) .
[8] Leon v. Pacific Tel . & Tel . Co. , 91 F. 2d 484 (9th Cir. 1937) .
[9] Caruthers v. R. K. O. Radio Pictures , Inc. , 20 F. Supp. 906 (S. D. N. Y. 1937) ; Echevarria v. Warner Bros. Pictures , Inc. , 12 F. Supp. 632(S. D. Cal . 1935) .
[10] 499 U. S. 340 (1991) .
[11] Feist , 499 U. S. at 358. 该法院引证了以下案件中提到的最低程度的创造性标准: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 188 U. S. 239(1903) (Holmes , J . ) .
[12] 499 U. S. 346 (1991) .
[13] Feist at 1288.
[14] Keith Aoki , Authors , Inventors and Trademark Owners : Priv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Public Domain(Part I) , 18 Columbia 2VLA Journal ofLaw &the Arts 4 (1993) .
[15] Norman Siebrasse , A Property Rights Theory of the Limits of Copyright ,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34 (2001) .
[16] 71 F. 3d 464 , 470 (2d Cir. 1995) .
[17]44 F. 3d 61 , 66 (2d Cir. 1994) .
[18] 967 F. 2d 135 (5th Cir. 1992) .
[19] 还可参看Dennis S. Karjala , Copyright in Electronic Maps , 35 JURIMETRICS J . 395 (1995) .
[20] 499 U. S. 340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