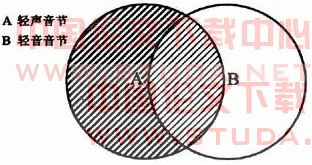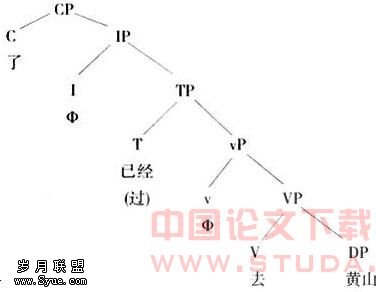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
众所周知,我中华先贤前辈遣词造句力求言简意赅,行文力求流畅洗练,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故而古代汉语中名词以单字为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与之对应之词有“人”、“民”、“族”、“类”、“部”、“种”等若干,而“民族”这一双字词,在古代汉语中的确是难觅踪迹。多年以来,诸多学者试图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处,但遍索经籍典册,却收效甚微。就学者而言,欲加深对民族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就必然要涉及到汉语“民族”一词的出处、涵义与用法问题,因此,搞清汉语“民族”一词之由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学者彭英明于汉代学者郑玄之《礼记注疏》中,发现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1)之语。但一览便知,此处“民族”二字虽前后连缀,但并未组成一个名词。与此同时,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专家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取得很多收获。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寻到出处。但终有斩获,他们在中国近代的书刊中,发现多处“民”、“族” 二字连用组成一词之情况,并将其最早出现时间确定为1882年王韬所撰之《洋务在用其所长》。王韬云:“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2)而真正具有当今“民族”含义之出处,当属梁启超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及能言之详尽焉”等语。(3)至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民族”之定义,则始于1903年梁启超撰《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德人布伦齐利的民族八大特质翻译引进之时。(4)由于长期搜寻未果,“‘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华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国民族学大家林耀华先生就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是“受日语的影响,日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我国又从日语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民族”词条综合当时的研究成果,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即伯伦知理,笔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6)我国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民族”之词条,其舶来身份似成定论。
至2001年,青年学者茹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茹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7)
茹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
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8)
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 、 “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与江东之汉族无疑。而所谓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改变,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中原华夏族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强调“夷夏之别”(9);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10),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虽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调和佛道两教之纷争,但实际上却是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抵制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11)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713—761年)之时,(12)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有可能也。
注释:
(1)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的初步考察》,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5页。
(2)载《洋务运动》第一册,第496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22页。
(3)梁启超:《东籍月旦》,载《梁任公全集》卷四,第209页、212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32、33页。
(4)见《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71-72页。转引自韩锦春、李毅夫编:《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理论室1985年印,第51页。
(5)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175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
(7) 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页。
(8)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第934页,《高逸传·顾欢传》。
(9) 《论语·八佾》,引自张以文《四书全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0)《孟子·滕文公上》,引自张以文《四书全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11)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第2页,《出版说明》。
(12)参见《道藏要籍选刊》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6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