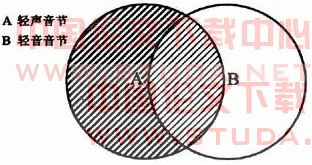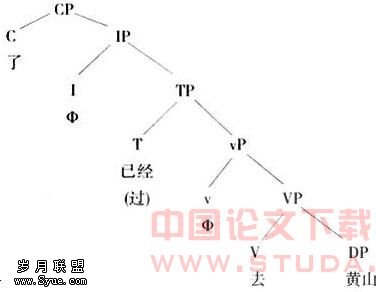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之反思
摘 要:面对长期以来结构主义等学派在发挥巨大积极作用同时又具有深刻消极影响的状况,当前的汉语词汇研究,最好能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走势,回到最为根本之处,开启多维视角而突出人与生存空间互动这一主要视角,确立多层目标而突出认识民族“人”这一最高目标,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认知—解释—文化—”这一基本思路。
关键词:汉语词汇;词汇研究;结构主义;
Abstract:For a long time,structuralism has played quite different parts in lexic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both active and inactive.At present,a better way out for Chinese lexical study i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alism and return to the most essential state.A multi-proportion view should be introduced wit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space of existence as the most primary.Besides,a hierarchy of goals should be set up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man” in the national mind as the highest.Finally,different approaches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cognition.explanation——culture——philosophy” as the most basic.
Key Words:Chinese lexicon;lexicological study;structuralism
在,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人,大都不会忘记,自上古以来,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中,在汉语的研究中,词汇研究如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发挥出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表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不能对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无动于衷。早在1990年,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就已明确指出:“从本世纪初叶起,在德·索绪尔的语言学说的影响下,语言学共时的、结构形式的研究成为潮流;语言学中的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都摒弃意义,将索绪尔所提出的成为语言符号一个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号,认为概念、意义属于实体范畴,而实体不是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东西。于是体现着‘实体’的词汇,被置于研究观察的视野之外。……心理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逐步强调意义分析对于句子生成规则的重要性,甚至将‘词汇’的分析作为一种基本规则列入生成语法规则系统之中,但是实际上只是临时零碎地对个别词作义素分析,以便在词语搭配上为句子语法规则提供语义选择的必要补充,并没有对整个词汇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1]2近来,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强调:“汉语研究的重点一直是语法,而词汇研究长期以来很少过问,一直是个薄弱点。似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有个别汉语词汇的著作问世,不过大都是参照苏联或西方国家的词汇学或词义学著作的理论和体系,加上汉语的一些例子写成的。……但遗憾的是,国外的理论往往离汉语的实际太远,解决不了汉语的不少实际问题。”(注:参看胡明扬为《词汇学词典学研究》所作的序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两位先生的论断,诚挚尖锐,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一种有力的激励。
当然,另一方面,最近20年来,中国许多汉语词汇研究者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引进推出,又有了丰富的收获。词汇研究朝着细致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专书研究、统计分析、语感测量等等新的方法不断运用,新的视角不断开拓,新的选题不断出现,新的学者不断显露头角。可是,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似乎仍然没有突破性的。
那么,面对长期以来结构主义等等学派在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深刻消极影响的状况,面对汉语词汇研究在古代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而在当代却已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从根本之处着力,推进汉语词汇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使之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呢?当然,这里所谓的“突破性发展”,并非说要在两三年内就“一鸣惊人”、“跃上一个新台阶”,而是说更新观念、扩大视野,从词汇是人所创造运用的、为人而创造运用的、人之所以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语音符号这一最为普通、最为根本的事实出发,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定势,实现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在现有基础上的新发展。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重大课题,需要群策群力地共同努力。隅见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回到根本处,开启多维视角而凸现人与生存空间互动这一主要视角,确立多层目标而突出认识人的本性与存在这一最高目标,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认知—解释—文化—哲学”这一基本思路,进行新的尝试性的汉语词汇研究。
一、开启多维视角中的主要视角
观察和研究汉语词汇,首先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汉语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对人而言的存在和对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贮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创造、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例如,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则或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外部关联,解剖词汇词义的微观结构或者把握词汇词义的宏观发展,对词汇系统存在的事实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写或者对词汇系统发挥的效应进行合理可信的综合释解,对特定专书与词典中的词汇词义进行静态的归纳或者对特定语境与文化中的词汇词义进行动态的考察,开展符号学、名称学的词汇研究或者开展社会学、文化学的词汇研究,编写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词典”或者编写特定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词典”,进行词汇的分类统计或者进行词汇的信息处理,等等。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维视角之中,有一种更为根本、更为主要、更为关键的视角应该重新开启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体察汉语词汇作为中介符号、象征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
如所周知,人类起源于动物,并且又和各种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理机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相应地又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都必然要受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的作用和影响,都能对于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进行感受和反应。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真正的现实就是由自己与其生存空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然而,正如符号哲学大师卡西尔论证的:在使自己适应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的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以“应对”外界刺激。“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33符号与一般动物也能掌握的信号、手势、宣泄情绪的喊叫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约定的约定性、表现形式与所代事物无必然关联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间上与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时间上超脱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够超越此地此时的具体情境以指称任何“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能够表达特定对象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人综合经验、增生经验、使经验得以表达和传承,进而促使人类创造和运用一种与所有动物完全不同的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
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语词符号无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灵便、最有普遍适用性的符号系统。这是因为:语词是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以语音为物质形式,以事物为指称对象,以意义为表达内容,具有层级性、系统性,以灵活组合,无须依附它物;语词是一种表达符号系统,它划分事物使之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而成为表达对象,它概括特征使之从事物中突显出来而转化为意义,它表达意义使之得到交流传播而不断增值。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交际方式,建立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交际方式,组成以语词符号为纽带的人类级别的社会组织;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思维方式,创造人类级别的思维成果;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并在抽象意义上思考那些关系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关系思维;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从混沌茫茫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别择出某些固定的成分进行专门研究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语词符号反思。正是在语词符号的作用下,人类逐渐改变了自身,发展了自身,得以在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创造和发展自己特有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为互动过程中的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以创造文化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注:参见高宣扬《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和权力运力》,载《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9页。)就人而言,他是只能凭借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认识、揭示和改造原有的生存空间以创建新的生存空间,他是运用也只能运用语词符号为前导并通过语词符号从事创造活动;就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而言,它们是通过也只能通过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进入人的视阈并向人表现自己的存在。这正是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正是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本体论意义之所在。尽管就“此地此时”的个别而言,人的生存空间是各自的、特定的,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有无数的形态与表现,但是就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总体而言,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却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的系统,其主要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我”的相同环节与线索。
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语词符号,是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而创造的,是作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而存在的,是在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造就其根本属性、发挥其主要功用、形成其发展规律的,是人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不可或缺的凭借。如果没有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就没有语词符号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更无所谓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以考察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动力、方式、结构、效应以及词汇的根本属性,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开拓主要视角,更新词汇观念,正本清源,把握关键,从以前未能着眼之处着眼,在以前未能提出问题之处提出问题,发现并强调以前不曾发现并强调的机制与规律、特性与功能。
譬如,《尔雅·释畜》记云:“回毛在膺,宜乘;在时后,减阳;在干,?方;在背,阙广”。显然,“宜乘”、“减阳”、“?方”、“阙广”四词的产生,是中华先民以回(旋)毛的位置为标准对马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结果。可是,这四个名词何以能在战国时代产生、却在两千年后消亡呢?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尔雅注》中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线索:“伯乐相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马”。由此可以想见,在上古时代中华先民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有重要的价值,是人的朋友,人们关注马、爱护马、寻找千里马,并由此发现了其旋毛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如此分类和命名,这四个名词也就有了自己形成的动力与方式。而在后来中华民族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不再具有往昔的价值与地位,人们不再重视其旋毛的位置,因而没有必要如此分类和呼名,这四个名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这里,隐含着汉语词汇形成或消亡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角度才能发现它、揭示它。
又如,面对古代汉语的常用名词“时”,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上古时期,中华先民既已在原初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月、年”诸词,可以标度时间之流,他们何以还要另造名词“时”以及“春、夏、秋、冬”诸词,来标度已被“日、月、年”诸词清晰标度过的时间之流呢?一当深入到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农耕生活文化中去就能发现,中华先民要协调农耕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而使之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顺利的发展,自然特别关注一年之中季节的存在和变化,因而划分季节,分别命名,并将季节总名为“时”,以便概括和交流关于季节的经验,将其引入民族文化系统。对此,《汉书·律历志》早有深刻的解释:“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因以天时。……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由此,我们就可以对其本义有着更为准确、更为深厚的理解,更好地分析其词义结构,发掘其文化意蕴;就可以对其引申规律有着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其引申言向,探求其引申效应。
二、确立多层目标中的最高目标
从当下的多方实际出发,确立适当的研究目标,不仅可以激励研究的志向,衡量研究的成果,而且能够明确研究的方向、启示研究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词汇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汉语词汇既在汉语系统中存在又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中存在,既是对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对人而言的存在,既是个体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既在贮存状态中存在,又在创造、运用状态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园”又是人居住的“家园”,所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复合性的、层次性的、人文性的。具体说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可以在于:由个体的而群体的而整体的,由个人的而人群的而社会的,由专书的而断代的而全史的,由词形的而词义的而词形、词义相结合的,由比拟命名的而分化孳乳的而复合衍生的。是探求本义的、追踪引申的,更是词义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是词汇系统内部规则的、词汇系统外部关联的,更是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是词汇对于现实事物之指称与表达的、词汇对于生存空间之切分与建构的,更是二者之共变关系的,是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轨迹之描写的、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机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发明的,等等。每一种研究目标,都有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局限,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相互的关联性,各种研究目标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并且有序地组合成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层研究目标之中,应该有一种更为高远、更有意义也更为关键的目标。卡西尔的经典著作《人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我们可以将这句名言稍作引申:认识自我应是一切人文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一切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我。如果失去了这一最高目标,一切人文科学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据与价值。那么,语言学、词汇学乃至汉语词汇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是否也应该也可以是“认识人自我”呢?在我看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然而,我们却又绝对不能据此而将语言符号仅仅视为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工具,更不能仅仅视为交际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而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激励下,人才能滋生出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才能在与交际之“你”的关系中产生出主体性,才能开始反思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过程,才能建构起理想并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从而发展出一种不断审视和更新生存空间的能力;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种存在物在分类概括中呈现出来并且变得可以理解,使整个世界在切分重组中呈现出来并且得到重构,人也因此而能拥有存在物、拥有世界并超越之。如果没有语词符号,一切事物连同整个世界都难以“出场”并显示,而只能沉默于黑暗的混沌之中;语言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整合下,人才能把各种结构的活动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各种文化形态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以,正是这种语词符号化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性”的圆周。[2]87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论证的:作为“此在”的人,有三种基本存在方式:一是“处身性”,亦即意识到自己存在状况的可能性;二是“领悟”,亦即具有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可能性,具有主动与世界互动的可能性;三是“言说”,亦即“处身性”和“领悟”过程都呈现为“言说”。在言说中,此在显现自身并“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敞开自己并转化为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对自己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理解,人对自己存在的“筹划”。(注:参阅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至此,我们更应该能够理解: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民族创造语词符号、运用语词符号通过语词符号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创造文化,其最高目标应该是也可能是汉民族的“人”。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关注汉民族人的造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形成的动力与方式,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例如,《尔雅·释天》记录了四种和风的名称,并且作了解释:“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中国先民为什么要将和风细分为四类,并各予这样的一个名称?这四个名称各有何种独特的意蕴?这样,我们就必须立足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于是就能看到,在这样的分类命名过程中,中华先民已经本着自己农耕生产生活的需要与经验,表达出自己对于和风的独特感受和独特态度,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方式,因而也就在揭示和风存在的同时彰显出一个自我来。又如名词“义”,是古今汉语的一个常用词,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前人已经对其来源作出了清晰的考证,亦即《毛诗郑笺》所说的“义之言宜也”。但是,我们现在却有必要在前人止步之处继续发问:“义”与“宜”何以能够同源?其同源关系说明了什么?这样就能明白:所谓“义”,无论儒家提倡的思想范畴,还是民间流行的道德信仰,究其根本,都是适宜于人们生存发展的行为、事情和精神,都是“宜”在人的生存方式领域的发展。倡导“正义”或讲求“义气”,都是为了在各种境遇中都能够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略略窥见中华先民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品性。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深入到人们的对话之中,关注汉民族人的用词释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的表达与效应,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基本特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总是在与他的对话中,也许更多地并且更隐蔽地还在与他的后人的对话中。”[3]101对话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活动和存在方式;人在对话中使用语词解释语词并通过语词以解释存在、交流思想、彰显自己、创造意义,而其意义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是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譬如,明代著名学者焦闳《焦氏笔乘》记载了北宋家李彦平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
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选,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伤,姑归读书可也。”某意不怿。仲修曰:“公颇读《论语》否?”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读此,且道‘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某茫然不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纟希?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既欲学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某闻其言,顿若有悟。
《论语》首章首句首字,便是一个“学”,这是孔子人生经验的和教导学人的纲领,意蕴非常深厚。赵仲修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填充其“召唤结构”,用自己的独到心得劝勉学人,使“学”的词义有了新的显现和拓展,使学人“顿若有悟”,并将所悟引入自己的人生实践。从这样的用词释词活动中,不仅可以看到特定词义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深化、发展的,而且可以领略儒家学者所信奉、所追求的,亦即他们理想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
三、拓展多向思路中的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论述,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在多维的视角中应该突出一个主要的视角,亦即汉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在多层的目标中应该突出一个最高的目标,亦即认识汉民族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在其多向的思路中必须突出一种基本的思路,那就是从主要视角出发,面向最高目标,将个体的语词符号放入整体的词汇系统之中,将整体的词汇系统放入汉语大系统之中,将汉语大系统放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之中,由孤立的词汇现象研究走向人的词汇活动研究,从而认识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认识汉民族人在语词符号化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自我的生存方式、根本特性和存在价值。而人的语词符号行为又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系统,其中主要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相同环节与线索,所以又可以将这一基本思路再分为认知学的思路、解释学的思路、文化学的思路和的思路,以便进行较为具体深入的阐述。
1.认知学的研究思路
认知活动是人与其生存空间一切互动的起点,是人脑通过符号(主要是语词符号)处理生存空间中事事物物信息的加工过程,亦即人对事事物物的特征、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感知和反映。认知过程包括低层次的感觉、知觉、短时记忆等等和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概念形成、推理过程、语言理解、知识运用和问题解决等等,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从“范畴化”到“概念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词符化”。(注:所谓“词符化”,是指特定事物获得词的表征亦即特定意义获得词的表达的过程,换一角度看也是命名造词的过程。“词符化”完成以后,特定事物及其意义便通过词的引渡而以词的形式进入民族人的生存空间,进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因为,生存空间及其万事万物正是以转化为概念和词符的方式表现对于人的存在并由此而成为“存在者”;人也正是在感知事事物物、认识生存空间、将经验到的外在现实加以概念化和词符化的心智活动中揭示事物的存在、彰显自己的存在并由此而成为“此在”。以此为根据,我们提出“认知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从认知活动的角度,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发掘词汇资料寻找相关史料,由已知求未知,探究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主要动力、内在根据、基本规律及其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中的作用和效应。其中最为切实、最为重要的是着眼于民族人的认知活动以扣住范畴化的进程和概念的表征:研究分类如何促使语词所指事物的类型化,它是词义形成的先导;研究概括如何促使语词所指事物的词义化,它是词义形成的方式;研究表征如何促使语词所建词义的词符化,它是语词形成的标志;研究人们如何以联想为根据,参照原有事物以认知新现事物,借用原有事物的名称作为新现事物的名称,它是人们常说的词义引申。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探知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动力、根据、方式和效应,而且可以发现汉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窥见民族“人”的心智特征。(注:参见周光庆《汉语词汇研究的认知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
2.解释学的研究思路
一般说来,解释包括理解和阐释,是作为解释者的人在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怀着自己的认识图式,基于认知的初步成果,理解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据、过程、特征和价值,确认它“是什么”、“怎么样”,并将其转化为意义而用语言阐述出来的活动。解释者对于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据、过程、特征和价值的理解和阐释,通常并不是“纯客观”的,镜子似的“反映”,而总是发挥了认知图式的设定对象的选择功能和整理信息的规范功能,成为了一种发现,或是一种创造。从哲学的高度看,解释所发现、所创造的意义,体现了人与事物、与生存空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构成了人与事物、与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是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从语词的实际看,解释所发现、所创造的意义,大都转化为词义,并获得了语词的表征。所以,如果说人存在的独特本质便是对生存空间及其事物进行以认知为基础的解释并由此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解释也就成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那么,由解释而生成的词义也就因此而具有某种生存本体的性质,折射出人的认识图式和生存方式,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此为根据,提出“解释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的基础上,从解释活动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人是如何在解释中形成词义、在解释中运用词义、在解释中理解和发展词义的。其中最有难度也最为重要的,是探讨词汇形成发展对于存在的解释和对于“人性”的彰显,是探讨词汇运用接受对于存在的解释和对于“人性”的彰显。(注:参见周光庆《汉语词汇研究的解释学路径初探》,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文化学的研究思路
人认知事事物物、解释生存空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人的一切功能的集中体现,是人的一切劳作的成果总和,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得以形成自己本性的有力动因。语言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文化的,文化往往以语言的方式向人呈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语言的,二者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具体就词汇与文化而言,一方面,作为语词创造的动力、表述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文化理所当然地起着主导作用,推动着语词的形成和发展,制约着语词的形式和内容,影响着语词的运用和解释,从而使语词符号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创造的凭借、形成的中介和表述的符号,语词又对具体的文化事项和整体的文化世界理所当然地发挥着概括与表征功能、引渡与导向的功能、述说和建构的功能,从而使文化世界具有自己的语言特征。要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离不开对词汇的发掘分析,要对词汇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对文化的发掘分析,而要对民族“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又离不开对语词与文化的互动的发掘分析。以此为根据,我们构拟“文化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和解释学思路的基础上,从文化活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语词作为文化表征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功能性,研究语词与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研究这种多重互动关系对于民族“人”的促进与彰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探讨“文化的创造发展与词汇的创造发展”、“文化的超越方式与词汇的运用解释”、“文化的内在秩序与词汇的内在秩序”。对此,拙文《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有具体的论述。
4.哲学的研究思路
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入乎言词的存在,就是存在的家园;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并非作为某种现成的空间而存在的,它需要运用语词符号行为等等方式予以重构;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待以表现与建构的是,人拥有世界。哲学要认识世界,却又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那是各种经验科学的任务),而主要应该研究语言如何表现世界,如何建构世界、如何传达世界的意义,以便真正引导人们更好地由认识语言而认识世界。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语言建立了人的主体性,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促成了人与世界的互动,开启了人对未来的理想,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哲学要认识人类自我,却又并不直接研究人的内在心灵(那是各种心理科学的任务),而主要应该研究语言如何促成人与世界的互动、如何成就“人性的圆周”、如何表现理性、如何形成思想,以便真正引导人们更好地由认识语言而认识人类自我。以此为根据,我们构拟“哲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解释学思路和文化学思路的基础上,进而应从哲学的高度,用哲学的方法以研究:民族人如何创造和运用词汇以揭示世界的存在、彰显自己的价值、建构自己的文化世界,而人的这种特定存在方式,又如何成为潜在动力、真正归向和规范原则,促进着、引导着、制约着民族语言词汇的创造、运用和发展,并且因此而形成了何种风貌与哪些规律。稍微具体地说,可以研究词汇产生与人的存在方式、词汇发展与人的存在方式、词义结构与人的存在方式、词义演变与人的存在方式的互动共变[4]。
最后应该强调:就其性的总体而言,人的认知行为、解释行为、文化行为和“哲学行为”(完善本质特性、彰显存在价值的行为)作为“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是一种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多样而统一的行为系统;词的创造活动、运用活动、接受解释活动作为“人的词汇活动系统”,同样是一种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多样而统一的活动系统。“人的词汇活动系统”既属于 “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又与之整体对应,构成了一种互动共变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构拟的研究思路中的认知学思路、解释学思路、文化学思路和哲学思路,同样也是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分别而连贯、多样而统一的系统,在论述时只能分别一一道来,在理解和运用时可以有轻有重、有先有后、有隐有显,但是在其深处则是相互结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并不能判然划分其界限。
[]
[1]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周光庆.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J].语言文字应用,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