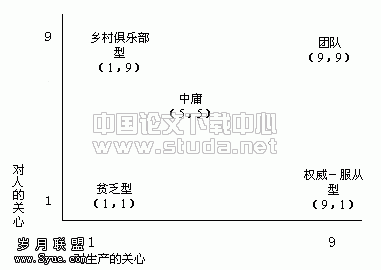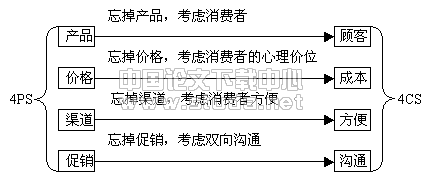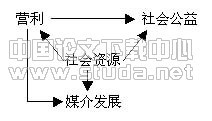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与传播学的亚洲主张
关键词: 传播学 普遍主义 话语 亚洲中心 本土化 范式
[摘要]:传播学滥觞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迅速扩张到全球。然而,当一种理论离开其生存的母体落地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时,必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产生冲突,这时必然要进行的是“本土化”改造。传播学的亚洲中心正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西方传统,建立新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与西方进行对话、互补,形成和谐发展的态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亚洲传播学的发展取向应该抛弃“中心”和“多元”的矛盾之争,建立根植于亚洲文化和现实的新的研究范式。
Abstract: Communication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reasingly became into an “universalism” discourse spread through the world rapidly. However, as a theory leave its matrix and be introduced into other countries or areas, the conflicts will appear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culture, values and customs of the local society. So the “localization” is necessary for a theory. The asiacentric of communication being put forward ju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its “localization”, whose purpose is not to build up a new discourse hegemony but to talk to the West, to form a situatio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Asia and the West. With the guide of this purpose, the approach of Asian communication should discard the contention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pluralism” to construct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ground in the Asian culture and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Universalism; Discourse; Asiacentric; Localization; Paradigm
一、引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与东方传统
东西方的对立或者说矛盾,并非绝对的和本源的,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与,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纬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张旭东,2006:5)然而,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随着资本的扩张,使得某种文化会以某种形式向其它文化扩张,形成某种“普遍”,而使另一些成为“特殊”。在这一过程中,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比如: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领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研究领域“理性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的博兴等。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引导下,有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话语似乎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状况。那么是谁赋予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权力,又是谁使得这一“普遍主义”的话语拥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之争。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对立的,普遍是特殊的总体,“它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它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黑格尔,1981:354)可见,普遍性的产生离不开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张旭东,2006:4)在黑格尔的逻辑下,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遍性”,也并非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义,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视为“特殊”,并且把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这有点类似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即西方话语在发展过程中,赋予自身“普遍性”的权力,即在与他者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获取一种“真理性”,证明自己为真,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成为一种“普遍话语”。
与西方对立的是东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赛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的概念“主要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一种文化和物质殖民现象,这种现象与19世纪的欧美殖民帝国主义有关。而‘东方主义’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谢少波,王逢振,2003:225)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文化价值领域。面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随着世界市场席卷全球时,东方世界更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东方传统”的问题,于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亚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们谈“东方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红木家具、穿旗袍、喝绿茶、看中医、坐人力拉车。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东方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创造生存的空间、找到传播的渠道、建构理论和上的意义,让其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开辟出一块蓬勃发展的空间。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及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也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博弈。
二、传播学的西方起源与全球发展
一般认为,传播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诞生之初,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传播现象,提出诸多传播理论以及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8),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播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免受灾祸外,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外,更与美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学术界盛行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效用。而信息传播、人与人沟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沃土。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而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等。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就来看,传播学于上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而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661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研究生层次的,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止,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张晓锋,马汇莹,2007)
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当前,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自己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本土的传播学理论还远没有被纳入到传播学的主流中,也未曾对传播学的主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也有着其不可克服的缺点。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赵晶晶,2008:11)
三、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亚洲中心”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症,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过程中的重重阻碍,终于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仲富兰,2008)
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Yoshitaka Miike,2004:67)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欧洲传播’或‘非洲传播’)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Guo-Ming Chen & William J. Starosta,2003)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赵晶晶,2008:11)华裔美国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赵晶晶,2008:13)
四、全球化时代“中心”与“多元”之争
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约翰•汤姆林森,2002:4)全球化“是快速、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系统”,(约翰•汤姆林森,2002:2)即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 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是多重价值的联结,它跨越了国界,将人们的实践、体验以及各民族、国家的、、环境以及文化绑在了一起。“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费的全球趋同,那就过于简单了。“全球化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约翰•汤姆林森,2002:1)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本土及区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反霸权”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过经济、技术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的“多元”之争。在此背景下来观照人类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碰到的是“中心”与“多元”的矛盾斗争。
如上文所述,西方话语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是由于凭借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治领域的霸权,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的过程中,排挤他者话语的空间,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西方传播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假“普遍”之名试图掩盖和压制他者文化中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美国的时代,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多元主义取代西方所倡导的“普遍主义”。 而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或者试图树立多个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真正让各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全球话语的一元存在。因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任何对“普遍性”的强调实际上都强化了统治群体和亚群体的等级制,具有一种压抑性和反动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多向流动,不是任何“中心”的单向输出的过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文化自主性,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价值系统中去。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非西方”一定要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并非要与“西方”进行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要强调,“非西方”世界应该在其自身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自我发展的问题,要寻找适合自身的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保持或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对话或者交流,使得“全球化”的过程真正充满活力并趋近多元。
由此来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笔者认为并非是要用“亚洲中心”取代“美国中心”或者“欧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结果应该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实,亚洲中心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亚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亚洲中心主义,也不是种族中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亚洲的翻版。亚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将亚洲的世界观设定为宇宙之惟一,更不会强加在非亚洲人身上。研究者们明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与欧美中心不是对立的关系,声明‘坚持亚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亚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的悖反’,胸怀宽广地倡导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极端,呼吁东西方融合,互补双赢”。(赵晶晶,2008:12)虽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也是文明本身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再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努力建构的同时,需要警惕新的语言霸权在亚洲内的建立”。(赵晶晶,2008:12)因此,笔者认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话语,或者新的学术霸权,来对抗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并非是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谓的“亚洲中心”应该是一种“主张”、一种“视角”、一种“取向”,甚至是一种“方法”。
五、“亚洲中心”的取向:建立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抛开“多元”与“中心”之争,就意味这我们尝试着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思维和认实践的最主要范式。在这种视域下,我们提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不在于要统计有多少亚裔的传播学者、有多少亚洲的传播学期刊、有多少“亚洲问题”,而在于在研究和解释人类传播现象时、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是否运用了亚洲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使用了亚洲的研究方法、解释体系以及话语表达,同时这种价值体系、研究方法、解释系统和话语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成为西方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人类传播现象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在讨论研究传播问题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产生冲击,对其“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整,并能够建立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在《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来说明科学的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仪器、标准等同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许为民,2002:147)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提出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应该朝一下几个方面努力:
1. 挖掘亚洲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
亚洲是一个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亚洲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亚洲中心”谈何容易。然而,正如亚裔传播学者陈国明所言,亚洲,就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目的论各个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和谐被当作是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等,(Guo-Ming Chen&William J. Starosta,2003)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亚洲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应该挖掘亚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打通亚洲不同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2. 运用亚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来源于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倡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亚洲哲学强调“和谐”、“整体”和“中庸”,于是在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时,应该运用亚洲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比如:“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或‘思考’;重视同情性传播……愿意主动接受事物、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这与亚洲人崇尚宁静有关;和谐观念能够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鼓励实践“中庸之道”;在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亚洲人会通过一种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Guo-Ming Chen&William J. Starosta,2003)等等。
3. 建构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现实的传播学理论
新的范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建立。相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西方传统而言,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范式建立的表现之一是应该有一系列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问题的传播学理论的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亚洲传播学也应该是只有亚洲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的,这些理论是极具亚洲特色的,是贴近亚洲现实,解决亚洲传播现象的,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学者不能提出的。比如日裔著名的传播学者三池贤孝从亚洲中心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提出了5个与西方中心相异的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汇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Yoshitaka Miike,2004:67)虽然三池贤孝的理论还止停留于假设层面,但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不同的是,亚洲文化更崇尚阐释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些理论假设在研究层面也同样具备了理论价值,是亚洲传播学研究的大胆创新和尝试。
4. 建立传播学研究的共同立场、站在在亚洲视野的高度与西方对话
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建立首先应该达成共识的是传播学研究的亚洲立场。立场不统一必然导致话语的多样化,而任何一个特殊的亚洲文化都不能代表亚洲文化的整体。因此,在建构亚洲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建立一个亚洲人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研究立场;其次应该站在亚洲视野的高度,摒弃任何狭隘的地方主义,与西方传播学进行对话和交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传播学传统能够迅速壮大并具有全球扩张的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它能够把“他者”文化和问题包容进来。而我们所倡导的“亚洲中心”若想在世界传播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大亚洲”的高度,尽可能地扩展亚洲传播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的适应性和包容度。在这样的基础上,与西方传播学传统进行对话,取长补短,才能在世界传播学领域发出声音,才能为人类的传播学发展做出贡献。
[]
[1]张旭东(2006).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Zhang Xudong(2006).Culture Identity in Globalization Age.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黑格尔(1981).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Hegel(1981).Logic(translated by Yang Yizhi).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3]谢少波,王逢振(2003).文化研究访谈录.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Xie Shaobo,Wang Zhenfeng(2003).Compile of Culture Study Interview.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4]张晓锋,马汇莹(2007).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76716/5294312.html.[Zhang Xiaofeng,Ma Huiying(2007).The Situation and Challen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raduate Education—The Summary of “Chinese Society &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Conference.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76716/5294312.html.]
[5]赵晶晶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Edmondson,Jingjing Z.(Ed.).(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6]仲富兰(2008).传播学面临中国本土化的重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52f810100a3dw.html.[Zhong Fulan(2008).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localizatio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52f810100a3dw.html.]
[7]约翰•汤姆林森(2002).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John Tomlinson(2002).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translated by Guo Yingjian).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8]许为民(2002). 科技 社会与辩证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Xu Weimin(2002).Nature Technology Society and Dialectic.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9]Yoshitaka Miike(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1).
[10]Guo-Ming Chen, William J. Starosta(2003).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