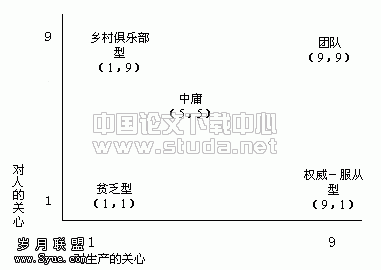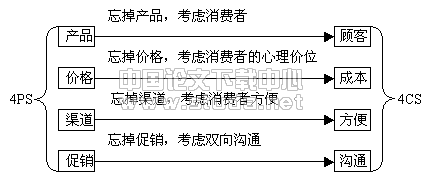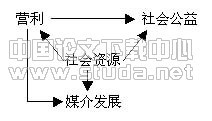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防线——评格里尔逊的“创造性处理”论
【内容摘要】文章分为四部分:1、纪录片的定义——不允许虚构;2、“对现实创造性处理”的积极理解;3、主张虚构是纪录片虚无主义倾向;4、技术可以撒谎=纪录片可以虚构(?)。文章认为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防线,必须真诚地对待现实和观众。?
【关键词】非虚构;纪录片;“创造性处理”论?
自从约翰·格里尔逊在1926年2月把罗伯特·弗拉哈迪拍的那种不同于摄影棚制作出来的影片叫做“纪录片”(Documentary)以来,我们多少次地争论有关纪录片的基本属性问题,尤其对于纪录片可不可以虚构之类的争吵,始终没有停息过。至于在纪录片创作实务方面,更是泾渭分明。从19世纪末,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的两个摄影师——坚持扛着“活动电影机”把异国他乡的真实情况报道给法国人民的菲利克斯·梅斯基奇和善于借用有关无关的影片资料“再构成”来代替实地拍摄,以此蒙骗了卢米埃尔和法国观众的弗朗西斯·杜勃利埃。到20世纪末,在西方出现的主张虚构的“新纪录片”以及与其相对的在西方成为纪录片主流风格的“真实电影”(CinemaVerite)和“直接电影”(DirectlyFilm),主张纪实和鼓吹虚构这两根线始终贯穿在纪录片的进程中。其结果是在电影诞生百年之后,我们还不能在纪录片基本的特性方面获得统一的认同。呜呼,哀哉!
纪录片的定义——不允许虚构
其实,纪录片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纪录片让虚构走开。上文提到的第一个使用“纪录片”这一个概念,并由他开始词典上出现了这一专门词语的约翰·格里尔逊,他当时在看了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记录南太平洋岛国土著人生活的《摩阿纳》之后,在1926年2月8日号纽约《太阳报》上撰文对纪录片这个词作了明确的界定: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总的来说纪录片是指故事片以外的所有影片,纪录片的概念是与故事片相对而言的,因为故事片是对现实的虚构(fection)、扮演(staging)或再构成(reconstruction)”。
如果说,格里尔逊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纪录片的概念还不那么成熟的话,到了30年代,他的认识就明确多了。1932年,约翰·格里尔逊对当时的英国纪录片运动提出的纲领是这样的:“第一条原则:(1)我们相信,纪录电影就其所触及的、所观察的以及选自生活自身的容量,足以开发成一种新的和极端重要的形式。摄影棚电影极大程度上不顾及在真实世界之上揭开银幕的可能性。他们拍摄扮演的故事,并以人工布景为背景。纪录片将拍摄活生生的场景和活生生的故事。(2)我们相信,原生的(或土著的)角色,和原生的(或土著的)场景能比较好地引导屏幕解释现实世界。它们给电影提供巨大的素材的宝藏。它们使每幅影像的力量陡增百万倍;他们促使对于真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说明比摄影棚里施作魔术和依靠机械重演更有力量,更丰富和令人惊讶。(3)我们相信,从这样状态下获取的素材和故事,可以比扮演的东西更好(在认知上更加真实)。自发的自然产生的姿态在银幕上有一种特别的效果。电影具备了一种令人振奋的能力来提高传统形成的运动或者显得平稳光滑的节拍。那是一种以专断的矩形的特别展现的运动: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给了它极大尺码的套靴。”?①
这两段精辟的论断说过还不到80年,就有人篡改它的含义了。1993年春季,美国《电影季刊》上发表了林达·威廉姆斯的文章《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这位美国电影理论家把主张虚构的纪录片创作倾向概括为“新纪录电影”,而且认为“纪录片不是故事片,也不应混同于故事片。但是,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新纪录片运动”及其支持者之所以公然主张纪录片不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主要的理论根据就是断章取义地抓住了约翰·格里尔逊1926年说的、现在看来较为含混的一句话: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
对现实创造性处理”的积极理解
其实,“对现实创造性处理”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正确的、积极的理解,应当是指作为作品必然包含的创作主体对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的社会倾向以及审美取向。
1979年有美国南加州大学(UCLA)、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休斯敦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著名电影学教授合编出版的《电影术语词典》对于纪录片做了至今我认为最精辟和经典的界定:“纪录片,纪录影片,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docunmentary film, documentary A non –fection film which has a persuasive theme or point of view, but which draws its material from acturelity and uses editing and sound so as to enhance the process of persuasion)。在这个定义中,首先排除了虚构。但是,它又明确指出纪录片应当具有特定的主题或观点,这种主题、观点还有能“吸引人”和“有说服力”的功利目标;随即,又同样明确的指出纪录片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并用剪辑和音响这两种主观创作手段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它对格里尔逊说的“对现实创造性处理”也是最好的说明了。荷兰的纪录片先锋伊文思也说过同样精彩的话:“纪录片不能虚构,但要想象”,“有人认为纪录片不是艺术,因为它没有想象,这个看法不对”,“从拍摄开始之前到最后剪接完成,自始至终不能脱离想象”。伊文思进一步阐明道:“实际上这也跟石料对于一个建筑家或雕塑家一样,石料本身并没有艺术价值,经过建筑家和雕塑家的加工,才成为艺术品。同样生活也只是素材,而不是艺术品本身。艺术开始于对素材的选择,现实生活需要经过选择、剪裁,才能形成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影片”。?②在这一段话里,老伊文思以他几乎一生纪录片艺术实践的体验,对我们所讨论的“对现实创造性处理”作了精辟、形象的诠释。
对于纪录片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环节,伊文思认为是剪辑:“它并不仅仅是把一个个片段拼凑在一起就算了事。这是对不同的情感的剪辑,对各种情况下和气氛变化不同的心理冲动的剪辑。”伊文思认为,纪录片剪辑有不同高度:第一个标准,是简单的视觉上的剪辑。“动作与动作之间转换的流畅性,镜头与镜头衔接上的适当性,往往使观众看不出这一段里场景不同的镜头的确切数目”(我们可以把它简括为“剪辑的生理因素”);第二个标准,达到超过生理效应的心理因素——在观众中唤起情感;第三个标准,(更高一级),把电影摄制者的感情上的目的上升到表达一个观点——个人、社会和的观点。第三个标准,“主要目的是加深真实事物间的关系——揭示表面现象的实质”。伊文思从纪录电影的创作体验出发,讲述了“画面-情感-思想”的公式,它不仅适用于纪录电影,也适用于一切影像的、造型的艺术。它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完成创作主体充分的表现的十分宽阔的天地。我们可以在这个天地里自由翱翔,甚至把“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推行到极致。
我们似乎总回避不了辩论约翰·格里尔逊说过的话的是非曲直。仅有的道理恐怕只有一个——“纪录片”这个概念是他率先提出来的。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纪录片完整的定义,是由千百万纪录片的实践者、研究者共同出来的。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历史事实:在纪录片初创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20世纪20年代,甚至是英国纪录片运动骨干哈里·瓦特和巴锡尔·瑞特拍摄《夜邮》的30年代,由于当时电影技术手段的落后和作家本人对纪录片是何物在认识上的混沌,这些影片运用了一些组织、摆布拍摄的手段。这就是威廉·罗斯曼(William Rothman)在他的评章《作为狩猎者的纪录片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中揭示的现象:纳努克的冰屋是像布景一样的半边屋子,“微笑的尼拉”也并不是纳努克惟一的妻子,弗拉哈迪用刚强换取纳努克对拍摄影片的合作与承诺,等等。我们也可以谅解巴锡尔·瑞特、哈里·瓦特拍摄《夜邮》时部分场景是在布景片中安排,由群众演员完成的。但是,应当由历史来原谅这些先行者们,也同样应当让历史告诉未来,纪录片不允许虚构,当然也不允许扮演和再构建事实。美国学者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在他的著名文章《纪录片的人声》(TheVoiceOfDocumentary)里,系统的分析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纪录片策略与风格的演变过程。他把纪录片的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
1,从30年代到50年代末,为“格里尔逊模式”阶段,格里尔逊首创的“画面加解说”模式逐渐被演变成“上帝之声”般“自以为是的说教模式”,二战结束后,这种模式就“失宠”了。
2,整个60年代,是“真实电影”(又叫“直接电影”)取而代之并兴盛的时期。它排除导演的一切干预,“它直接、坦率,仿佛拍到的乃是特定人物日常生活中未经修饰的事件,所以‘真实感’更强”(比尔·尼科尔斯语)。但是,这种电影“有时使人困惑,更时常使人为难,难得向观众提供他们所寻求的历史感、时代背景或前景”。
3,因此,到了70年代,“我们又看到了第三种风格,它常常以采访的形式进行直接表达(人物和解说员直接向观众说话)”,“形成了当代纪录片的标准模式”。
4,到了80年代后,美国为首出现了第4种模式——自省式(Self-relfexive)。“纪录片把评述和采访、导演的画外音与画面上的插入字幕混杂在一起,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纪录片向来是只限于再现,而不是向‘现实’敞开明亮的窗户,导演向来只是参与者——目击者,是主动制造意义和电影化表述的人,而不是一个像在真实生活中那样中立的,无所不知的报道者”。
比尔·尼科尔斯这样简明清晰地阐述了历史,而且是从纪录片作品的文本精神(《纪录片的人声》)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而不是单纯从影像的表现技巧的视角来阐述历史。它阐明了纪录片创作主体逐渐由直截了当的说教者转化成中立、客观的报道者(30年代至50年代末),又由此转化成参与者目击者的过程。这一过程,突出的贯穿着非虚构、用事实说话的主线,而全无以虚构和扮演、重建来代替事实的报道的踪影。
主张虚构是纪录片虚无主义倾向
对“对现实创造性处理”的消极理解,是主张虚构。这种主张实际是把纪录片推向消亡。非虚构是纪录片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它,纪录片同故事片就分不清界限,也失去了它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
那么,为什么无论在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人在鼓吹各种重现、再现乃至虚构的合理性,又总有人在努力运用各种重演、扮演手法拍摄纪录片呢?
1.是由于一种顽强的自我表现心理作怪。利用拍摄纪录片来达到表现个人的目的,这在战争年代者是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世界进入比较安定,甚至社会达到一定富裕的程度的时候,有些纪录片制作者厌倦于抓取生活的本来面貌,他们也惧怕为真实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再去花费精力、时间和经历千辛万苦。他们不甘心再让普通的群众作为纪录片的主人,而自己则是事件的记录者的地位。于是,有人提出要拍所谓的“个人的纪录片”,他们不惜动用纳税人的钱,占用强势大众媒体和纳税人——观众的时间,来表现个人的社会倾向和审美追求。而社会财团或媒体也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为他们投入,当然,其目的是为了赚回更大的利润。于是,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高呼“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这样的口号的同时,也不得不焦虑地预言:“在这类影片(按:指用演员扮演的纪录片)里,造型的冲动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倾向,处于压倒的地位。”克拉考尔是主张“任何纪录片,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是倾向于表现现实的”。但是,他十分明白:“然而,就纪实影片来说,它只是向部分的世界开放,新闻片也好,纪录片也好,他们都并不怎么描写个人和他的内心冲突,而是描写他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用罗沙的话来说,‘纪录片依靠个人对他的周围世界的兴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罗沙继续写道,‘如果出现了人,他们对于主要主题来说是次要的。他们的个人爱恶是无关紧要的’”。克拉考尔进而指明:纪录片排除“那些由个人好恶”而产生的东西。?③
确实是这样,在我们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纪实的倾向和造型的冲动会始终困扰我们。有时,造型的冲动会膨胀到令人发昏的地步,以致漠视纪录片必须真实再现事件的使命。在创作的欲望和记录的本职、造型的冲动和及时的追求之间取得有效的控制和适当的平衡,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过分的注重形式上的“突破”,而忽视了对于内容的开拓。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有为数不少的文章竞相分析近年来纪录片徘徊于所谓的“低谷”状态的缘由,而且大部分观点都认为是从80年代后期形成的“纪实热”带来的恶果。要摆脱这样的状态,就要寻找新的形式。“真实再现”(又有称之为“情景再现”)就是一个“突破口”。
诚然,纪实主义,即要求按照事物本来面貌来反映世界,在西方又常常被称之为“现实主义”者,原属纪录片创作风格、方法、策略层面的事。它是纪录片创作方法诸多选择中的一种,不像纪实性或是非虚构那样,后者是对于纪录片是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特别属性。但是,也应当承认,纪实主义从巴赞为代表的“摄影影像本体论”美学理论作为基点,按照“物质现实的复原”来指导纪录片创作,无疑是更贴近纪录片“记录的真实”和非虚构的原则。自从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纪录片界彻底摆脱和清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并让普通的人民群众走上荧屏,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且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以跟随拍摄、场面调度配以同步录音的技术,来拍摄真实事件、真实环境里发生的真人、真事,在事件的发生、的真实过程得到尊重的基础上,细节的真实也得到了尊重,甚至被作为独立的叙事单元,而使纪录片更加生动和深刻。中国的纪录片开始频频在世界舞台上获奖,并担当“跨文化使节”越洋过海,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增进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这是多么好的局面呀!它是多少人、多少年奋斗得来的。每当我身处国际电视节评委席上,看到一张张熟悉的或陌生的同胞的脸,怀着胜利的喜悦,高举着奖杯,我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5月,我在美国芝加哥“风城”国际纪录片节主持“中国纪录片日”,几乎所有的美国评委都向我翘起大拇指,称赞中国纪录片的优秀。其中有一位叫麦克的教授,他甚至把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纪录片的繁荣和崛起同二战后出现在意大利战后废墟上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作比较,也就是题材和内容所具有的强烈的当代性和社会性;以及反映的真实性和由此直接产生的冲击力。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否定这短短20年来中国纪录片出现的这样难得、又这样喜人的局面?
其实,说中国纪录片处于“低谷”,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就2002年在“北京国际电视周”和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两项重大的世界性纪录片活动来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表现不俗。在“北京国际电视周”纪录片研讨会上,中央电视台孙曾田摄制的《祖屋》、成都电视台彭辉摄制的《平衡》、湖北电视台张以庆摄制的《英与白》在观摩和研讨中受到了中外观众和专家的关注和好评。此前,这些作品都在国内外获得了重要奖项。在第9届上海“白玉兰”国际电视节,我本人荣幸地担任了纪录片国际评委召集人,就评委们审看的20余部中外“人文类”纪录片来评量,中央电视台参评的《三峡移民》和上海电视台与徐州电视台合作的《干妈》,同其他参赛作品比较要突出很多。占国际评委多数的外国评委们特别赞赏两部中国作品内容的价值和讲故事的技巧。因此,两部作品很顺利地被评上了人文类纪录片“大奖”和“评委奖”。在参加2001年年底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年会”,和上述北京、上海的两次国际纪录片活动,我本人对于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创作方法上的进展有了这样的印象:
中国优秀的纪录片对于生活的观察和描绘越来越往深层次进发,它们入木三分地刻画现实人生的同时,主题更富于哲理性;中国优秀的纪录片更热衷于讲述一个真实而又动人的故事。它们几乎把其他姐妹,特别是文学、戏剧艺术的叙事技巧借鉴到纪录片拍摄中来。叙事对象更加个体化,叙事本身更加情节化,诸如:悬念和高潮的设置、误会法和幽默的的运用,以及开放式叙事结构的安排、处理等等,都使作品的审美品位加高了。
不足的是,中国纪录片题材面比较狭窄,样式也比较单一。我们还比较集中于拍人文类纪录片,对于风光类纪录片,我们关注和投入都不够;社会调查性的纪录片各地电视台拍得不少,但没有给与应有的地位,一般还是当着新闻深度报道来对待,制作得比较粗放。这后两种样式与国外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今后前进的道路还是在于深入生活、拓宽题材。更加讲究作品的当代性和社会性、哲理性。
在2002年5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视周”上,瑞士导演克利斯丁·福瑞(Christian Frei)拍摄的《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在观众里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这部纪录片有大量在第一现场拍摄的画面,使用附加在战地摄影师的尼康相机上的唇膏型数字摄像机拍的——本片主人公、美国杂志摄影记者詹姆斯·诺斯威在科索沃、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他所目睹的战争的残酷和人们的苦难。在影片开始的时候,银幕上打出了导演引用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画面不是足够的好,那你靠得不够近”(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 not close enough)。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的纪录片拍得不够好,确实应当首先检讨一下我们对于生活深入的程度。
这是一位成功的西方纪录片工作者想竭力告诉我们的话。但也有另一位西方人,那就是前面我们提及的威廉姆斯,居然告诉我们说:“技术使摄影机可以撒谎”(见《没有记忆的镜子》)。这句话,居然成为“肯定了被以往的纪录电影(尤其是‘真实电影’)否定的‘虚构’手法”,“纪录片可以而且应当采取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的理论依据了。简单一点,是否就成了这样的公式:
电子技术可以撒谎=纪录片可以虚构(?)
但是,克利斯丁·福瑞的片子雄辩地告诉人们:数字技术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关键是我们是否真诚地对待现实,对待观众,要时刻警惕地提醒自己离现实是否很贴近。这次获得本年度“白玉兰”奖的自然类纪录片——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长牙巨兽》(Tooth Titans)、《空中猎手》(Flying Devils)和英国BBC的《诡异自然;绝妙运动》(Weird Nature Prog 1:Marvelous Motion),使用了多种多样的先进的摄影技术来武装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但是,他们提供的是来自自然的第一手资料,全然没有以往考察片免除不了的棚内扮演和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特技处理。数字和电子技术使得摄影机可以探索和记录人的内心感受和许多以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景象。美国导演米歇尔·勒布伦(Michelle Lebrun)用微缩摄影机拍摄了她的丈夫与癌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秒的内心感受和生理的感觉,影片的标题表明了主题:《死亡,一个爱的故事》(Death A Love Story)。
我觉得,我们对于国外的理论和观点,应当要学习、借鉴,但是要去伪存真,不能人云亦云,不加区别地一股脑儿的搬来。更不能实用主义地搬来为自己的标新立异来作支撑。现在,电视界泡沫很多,理论界也有泡沫,那就是不重视实践,纸上谈兵;不重视,断章取义,借以唬人。
3.没有解决纪录片创作究竟是要“厚古薄今”,还是讲求当代性、社会性?
美国学者阿兰·罗森沙尔在他的著作《纪录片的良心》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纪录片的使命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增进人类之间的了解。”
纪录片就其本质来说,应当是创作者对发生在眼前的事件的观察和记录的成果。纪录片主要是靠纪录今天的现实、阐明今天的抉择来解释历史的。同样的,也只有真实地记录今天的现实,才能增进人来实现宽文化之间的了解。因此,纪录片不仅在它的内容要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社会性,就其题材的选择来说,也要以当代的现实为首要选择目标。今天我们记录下的现实生活,明天就成为了历史。因此,我们更要重视非虚构对于纪录片历史使命的至关重要的价值。我们决不能用虚构、扮演、重构方法,为我们的子孙提供一部虚构的历史、一部扮演的历史。
今天我们已经拥有多种现代的手段来纪录现实了:胶片的、录像的、数字的,我们难道还要子孙们像我们今天回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今天已经失落的)文明那样,再用几个人在那里装模作样的“过家家”吗?记得上一世纪6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何钟辛老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新影”当时在拍一部反映“大跃进”后中国某地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纪录片,打算用一段土地改革后坐在原地拍摄的资料片来作一番“新旧对比”,没想到50年所拍的资料片记录的土改以后翻身农民的生活情景远比60年代现拍的情境要好得多!原因是50年代拍的镜头是“组织、组织再组织,摆布、摆布再摆布”的造假产物,那段历史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说今天我们的纪录片界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也是有根据的。例如有的电视频道不仅自拍的纪实性节目爱津津乐道往事,还积极从国外引进讲述外国人往事的节目,而且在节目比重上,讲述旧事往事的占了上风。热衷于讲往事,只要在量上注意控制,不是给人一点历史知识,也本无可厚非。但是,讲往事,又拿不出真实的记录片资料,于是只好扮演、重演。我在北京的屏幕上就看到过引进来的英国人摄制的纪录片《刺杀希特勒》,全片都是靠演员扮演的,虽然用了黑白片来拍摄,也没有给人历史的真实感。它与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同名故事片比,编、导、摄、演都逊色多了,我不知道该片编导想没想过:观众何必丢掉摄制精良的同名故事片来看你那种低成本的扮演的纪录片?
在对待历史题材的记录片的扮演问题上,我们应当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例如《失落的文明》这样的片子,我们没有一位强求作者在表现在电影问世以前,即以100多年前为下限的已经消逝了的文明时,不能借用某些扮演、重构的手段。但是,在处理时我们依然应当要求这样的作品做到以下几点:
(1)在同一部作品中,扮演、重构部分的比例不能超过纪实的部分;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要充分发挥文物、、遗址、实物的阐释、佐证作用,扮演、重构只能在借助形象手段来作模拟、借代式的说明方面起作用。
(2)扮演、重构所采用的手法,应当本着“宜虚不宜实”的原则。例如,采用“局部蒙太奇”(或曰“细部蒙太奇”,运用主体的局部形象组合来引发观众蒙太奇联想的手法);“反映法”(以影子来反映主体,或从物上去追踪主体的活动踪迹,以达到“如影随身”、“睹物思人”的效果);“模拟法”(借用某些道具、实物模型演示)以及模拟的或数字动画技术来传达。
(3)对于扮演、重演的部分必须用字幕、解说词公开说明本段是“再现”、“情景重现”、“故事片资料”等等。这样做更显出作品的严肃性。
然而,这一系列扮演、重构,决不会成为记录片的主要手段。纪录片不可代替的、反映其本质属性的手段还是采访摄影和跟踪拍摄。
在今天的世界,纪录片更应当关注现实世界人类之间如何实现跨文化的了解。对于本民族来说,纪录片要做到与时俱进,用今天的事情,来鼓舞今天的人民,同时,也为将来留下可靠的、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以,不管题材如何,纪录片一定要响亮地回答当代观众、当代社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是责无旁贷的。从这个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任务来看,纪录片只允许有记录的真实,而不允许掺假,对于纪录片来说,非虚构是最后一道防线,它不属于“宽容”的范畴。?
注释:
①引译自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编著,《纪实主义和电影》,Realism And The Cinema,Edited by Christopher Williams,1980年初版,英国电影学院电影研究读本,1995年9月第3版。
②《关于纪录片创作的几个问题》,《电影艺术》,1980年10月第10期,第48页。
③见《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文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