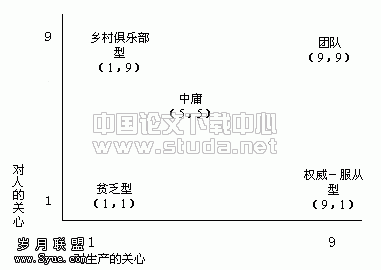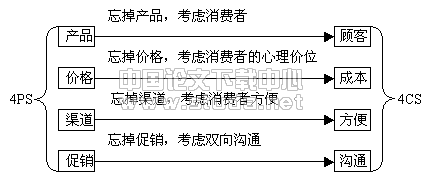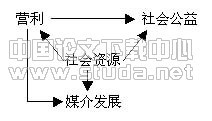论“废话”的语用功能
【内容摘要】语言的本质是正确地利用冗余的信息。不会说“废话”其实是不会说话。“简洁精练,言简意丰”不是最高明的智慧语言。应该摆脱用书面语规范口头语言的藩篱。当今广播电视媒介的语言应用更需要适度的冗余,它是修辞手段,更是有效传播的保证。“废话”的意义在于“没有什么意义”之外的“意义”。适度地淡化话语主流意义负载的所谓“废话”,可以成为节目的内容或资源,也可以是节目创作的“同构策略”。冗余和“废话”有不同的语用层次,也是一种语言的。?
【关键词】废话;语用功能;冗余;信息
广播电视媒介语言中的所谓“废话”,通常是指话语表述中的冗余成分,有时泛指缺乏主流文化价值或离开话题主旨的言语。因为它们是“毫无意义”的,故称之“废话”。探讨“废话的功能”并不是提倡多说废话,而是觉得权威的媒介语言理论有时过分强调说话“简洁精练、言简意丰”有所不妥。去年在研究会听讲学,论者将这个观点推向极致,要求主持人们说话时要做到“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并告戒大家要杜绝一切“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
但是,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这里“废话”被设定了一个很模糊的“意义”评判标准,也就赋予人们武断的语用评价的便利。其实,这并不公平。因为那可能是脱离具体语境的、静态、平面化的语用评价,如果放在特定的话语情境中整体地观察就会发现,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可能是一种修辞手段,可能属于很适当的“有效冗余”,是具有某种交际功能的语用策略。
不妨说几个有趣的例子。
美国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视谈话节目,叫“Cosby Show”,节目主持人Cosby在电视上口若悬河地说,说得妙趣横生,但见这位主持人的语言根本谈不上“简洁精练、言简意丰”,而且会话附加语特别多。“会话附加语”是一种附着于意义表述之外的很?嗦的话语,是随口说出的不表达具体实在意义的口头语,通常被斥之为“语言的杂质”,甚至被看作“口头禅”。加利福尼亚一家报纸刊登文章说,Cosby在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里共计使用了178个会话附加语,但是,据说正是这些“可有可无”而又“毫无意义”的附加语,使他的话听起来“更加生动风趣”;原本是说家庭问题的一组对话,据说在Cosby的口里因为裹挟着许多的附加语,而显得“情深意厚、趣味无穷”了。
这是说消遣性谈话节目,如果是正规场合,似乎应摒弃“废话”。其实不然,这种场合可能更需要“废话”。据说,连任三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就有“废话大师”的“美誉”。他擅长用说“废话”开展工作,同各方面周旋,“创造”了一种语无伦次与模糊重复的混合物:“FED语言”(美联储语言)。
举出这些有点耸人听闻的语用案例,并非试图把“废话的功能”也推向极致,只不过是想以此引起人们对这类语言现象研究、探讨的兴趣罢了。
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信息系统,用尽量的言词传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让别人在短时间内获取高质量信息,这个良好的愿望或语用方式无可厚非,而“简洁精练、言简意丰”可以是媒介语用的一种方式(例如新闻节目),但绝不是惟一形式。从理论上以此规范广播电视媒介的一切言语、以此限定主持人语言运用的“规格”,是不妥的。于根元教授认为:“语言运用的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对语言生活认识的简单化、纯粹化,有时会导致我们语言工作的粗糙化、粗暴化。”①这是正确的论断。单纯的“简洁精练、言简意丰”,不仅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当今主持人的语用现状,也误导了语言运用与语言生活的分离。正如《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所言:“话说得太稠,圆润光滑,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流畅,天衣无缝,一眼就看得出那是语言表演。”②——真是一语中的。
一、“简洁精练,言简意丰”不是最高明的智慧语言
在言语交际中,一定的表达质量需要一定的“语量”作保证。可以说人类是最善于说“废话”的高级动物,而不会说“废话”其实是不会说话。智慧语言的主要特征不仅是直截了当的“简洁精练、言简意丰”,还在于善用“冗余”。
哈特曼认为:“所谓语言就是利用冗余信息。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为了保证理解,总是给出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信息。”③这说明,聪明的表达必会利用一定的冗余信息(又称剩余信息、羡余信息);与此相反,信息量呈满负荷状态(所谓“简洁精练、言简意丰”),并不是最佳表达形态。表达信息量与接受信息量二者之间是不可能划等号的,在大多数的语言环境里都是前者大于后者。尤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时代语境的变化导致言语表达形态的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人们都是在保证一定量的“信息差”的情况下说话的。
这样说可能抽象了一点儿,我们可以从当代人的接受心理及其信息传播过程来证明适度“废话”的作用,证明媒介语言应用中“冗余”存在的合理性:
第一,国外有关研究表明,由于当代社会物质文明的快速,视听信息刺激纷繁,“注意力经济”争夺着人们的眼球,人们普遍耽于视觉感官享受的愉悦,因此“差己经是当今中面临的重大问题”④。而且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热点不断出现,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浮躁,这就使人们的聆听耐性大为减弱。所谓“听力下降”不仅限于“企业人员”,而是“人”存在的普遍问题。这样,发挥信息冗余的调节功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信息冗余的调节方式很多,例如:用同形同义的言语方式传达剩余信息;用异形同义的言语方式传达剩余信息;用追加补充的言语方式传达剩余信息;用不同的言语代码传达剩余信息等等。将这些话语中的“剩余信息”斥之为“可有可无的废话”,是不对的。?
第二,从信息传播的过程看,言语交际行为经过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这几个环节,但处于动态语境中的这几个环节,出现一些阻滞或障碍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另一方面,由于“说话人往往很难完全确切地、百分之百地传输自己要传输的信息,而听话人也很难完全确切地、百分之百地把言语形式‘还原’为它所代表的全部信息,编码和译码只能求其最大近似值”⑤,在这样的情况下,“给出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羡余信息”更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适度冗余也是一种口语修辞的手段,在修辞学里就有“故复”和“旁逸”这类修辞格。所谓“故复”,就是以不同的方式故意反复地运用同义话语,以保证受众在视听过程中接受某种强刺激所需要的“语量”。“旁逸”是在说的过程中故意“逸”出表述主旨,说几句题外之言——如果没有这些冗余信息,话语表达过于追求简洁凝练,就很难使人们产生接受认同。而在有些广播电视节目中,那些松散的“谈话”看来是“冗余”,却可以营造一种气氛;可以是表达中的一种过渡,可以是一种强调,可以是稀释费解的信息的手段,甚至是一种属于言语美学的幽默或情调的渲染。?
广播电视是依靠口头语言进行传播的。片面地强调“简洁精练、言简意丰”,追根溯源,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语言文化观念和媒介语用观念造成的,那就是“重文轻语”和“以文为本”。口头语言与书面语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语言表现形式。口头语言当然需要规范,但那是不同于书面语的另外一种“规范”。口语按照语言法则表达,它更注意冗余的利用,成为充满创造的活在人们口头的交际语言;书面语不是口语的直接反映,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在语法、词汇、修辞等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坚持“以文为本”必然轻视“真实的口语”,他们认为,一个人说起话来越是如“文章”那样“简洁精练、言简意丰”,就越显得有“水平”;如果是包含了一些冗余的成分,就会被斥之为“没品位”或不懂得“语言美学”。在这个坚挺“理论”指导下,人们当然习惯于用书面语的“简洁精练、言简意丰”来规范广播电视的媒介用语了,包括节目主持人的口头语言,几乎是“书画语的有声版”。但是,依靠“书面稿”、在“语言保姆”的搀扶下长大的主持人,囿于“简洁精练、言简意丰”,不可能有语言才智的现场发挥和语用个性的体现,也不可能正确地运用冗余、轻松地进入“真实口语”的表达状态。但是,一切节目都是语言框架内的创造,语用观念的变化是电视观念变化的重要标志。正确发挥语言冗余的构造功能,是提高节目语用水平的重要方面。
二、废话的意义在于“没有什么意义”之外的“意义”
笔者也曾经对广播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喋喋不休地说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很觉愤然,就写了一篇《废话轰炸》的小杂文,发表在《羊城晚报》的副刊上。但是后来发现,一些节目主持人其实是故意地说废话的。他们认为,听众“宽容”废话、甚至需要废话,有时是心甘情愿地“吞”下主持人们“生产”出来的大量废话的。广东《南风窗》杂志就发表过一位主持人对此写下的一篇妙文。从行文看,作者黄茵女士可能是冲着我那篇小杂文的“有感而发”。
现引录一段如下:
“……如果说在单调贫乏的环境中广播起了一种抚慰人灵魂的作用,那么在今天这个充斥着各种声音,以至泛滥成灾的年头,广播还余下多少打动人的力量呢?我总是奇怪,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他们吞下了许许多多的废话,却觉得自己的寂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和稀释。我最感觉到迷惑不解的就是广播的神奇,毫无疑问,广播里的废话最多,你想想有那么多的电台和频道,一天24小时的狂轰滥炸……独独广播,我以为人们给予了超出相象的宽容。每一次我去做电台的节目时,我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没准真的是听人说废话而不觉得废话吧,尤其是当人们说得很有感情的时候。”⑥
在未见到学者们对主持人这类“废话”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评论之前,无意中看到李东先生的一段表述。他认为:现在“有些听众是把听广播作为消遣方式,他们在一种似听非听的状态中打发大段的时光”,因此“在这一类节目里,满足听众的心理需求是首位的,信息传播显然处于次要的地位”,这样“在语言的运用上就不是着眼于信息的明晰,而是追求感情的酣畅和理想的氛围”。⑦
据了解,李东先生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他对广播语言与媒介特性的颇有时代气息的领悟,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他“部下”的观点。?
黄茵和李东的话是不是奇谈怪论?如果我们不是“固守”某些传统观念而始终保存惯性的语言歧视,就会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他们的观点是对广播媒介某种功能或特性的一种“发现”,也可能是对当今社会语境中受众接受心态的一种理解。媒介语言研究应当面对现实,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受众视听心理发生的变化,这样就不会拒绝“废话功能”一类课题的探讨了。
从符号语言学的角度说,任何人说出口的任何话都是有意义(意思)的,“没有意义”的话是不存在的。但是由于“教化意识”和社会意义评价的强势介入与主宰,人们从来都以主流政治文化价值作为意义评判的标尺,而将其他的话语意义一概斥之为“没有意义”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社会语境的改变要求我们摒弃那些带有“后革命”印记的语用观念,确立富有时代意义的语言评判尺度,简而言之,要求我们来一次对语言功能和媒介功能的“再发现”!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其中之一是,不应该将语言只看作是传播信息的“工具”,那是不全面的。语言不仅仅是主流价值意义的载体,它无所不在,它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维特根斯坦说得好:“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所以,选择一种语言就是选择一种文化价值,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可以具体化为对语言功能和语言运用方式的重视。
作家汪曾祺说过这样一段话:?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把语言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我们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⑧
——不管你说了什么,你的语言本身就是“内容”。这是一种发人深思的语言观,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语言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用来说着玩儿;用它解闷儿,打发时光。比如谈天气、谈陈年往事、谈奇闻趣闻,什么都谈——这个“功能”开发得比较充分的眼前的例子,当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如果说这个节目非常优秀尚难苟同,但是这个节目的“创意”在于,他们“故意”地把有用的内容和“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放在一块儿做出节目来,获得了效益。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没有什么意义”——承载过多的“意义”,可能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说闲话或“侃大山”是人类最古老、最方便的休闲、消遣方式,是一种市井化的自娱文化形式,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那些城市“白领”把业余时间与财富、业绩挂钩,他们还有更“高级”的娱乐方式,只有一般市民才用大量的时间听广播、守着电视——的广播电视节目主要是办给平民看的这个基本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当人们百无聊赖或心里面闷得慌时,以轻松的聊天方式,或发挥话语的“游戏功能”制作出来的节目,里面多少也包含着文人们经常说的“人文关怀”。即使是“插科打诨”,在文艺、娱乐或消遣类节目中,“插科打诨”是一种幽默与诙谐,可以益智。李渔说:“科诨非科诨,乃看戏人之人参汤也。”此非虚妄之言。怎能将这类节目一概斥之为“废话轰炸”呢?毛喻原先生说:“汉语本身的缺陷与几千年的专制话语体系有很大的关系。汉语从来也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存在的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潇洒、逍遥,着实让人吃惊。”⑨这是十分深刻、中肯的批评。??
三、适度“废话”是“同构策略”,但语用层次有高低之分
脱离不同的语境去规定广播电视的语言运用的理想范型和规则,是十分轻巧方便的事情,但这不利于节目的语用实践和创新。随着主持人节目的更新与,他们大胆的语言实践早已把那些“理论”和“规则”抛在一边,而是按照媒介特有的“游戏规则”朝前走——他们强化了语言应用的经验取向和实用性格,我们不应回避、漠视这样的语用现实。尽管权威们一味强调说话必须“简洁精练、言简意丰”,却阻挡不了媒介语言多元共生、多体混成局面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用陈旧的条文去“规范”是徒劳的,而依靠整体的创造与整合,依靠理论的与必要的引导,才可能推动语言演化朝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如前所述,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是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反映的是一种民族风情和社会情绪。比如英国气候多变,英国人说话就喋喋不休地说天气;前些年中国人生活多艰辛,开口爱说的是柴米油盐;现在青年人爱说时尚、老人爱说往事、股民闲聊股事等等,媒介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当我们开掘节目资源的时候,说群众爱听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废话”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同构策略”。当然前提是有公平的尺度,才可能有“废话”不“废”的评判。而在这些节目中,追求所谓“言简意丰”则是错误的语用选择。
我们从语用功能的角度肯定了冗余或“废话”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测定媒介传播行为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应该是把握冗余信息的“度”。适度的信息冗余可以在传播和交际中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超度的剩余信息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流向低俗或鄙俗,这就是“有效冗余”与“无效冗余”的区别。?
允许信息“冗余”的存在,并不是指言语生成就是“用有限的手段生成无限的句子”——当前部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有一种超限生成大量“废话”的“本领”,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素养的低下和思想的贫乏。那些“无限生成”的语句,一般是以极少的“语料”使言语生成无限扩张;他们依靠的“有限的手段”,一是“散点式”,“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二是充分运用语言的“递归性”(recursiveness),其表达结构循环往复,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又说回来,然后又在原有的起点顺着说下去。广东有句民谚,叫作“口水多过茶”,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我国广播界的关注。
去年夏季,国内50多家广播电台的代表汇聚乌鲁木齐市参加“全国广播谈话节目研讨会”,《会议纪要》指出:近10多年,由于大量系列台的开办,吸收了大量非本专业出身的人员匆匆上岗,主持人的“量”与“质”的比例失调。一些节目主持人素质偏低,“常常是嘻嘻哈哈大篇闲扯,有的是胡说八道,男女主持人打情骂俏,污染了听众的耳朵,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不抓紧提高节目主持人的素质,就会给精神空气造成污染。”
这说明“可有可无”的冗余或所谓“废话”,是应该划分出不同的语用层次的:有的是为了缓解情绪、为了稀释内容、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有的是用无害的“段子”或语言的游戏为听众打发闲暇的时光;但有的却是为了自我张扬、炫耀卖弄;有的是开口皆陈言,用“废话”掩饰内容的空洞与苍白;有人甚至是故意用一种所谓“充满性感的、带有磁性的声音”、或者是“死魂灵的声音”(引自《南风窗》另一文章语)滔滔不绝地胡说八道——那其实是对广播工作的亵渎,反映的是庸俗不堪甚至病态的语用心理,是对受众的轻慢和极不尊重。
广播电视媒介通过口头语言传播的当然应该是有一定质量的信息,不是无节制的、潜意识的思维语言的直接外泄。在任何情况下,主持人的话语都缺不了“过滤”和“加工”的环节。他应当在表述中正确地利用冗余,他是“废话”的主人,而不是“废话”的奴隶;他的冗余或所谓“废话”应当始终接受理性的监督。把该说不该说的、可说可不说的一古脑儿都通过喋喋不休的“语流”倾泻出来,这些可能在生活中允许存在的“废话”,与主持人节目中允许存在的冗余(“废话”)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也是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
——可见,说“废话”也需要技巧,甚至是一种“”。
注释:
①于根元:《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载《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
②莎莎:《崔永元不会表演》,《南方声屏报》1999年58期。
③《语言与语言学词典》2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④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446页,陕西出版社,1987年。?
⑤范继淹:《语言与信息》,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
⑥黄茵:《说广播》,载《南风窗》杂志,1996年第10期。?
⑦李东:《走出魔圈》,载《主持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⑧转引自《随笔》2000年第3期,37页。?
⑨毛喻原:《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载《读书》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