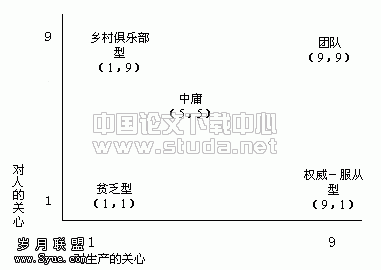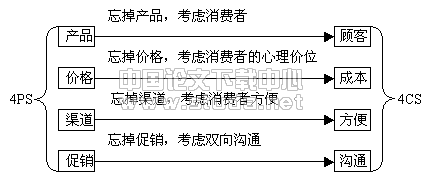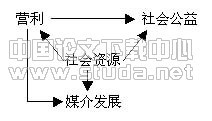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美观照
【内容摘要】“审美观照”是一个颇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审美范畴,在学术界被广泛运用,但却并未得到学理上的建构与阐析。“观照”这个概念来源于传统美学。审美观照是在创作中摄取、形成审美意象的重要途径。审美观照不是一般的观看、观察,而是审美主体在进入特定的审美情境之后,以充满独特情韵的眼光来看对象物的观赏与晤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审美观照的主要方式,是“仰观俯察”、“远观近察”的“流观”。中国的审美观照方式与传统中的道家、佛学与都有某些内在的联系。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韵味与意境,是与其独特的审美观照方式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审美观照;观照方式;仰观俯察;远观近察
一、“审美观照”的涵义与“观物取象”
审美观照,是一种重要的审美活动,是审美主客体之间发生实践性联系的特殊方式。中国古代诗论、画论中在这方面有十分丰富的资料,却并无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概括。在当代的美学论著中,多有使用“审美观照”这个概念者,却同样缺少关于“审美观照”这个概念的理论建构。而笔者以为,“审美观照”是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当代理论活力的美学理论范畴。
无疑地,中国古典美学有着广大而渊深的理论资源,很多资料至今对于艺术创作和当代的中国美学的,仍有源源不断的借鉴价值。但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很多概念,尚处于前理论的状态,以一种经验的、未经抽象的形式存在着,如同未经提炼的矿藏。然而,这些概念的存在,却是美学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美学在当代世界美学格局中的地位与突进,有赖于传统文艺美学中的范畴的升华与理论提炼。“审美观照”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范畴。
什么是“审美观照”?这是应该从学理层面加以厘清的。“观照”是一个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它的来源出自于佛学。《辞海》中的“观照”辞条说:“观照:佛教指静观世界,以智慧照见事理。”这个辞义是来源于佛学辞典的。丁福保《佛学小辞典》中即说:“以智慧而照见事理,曰观照。”观即“止观”,这就要求主体以般若智慧直观事物,而直接洞照事物的本质。如《坛经》所云:“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菲起诳妄,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道。”指的便是不借助于理性解析的直观体验。而“审美观照”这个范畴在中国古代的美学资料并无直接的存在,更多的是以“观”等说法指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独特的观审角度与方式。
审美观照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摄取、形成审美意象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审美创造主体对于对象物的观照,审美意象是很难形成的。“观物取象”是关于“审美观照”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周易》已提出“象”与“意”的关系问题,其中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①这里将“象”作为表达“圣人之意”的最重要的因素。《周易》中所说的“象”是卦象,而非艺术形象,但却是与艺术形象或审美意象相通的。“立象尽意”之说对后来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是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的。正如李泽厚、刘纲纪先生所分析的:“《周易》所说的‘象’虽非艺术形象,却同艺术形象相通。其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出于什么巧合,而是因为《周易》中大约始于殷商的各个卦象,经过《传》的阐释发挥,已不只是为了定吉凶而已,而且成为整个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象征,俨然构成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模式了。而《传》的作者们既然企图用殷周遗存下来的卦象来解释和人类社会,特别是解释奴隶主阶级理想中的文明社会,他们就不可能把‘文’或美的问题撇开不管,因而使得《周易》所说的‘象’既包含着对现实事物的摹仿(以符号指谓象征现实的形象),同时又有美的因素,涉及了自然和社会中的美的事物。这样,《周易》所说的‘象’就不只是卦象,而同时具有美学的意义了。”②这种分析,应该说是较为客观的,这从中国艺术理论中对于意象的重视及“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方式对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就可以得到印证。
《周易》中所说的“象”是对客观现实事物的一种反映与摹仿,如《系辞》中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是,像也。”意思是《易经》的内蕴是卦象,卦象是用卦来象事物。但是,《周易》之象并非仅是对事物表层形象的摹写反映,而是对事物深层蕴含的符号化彰显。《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所谓“赜”,是指幽深复杂的事理。在《周易》作者来看,“象”是圣人发现天下幽深难见的道理把它譬拟成具体的形象,用来象征事物适宜的意义。如果仅是对外在形象的摹写与反映,那就没有多大价值了。易象又是以之表明事物变化的征兆。《系辞》上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因而,“象”是作为事物变化的征兆而被人们加以把握的。
易象是“观物取象”的产物。它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的摹仿、反映,一方面又是主体创造的结果。《系辞》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是《易经》中“观物取象”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它指出了“观物取象”是对外物的观察、摄写,同时,也以此沟通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段论述还将“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留给后人,成为中国艺术创造过程中关于审美观照的基本方式。叶朗先生曾分析了“观物取象”的三层意思,指出:第一,观物取象说明了《易》象的来源。《易》象是怎么来的呢?是圣人根据他对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的观察,创造出来的。《易》象是“圣人”的创造,但并非是圣人的自我表现而是对于宇宙万物的再现。这种再现,不仅限于对外界物象的外表的模拟,而且更着重于表现万物的内在的特性,表现宇宙的深奥微妙的道理(“天下之赜”,“万物之情”)所以这种再现就带有很大的概括性。第二,“观物取象”说明《易》象的产生既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观”就是对外界物象的直接观察、直接感受。“取”就是在观的基础上的提炼、概括、创造。观和取都离不开象。第三,“观物取象”还说明了“观物”所应采取的方式。③“观物取象”的命题说明观照与意象创造之间的密切关系。观照的目的和结果都是审美意象的创造。
二、审美观照与主体心境
审美观照不是一般的观看、观察,也不是一般的浏览,而是审美创造主体在进入特定的审美情境之后,以充满独特情韵的眼光来看对象物时的观赏与晤对。观照不只是用眼,更是用心;不仅是对于对象的映入,而且是以特有的角度将其改造成以此一对象为原型的审美意象;不仅是以对象物为观赏的对象,而且是与对象物彼此投入,形成物我两忘的关系。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瞻万物而思纷”的“瞻”,即是一种审美观照。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也是一种审美观照。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审美观照,苏轼的“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也是一种审美观照。而主体的态度,对于审美观照来说,又是尤为重要的。
排除欲念纷扰、空明虚静的心胸,对于审美观照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老子》中所说的“涤除玄鉴”(或“览”),的命题,虽然不是就审美而论的,而是对“道”的观照;但它却对中国美学中关于审美态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涤除”,就是洗去心灵中的各种欲念或成见,使头脑像镜子一样空明澄静。“鉴”本意是镜子,引申为“观照”之意。高亨先生说:“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④“涤除玄鉴”,是关于审美观照的最早理论渊源。这里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三层含义:一是主体的虚静心胸的空明澄静;二是主体与客体的相关性,观照一定是相关于某个对象物的;三是观照是蕴含着主体智慧的直观,而非知性分解。《庄子》也以“虚静”为观照的主体条件,《天道》篇中云:“圣人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乎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由于主体心灵的虚静,才能呈现出一种观照对象的心胸。由《庄子》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主体的虚静心态,使观照不止于具体的对象物,而是以具体的对象物涵容万物,统摄万象。《庄子·天地》篇又云:“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与万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所谓“独见”、“独闻”,即是以空寂虚灵之心对于对象的视听。而由这种“独见”、“独听”,则可以感受万物的。郭象注曰:“若夫视听而不寄之于寂,则有黯昧而不和也。”⑤成玄英疏云:“虽复冥冥非色,而能陶甄万象,乃云寂寂无响,故能谐韵八音。”⑥都指出了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态所做的观照,不仅是对所观对象物的观赏映照,而且,可以涵容万物,吐纳万象的。王羲之《答许询诗》中说:“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⑦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的“赞”中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以养。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养气》篇是说保养精神以使神思顺畅,但也关涉着创作主体对事物的观照。“水停以鉴”,是以水之平静为喻,以形容作者的心意闲静才能更好地观照对象。
三、“仰观俯察”与“远观近察”的审美观照方式
审美观照的重要问题是观照的角度与方式。《易经》中所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开创了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种典型的方式,即是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易经》所说的是卦象的取象的观照方式,但却对以后的艺术创作(尤其是诗、画)时的观照,形成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审美主体以宇宙天地为其观照的对象,而非专以某一物为其固定的观照对象,这样,就使所取的意象至为阔大,充满寥廓的宇宙感,同时,也使审美主体成为整体的意境的中心。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即是典型的仰观俯察式的观照方式。宋人范文曾举出了诗中的若干诗人以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所取的诗中的审美意象:“苏子卿诗:‘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魏文帝云:‘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云:‘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敬祖云:“‘仰视垣上草,俯察阶下露。’又:‘俯临清泉渊,仰观嘉木敷。’谢灵运云:‘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又:‘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辞意一也。”⑧范氏所举这些诗例,都是俯观仰察的观照方式。嵇康的《赠秀才入军》中多有以俯观仰察的方式而得到的意象:“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田,其乐只且。”“仰讯高云,俯托轻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⑨再如其诗中的“俯漱神泉,仰琼枝。栖心浩素,终始不亏。”⑩嵇康诗中的这种俯观仰察是与其“游心”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诗中,多处出现老庄哲学味道甚浓的“游心”字样。如说“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11)“游心大象,倾昧修身。”(12)“游心太玄”是与“俯仰自得”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的。王羲之著名的《兰亭诗》中也是以俯观仰察的方式来创造意象的:“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等等。这种俯观仰察的观照方式,造就了有广阔空间的意象,而且是以主体为中心的高下二维的广阔空间。主体的观照角度是稳定的、是站在一个基点上的。宗白华先生对此曾有精妙的论述,他说:“早在《易经》、《系辞》的传里已经说古代圣哲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13)从美学的角度将这种“俯仰往还,远近取与”的观照方式,揭明为中国哲人与诗人的独特观照法。宗白华先生还举了这样一些诗歌创作中的有关例子:“左太冲的名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也是俯仰宇宙的气概。诗人虽不必直用俯仰字样,而他的意境是俯仰自得,游目骋怀的。诗人、画家最爱登山临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唐诗人王之涣名句。所以杜甫爱用‘俯’字以表现他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他的名句如‘游目俯大江’,‘层台俯风渚’,‘扶杖俯沙渚’,‘四顾俯层巅’,‘展席俯长流’,‘傲睨俯峭壁’,‘此邦俯要冲’,‘江缆俯鸳鸯’,‘缘江路熟俯青郊’,‘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等,用‘俯’字不下十数处。‘俯’不但联系上下远近,且有笼罩一切的气度。古人说: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诗人对世界是抚爱的、关切的,虽然他的立场是超脱的、洒落的。晋唐诗人把这种观照法递给画家,中国画中空间境界的表现遂不得不与西洋大异其趣了。”(14)将中国诗画中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加以集中地讨论,并指出其与西洋艺术的区别所在。韩林德先生则在《境生象外》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审美观照方式,称之为“仰观俯察、远望近察‘流观’观照方式”,将其作为华夏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华夏民族对天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审美观照,大体上都是持仰观俯察、远望近察的‘流观’方式。……事实上,仰观俯察、远望近察这一‘流观’方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观照世界的一个模式(定势),已经自然而然地支配着我们民族审美活动的开展,也就是说,不但在对于天地自然和艺术美的观赏中持这一观照方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物的审视,也大抵持这一观照方式。”(15)
“流观”的观照方式,除了有稳定视点的仰观俯察之外,还有审美主体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中的观照。这种“游观”,使诗人或画家所创造的意境更加富于变幻,呈现出多姿多采的风貌。画论中所说的“移步换形”,即是指主体身位的变化带来视点的游移,而使所见呈现出的多面景观。如果说仰观俯察主要是固定视点的上下观照,那么,远望近察则更多是主体的位置不断变换而得到灵幻多变的意境。张法先生对此作了更细的分析,他说:“这种俯仰远近的游目,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游’,一是人之游,中国人不是固定地站在一点进行欣赏之观,而是可以来回走动地进行欣赏之观。……游目的另一意义就是人不动而视觉移动。”(16)远望近察明显是属于前一种。董欣宾与郑奇先生也于此有颇为精妙的见解:“仰观俯察,属于相对静观;远取近求,属于辩证动观。俯仰远近,使人的感受与认识领域通向了上下东西南北中四荒八极的宏观追索。无怪乎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是不定时不定点的任意游移性心理透视观。只有这种透观,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现中国人观察事物的深广度以及综合事物、把握事物的强大的主观能动力量。观属于宏观,察属于微察,观之察之,是一种宏观与微观贯通的天地,宏观可取气势、驾驭关系,微观可得性情,把握质性;宏观求宇宙之大,微观求品类之盛;宏观达万物之表,微观入万物之里。于此可见中国画观察方法的博大深微所在。”(17)这里的论述使审美观照方式的认识得到了进向纵深的进展。
以分解的眼光来看,这种远望近察的游观方式,使诗人、画家们所取的审美境界,与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相比,或许是更为浑灏汪茫、灵动变幻。视点的自由移动变换,使作品的意境既有浑茫阔大的气势,又有细致入微的妙观。正如王夫之所说的:“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18)又论谢诗谓:“广远而微至”(19)适可说明远望近察的观照方式所取的意境的特点。且如陶渊明诗中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20)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睛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21)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22)苏轼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催。”(23)等,都是以远望近察的观照方式而得到的意境。
在远望近察的观照方式之中,“远”受到格外的重视。这是因为,远观能够得到十分独特的审美境界。审美主体在较远的距离来观照对象,可以使对象呈现为模糊朦胧的氤氲,亦可其有着咫尺万里的“远势”。刘宋时期的著名画论家宗炳有这样论述:“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24)宗炳的这段话有相当深刻的意义。宗炳在这里首先指出的是,对山水的观照目的是以山水的形色而为山水画的形色,因而便应盘桓于山水之间作细致的观察,对山水的形色了然于心。“盘桓”这里是身入山水之境远近逡巡,“绸缪”是细察其景的意思。宗炳又远观与近取的差别。当然,宗炳是主张在对山水的观照中以远观取其势的。如以面对昆仑为例,以昆仑之大,眼睛之小,如果将眼睛逼近方寸去看昆仑,那就会根本看不清山之形貌;而如果站在数里之外的距离来看,山的形貌与气势,都可以进入眸子的“取景框”之中。“去之稍阔,则所见弥小”,这里揭示了在绘画学中近大远小的透视学原理。这个命题现在来看,实在是最为基本的道理;可是从中国画学史上,此前无论是从创作还是理论,这种意识都还是很模糊的。真正在理论上加以如此明确的揭载的,宗炳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还应指出的是,宗炳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意旨,并非仅是以较小的画幅来表现山水之形,而是在其形质之中生发出山水的灵韵气势。在宗炳看来,主体所晤对的山水,不仅是形质的存在,而且是有着神韵灵趣的,正如他在《画山水序》中所说的“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宗炳所要着力表达的意思,不止于“徒患类之不巧”,而更在于“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所谓“似”,这里尤应加以深入理解。我认为宗炳这里主要是强调不应由于画幅之小而影响表现山水的神韵气势。我非常赞同陈传席先生的阐释,他这样说:“‘似’字,一般应释为‘相似’,‘类似’。但此得不可简单地作如是解。如解释为:‘不因绘制小幅而影响其原山水相似的话,则无甚意义。历来画山水,画与真山水相当大者绝无,其他画和原物相当大者亦极少,故这话毋须宗炳来讲。姚最《续画品》评萧贲云:‘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杜甫诗《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云:‘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故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此语可以帮助我们对’不以制小而累其似的理解。宗炳的‘似’,联系上下文一看,便觉了然,乃指‘千仞之高’、‘百里之迥’之势。是说不因画幅小而缺乏‘千仞’、‘百里’之势,否则与地图何异?所以宗炳接着便说:‘此自然之势如是。’一‘势’字宜着眼。”(25)陈传席的理解是能够得宗炳之真髓的。宗炳所说的“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表明了宗炳的美学追求不在于形似,而在于以画幅钟集山水之神韵。“秀”不在山水之形的本身,而在于其所蕴含的神气;“玄牝”,在老子哲学中以喻形而上的本体。《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吾师张松如教授解释“玄牝”云:“玄牝,微妙的母性;指天地万物总生产的地方。”(26)其实,“玄牝”就是指作为万物本根的“道”。《老子》第一章中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陈鼓应说:“‘玄牝之门’,‘天地根’,是说明‘道’为产生天地万物的始源。”(27)宗炳所说的“玄牝之灵”,是指超越于有形的山水之质之上的灵韵。而这些,是需要“迥以数里”的远观才能得到的境界。与此相近的是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所提出的“远”的审美效果:“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28)远处观之,无论是人,是树,是山,是水,意境都是较为模糊的、朦胧的,却也因此而产生了“蓝田日暖,良玉生烟”的审美境界。
谈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观照方式,不能不涉及到宋代著名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出的有关观点。如人们所熟知的,郭熙提出了著名的“三远”说,即“高远、深远、平远”,这是郭熙所出的山水画家在观照山水时的三种不同的远观的审美观照方式,对于山水的艺术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实际上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阐发的绘画理论,有更为丰富的美学意义。对于山水画创作中的审美观照问题,郭熙的看法是颇为全面而深刻的,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中,也有不同寻常的价值所在。在郭熙看来,自然山水是气象万千、千姿百态的,只有对山水做全方位、多侧面的深入观照,才能真正把握山水之美的真谛所在。因此,他并非单纯地推崇远观,而是对“远望”和“近看”作了辩证的分析。不仅如此,他还对从各个侧面来看山和四时看山之不同,都作了分析。郭熙如此说: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川谷,远望之以取其深,近游之以取其浅;真山水之岩石,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玩习不能究一川径隧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睛远望可尽,而近者拘狭不能得一山明晦隐见之迹。(29)
在这段论述中,郭熙首先指出了画山水与画花、画竹的观照方式的不同。相对而言,画花、画竹时,对花、竹的观照方式较为简单一些,而画山水却须亲临山水以做各个角度、各种质素、各个季节的全方位观照。川谷、岩石、云气,远望与近观,春夏秋冬四季,都会对审美主体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郭熙不仅是重视“远望”的观照方式,而且也辩证地看到“近看”的效果。远望可以得山水之势,近看则可以山水的形质,都是不可缺少的。四时看山水的烟岚景象是有很大不同的,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这都是山水四时的整体意态。远望可以得其势,近看可以得其质,不仅是对山水的岩石来说的,也有着普遍性的美学意义。当然,全面地看郭熙的画论,他还是更为重视“远望”的观照方式的。“山水之势”是其山水画的追求目标。所以他强调“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郭熙进一步指出移步换形地看山的观照方式,他说:
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30)
这里,郭熙所主张的是变换各种角度、各种方位来看山,这样可以得到山的千姿百态的不同风貌,从而产生了观照山水时的美感的丰富性。同时,这种形步换形的观照方式,还可以使某个个体的山,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兼数十百山”的审美效果,达到“以少总多”的审美效果。
郭熙又提出著名的“三远”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重叠,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为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郭熙对“远望”的审美观照方式做了进一步的区分,也即“高远、平远、深远”。所谓“高远”,即是仰视看山;“平远”即是平视看山,“深远”则是平视看山。这在绘画透视学上是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正如葛路先生所阐释的:“三远法是中国透视学的总结,具有民族的特点。它给画家观察自然景物以充分的自由。仰视山颠,可见山势突兀,山色清明;俯视山后,可见层峦叠嶂,山色重晦;平视远望,可见景象渺茫,山色有明有晦。当画家饱游饫看,所经众多,进入艺术表现阶段,三远法又给画家经营位置以广阔天地,”(31)三远之中,又以平远最为佳境。这是因为,“平远”的审美观照会给画面产生“冲淡”的审美效果,即是郭熙所说的“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郭熙本人的画作亦多以“平远”为题,如《夏山平远》、《秋晚平远》、《平远秋景》、《雪溪平远》、《风雪平远》等,足见郭熙对于以“平远”为观照方式进行创作的重视程度。
四、的审美观照的某些因缘
在中国的审美观照方式上,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道家的、佛家的、的思想方法,都对中国艺术创作中的观照方式有着难以剥离的影响。如“游目”、“流观”的观照方式,与庄子哲学上的“游”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韩林德先生曾于此举了很多相关的例子,他说:“如东汉张衡《思玄赋》云:‘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李善注:‘冯衍《显志赋序》曰:’游情宇宙,流目八。’西晋张华《答何劭》云:‘属耳听鸣,流目玩鱼。’唐李白《荆门浮舟望蜀江》云:‘流目浦夕烟,挂帆海生月。’战国屈原《哀郢》云:‘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东晋陶渊明《读山海经》云:‘泛览《周公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还有称其为‘身所盘桓,目所绸缪’的,如南朝宋宗炳的《画山水序》。以上各家所言,字面虽微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在特定的审美活动中,主体观照客体对象,其身体是盘桓移动的,其目光是上下流动、往复推移的。诚如程泰万《水墨壑图》题诗所言‘看山若不足,步步总回头;看水吟不足,将水逐溪流。’这是一种‘流观’,而不是西方油画家的‘焦点透视。’”?(32)
这种在中国的诗画艺术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的观照方式,是与道家哲学中“游”的思想有深刻的内在渊源关系的。“游”作为精神自由的象征,在庄子哲学中成为基本的命题之一。《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而所谓“逍遥游”正是精神的自由解放。《逍遥游》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自由。这种“游”,也是以身体的遨游为特征的。《庄子》中描述到“藐姑射山之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个“游”,显然是身体之游。徐复观先生在阐发庄子艺术精神的时候,以“精神的自由解放”作为“游”的精神本质,虽然未免失之肤廓,却也道出了其中意味。在嵇康诗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老庄思想与“游心太玄”之间的联系。如说:“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33)又说:“羽华华岳,超游清宵。云盖习习,六龙飘飘。……齐物养生,与道逍遥。”(34)“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惟龙化,荡志浩然。”(35)都有力地说明了嵇康的“游”,是与老庄哲学分不开的。
审美观照中的“返照”、“以物观物”、“物外之赏”等方式,深受佛学、理学的观念影响。如唐代大诗人王维,笃信佛教,于佛学造诣精深,曾有很多佛学著述,如《能禅师碑》、《西方变画赞》、《绣如意轮象赞》等。王维的诗歌创作艺术思维也渗透着佛学的痕迹。“返照”,是王维诗的一种独特的观照方式。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其实都是以“返照”作为审美观照方式的。所谓“返照”,在佛教禅宗里是基本的“悟道”方式。禅宗的“悟道”,是一种对于自心的“返照”,欲将自身蕴含的佛性,转化为成佛的现实性,必须是自性的开悟,而不应该舍弃自心,向外觅求。《坛经》云:“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本性,即是小根人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有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禅的“顿悟”,即是通过对自心的“返照”,使自在的佛性得以发显,如同拂去迷雾而见日月之明。禅之“悟”即是对内心的观照(而非知性分解),如果不得自悟的话,便应以般若之智进行观照,观照的对象仡是悟道者的“自性”,而非外在的客体。《坛经》又云:“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有真正善知识,一悟即知佛性也。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好得解脱。”指出了禅的顿悟是对自身“佛性”的“返照”。而在诗歌创作中,也作为一种艺术观观照方式而有了独特的韵味。
宋明理学的“观物”、“静观”的思想,与禅观是互相渗透、互相汲纳的。如理学大师邵雍提出“观物”的思想,有著名的《观物内篇》和《观物外篇》。在《观物内篇》中,他提出“以物观物”的命题,其云:“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他又在《观物外篇》中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所谓“以我观物”就是带着全人主观意欲偏好来看事物,在邵氏看来,这样的观察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以物观物”,就是淡化观审主体的主观偏好,而按着事物本来的样子来观照事物,也即是去除观照中的主观因素,也正是邵氏所说的“安有我于其间哉”。而从审美观照的角度来看,则正与西方美学中的“心理距离”说可以相通。程颢也以“静观”为其“感兴”产生的审美契机,他在《秋日偶成》诗中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静观”与“以物观物”是有其内在的一致之处的。苏轼、黄庭坚也都有着以超越心态来观审事物的审美观照态度。苏轼对事物主张作物外观赏,他在《超然台记》中有这样的有名论述:“凡物皆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甫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余之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物外之观,主要是说主体心灵的超越。著名的《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表达了诗人这种看法,认为只有站在事物之外,才能得其真实面目。苏轼还在有名的《送参寥师》一诗中谈到:“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这是以佛学的“空静”观为其底蕴来说明创作中的审美观照的。黄庭坚作为一个大诗人,又是禅学中人,在其作品中时常以“物外之赏”的观照态度来创造诗的意境,如说:“主人心安乐,花竹有和气。时从物外赏,自益酒中味。”(36)又云:“黄叶山川知晓秋,小虫催女献功裘。老松阅世卧云岭,挽著沧江无万牛。”(37)这样的一些篇什,都是借禅学的眼光以作物外之观的。
审美观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一个广泛的存在,是艺术家在审美创造活动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它不具有能够以解析的方法可以诠解的性质,却是一种高级的审美直观。审美观照,有时可能是以具体的目光来看外物、发现独特的意境,画家更多属于此类;有时则是以心灵与外物的关系为依据来谛视世界,构筑更有虚灵意味的审美境界,诗人更多的属于此类。“观照”是审美主体的视觉与外物的直接相触,用王夫之的话是一种“现量”,但它不是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而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来把握外物的美的属性,或者称之为“目击道存”。中国文学艺术有其独特的韵味、独特的意境,是与独特的审美观照方式有密切关系的。
注释:
①《周易·系辞》上。
②《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
③见《中国美学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74页。
④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98页。
⑤⑥《南华真经注疏》236页,中华书局排印本1998年版。
⑦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9页。
⑧《对床夜语》卷二。
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3页。
⑩《诗》,同上,第491页。
(11)《代秋胡歌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0页。
(12)《四言诗》,同上,第484页。
(13)《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见《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
(14)《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艺境》,第228页。
(15)《境生象外》113-1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17)《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18)《古诗评选》卷二评谢灵运诗语。
(19)《古诗评选》卷五。
(20)《归园田居》。
(21)《终南山》。
(22)《登高》。
(23)《有美堂暴雨》。
(24)《画山水序》),见《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25)《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6)《老子校读》,引自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
(27)《老子注译及评介》,第86页。
(28)《山水论》,见《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29)(30)《林泉高致·山水训》。
(31)《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32)《境生象外》,第109页。
(33)《代秋胡歌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9页。
(34)《四言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485页。
(35)《四言诗》。
(36)《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
(37)《秋思寄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