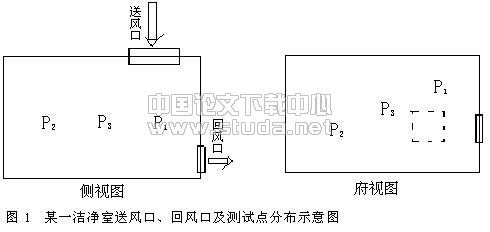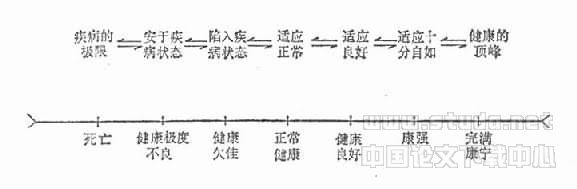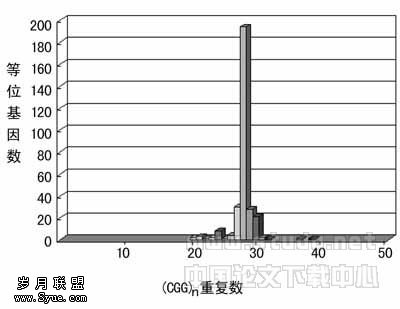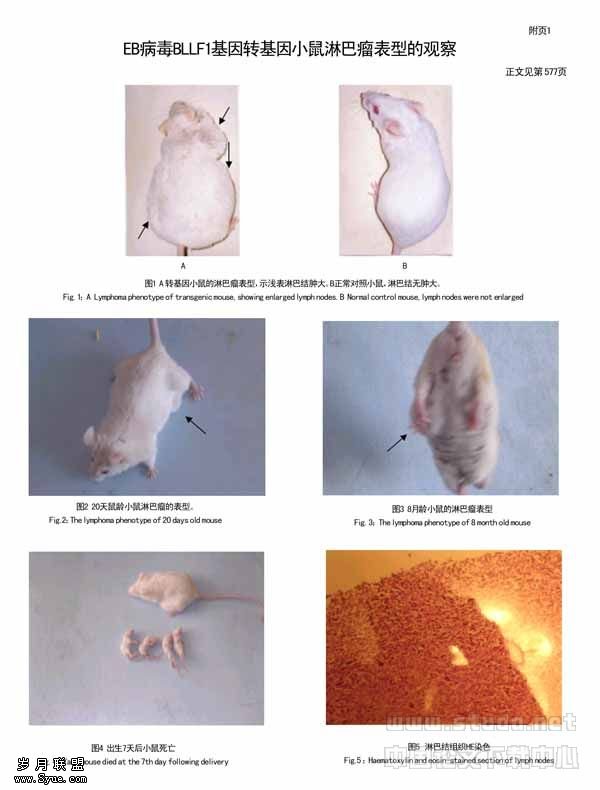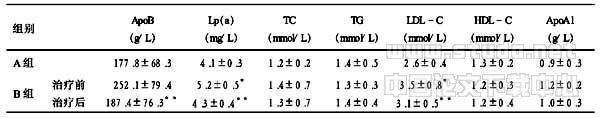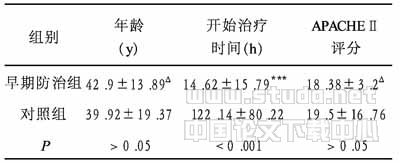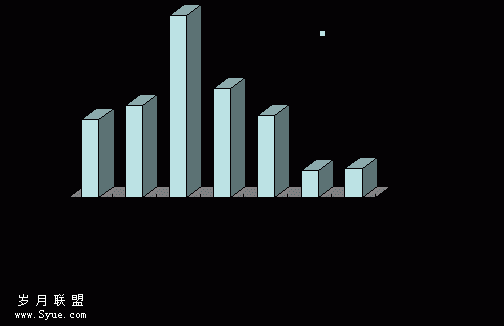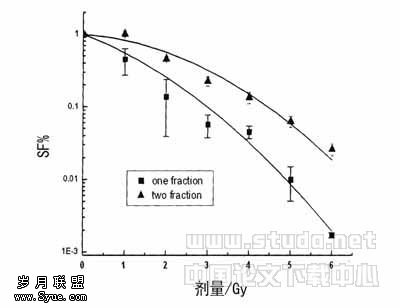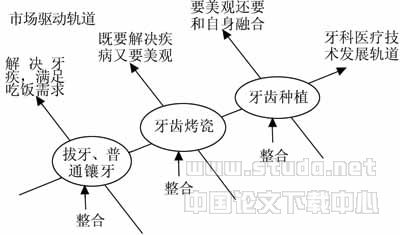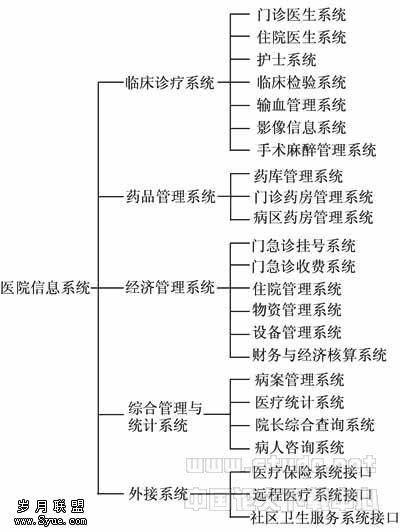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现状的反思与前瞻
【摘要】 回顾中医儿术的,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现状,从中西医结合、医辨证论治、教学与科研、继承、发扬、创新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反思,以推动中医儿科学术向前深入发展。
【关键词】 中医儿科学/发展趋势; 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术发掘; 辨证论治; 辨病; 辩证
自扁鹊为“小儿医”以来的2 400余年中,中医儿科学经历了起源、奠基、形成、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自成体系。同时,中医儿科学领域的多项成就,从钱乙的脏腑辨证论治纲领与创立的五脏虚实补泻方剂,以及钱乙的脾胃学术思想,到叶天士《幼科要略》中关于小儿四时病症的诊治而发展成温病学说等等,又为推动整个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儿科学体系而论,中医儿科学还创立了多项世界记录,如隋唐时期已经有多部儿科学专著问世,已在太医署正规培养5年制少小科专科医生;宋代建立了理论与临床内容完备、水平较高的儿科学体系,刘昉的《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儿科学巨著;明清时代儿科学术水平快速发展提高;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及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应用等等。人类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医儿科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又面临机遇与挑战。
如何面对机遇、面对挑战,如何与时俱进,使中医儿科学术健康发展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儿科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回顾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历史,面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现状,进行检讨与反思,很有必要,它将有助于向前探索与发展。
1 关于中西医结合
东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构成了东西方几乎完全不同的中西医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中西医的理论体系是东西方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人体生命科学的不同认识,但都能达到防治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自20世纪开始,西医文化的大量进入,给中华土地上的中医文化带来巨大撞击。虽谓“殊途同归”,但毕竟“道不同”、认识不同。古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医学领域却不能“不相为谋”,如何沟通,互相促进,达到真正的结合,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应当是大有裨益的。因此,20世纪开始便提出了“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大抵在20世纪前半叶,是以理论认识上的对照“汇通”为主,后半叶则在医疗、教学、科研领域里,“中西医结合”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这种“主要的形式”的实际内容,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病名的对照;运用西医的认识来解释中医;运用西医西药的理论来研究中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临床上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等。因此在近50年来,虽然“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中西医在理论上、在临床上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结合点,离中西医结合的理念还相距甚远。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与思路,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怎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结合点,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取长补短,达到真正的有机结合,是当今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1.1 关于中西医病名对照 中西医病名对照,是中西医汇通的第一步。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自20世纪初即开始了中西医病名的对照汇通。1918年出版的顾鸣盛撰著的《中西合纂幼科大全》,即将中西医儿科病名作了初步的对应,1947年沈伯超著《儿科更新》则几乎主张以西医病名替代中医病名。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则几乎达到中西医病名双重诊断。
应当指出,西医在认识疾病上,由于科学的进步,微观的认识比较细致、直观、可取。虽然有许多未知认识,但就已知的得到科学证实的疾病认识,已得到公认。这些认识,基本上揭示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变化,应当说西医病名的认识更为客观、直观。实际上,中医病名的认识,经过一两千年临床检验而确立的病名,也揭示了中医的认识规律。因此许多病名可以相通、或可相近,比如天花、麻疹、水痘等,就可相通;其他大量的病名,如厌食、腹泻、水肿、肺炎喘嗽等等就可相近。中医病名以证的认识为主,而证的认识包涵的范围较广,比较笼统;西医的病名对某一疾病的认识单一性好,也更为直观。中西医病名对照,应当是一种进步,是中西医沟通的第一步,为进一步的沟通和结合打下基础。但是医学领域有太多的未知数,许多疾病的病名目前还无法对应、无法对照,勉强对照,是不恰当的,不利于医学的发展。如乙脑和暑温,乙脑属于暑温,但不是说乙脑就是暑温,或暑温就是乙脑。应当采取同则同之,不能同的,又不能共的,采取约定俗成的称谓。因此在病名问题上,中西医有许多疾病名称不同,应当求同存异。目前不宜急于求成,强调一律,过早的搞中西医病名对照,事实上还不可能。不能要求大家接受目前还没有认识到的事物,也不能要求大家丢弃已经认识的事物。
1.2 关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 目前在儿科领域,甚至整个中医领域,均采取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形式。应当说,这一形式值得称道,也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很重要的实践。这一形式,既能展示西医辨病的长处,又能领略中医辨证的优势,应当说这是两长相加,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在新时期的切入点。
几千年来,中医学是在东方文化的理念指导下,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医是通过中医的病名来确立和认识疾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医的东进,加上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医病名的更加直观、更加客观、更具有单一性的揭示疾病规律的认识,为中医所接受,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医的进入为中医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撞击,也带来巨大的机遇。
如何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起来,使之更好地发挥长处,为临床医疗服务,是摆在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面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在当前历史时期,中医学从固有的中医疾病认识,转移至对西医病名疾病的中医辨证论治认识。这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跳跃。在这个跳跃中,应当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探索,充分地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把中医辨证论治发挥极至,而不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
必须指出,当前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结合”,在中医辨证方面过于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一个病名之下,列二三个、三四个、或五六个中医“证型”,就作为大学的教科书,作为临床的规范,作为国家行业的标准,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过于程式、过于固定。须知中医辨证是动态的、灵活的、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虽然每一疾病有一定规律,但决不是那么简单和固定。中医是辨证论治,从来也没有过“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辨证分型”和“分型论治”不能真正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成功经验,即是辨病与辨证的一个范例。1955年石家庄发生乙型脑炎流行,运用“清热解毒养阴”治则,采用白虎汤、清温败毒饮为主取得满意疗效。1956年北京地区又复流行乙型脑炎,用白虎汤疗效不佳,后用清暑化湿诸法(即白虎汤加苍术等)而显效。蒲辅周先生为此总结出乙脑治疗八法,这是因为当年北京暑盛挟湿,时值丙申太阴湿土在泉,气候湿热。1958年广州地区又发生乙型脑炎流行,使用上述地区经验疗效均不佳,是因当年燥热伤阴,按运气为戊戌“化火运”,气候燥热,故又在白虎汤基础上加生脉饮(即人参白虎汤加味之意),取得较佳疗效。疗效均达90%以上,并使当时的医疗界震惊。《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指出[1],“50年代中医药治疗乙型脑炎有两大意义,一是以其卓效在尚无抗病毒药物的条件下,说明辨证论治的价值;二是由于五运六气理论在治疗本病时取得一定疗效,引起人们重新对五运六气的重视和“估价”。这也充分说明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丰富性,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动态论的辨证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几个“分型”就能代替的。用西医学明确疾病诊断,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特长,摒弃简单化、程式化的“分型”,真正做到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真正发挥中医的疗效。
1.3 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 中西医双重诊断、双重治疗,这是近30年来中医医疗上的一大特点,在儿科领域更是明显。临床上双重诊断,有西医病名诊断,又有中医病名及辨证诊断,这应该是件好事,正如上述所论有助于中西医的沟通,有助于中医对西医病名疾病的认识。但是,也同样存在上述内容中谈到的难免出现中西医的勉强对照,中医辨证简单化。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因此,双重诊断存在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何改进、如何提高,正是当今面临应当认真探索加以解决的问题。
双重治疗,在大多情况下弊大于利。顾名思义所谓“双重治疗”,即是既用西药又用中药,这是西药、中药相加,是凑合,是“拼盘”,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在目前的现状下,所谓中西医结合治疗做得比较好的是,中西医在治疗某一疾病相互取长补短,针对某一病理状态、某一疾病阶段,发挥中西药的特效作用而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以发挥最佳疗效,减少副反应,缩短病程。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是肾病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激素治疗肾病综合征被认为是特效药物,然而激素的副反应大,肾病综合征的“反跳”与复发率高。然而在激素应用的不同阶段,根据辨证配合中药治疗能减轻激素的副反应,减少“反跳”,预防“复发”,同时还能增强体质,巩固疗效。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药合用,取长补短,有较好的临床治疗优点。
然而中西医双重治疗,中西药合用,很明显妨碍中医的发展,阻碍中医医疗技术的提高。因为西医治疗、西药的应用,靶向性较强,针对性较强,而且化学药物的定性定量准确,疗效确切。上述肾病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是激素的疗效确切,但副反应大,易复发,应用中医中药以巩固激素的疗效,并减轻激素的副反应,预防复发。在这个成功的“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双重治疗的例子中,中医中药也只是辅助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临床治疗现实却往往是中西药的合用是凑合,中药只是陪衬,或是点缀。中医治疗也往往不会认真思考、深入探索。尤其是儿科临床,西药针剂的注射往往比口服中药简单快捷,患儿家长都容易接受。既然西药起效了,何必再用中药,何必再去辨证论治,有了西医西药的拐杖,中医中药就必然“骨质疏松”,必然“缺钙”,中医的内涵就荒芜了,中医的特色就发挥不了,中医必然走向衰退。
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极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医疗经验。即使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临床上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情况下,也不应把中医辨证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发挥中医的独特疗效,或与西医西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向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迈进。
2 关于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在疗效。而中医的临证思维、辨证论治,则是发挥中医疗效的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2.1 破除“辨证分型”、“分型论治” 要提高中医技术水平,提高临证能力,就必须真正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学家孟庆云提出中医辨证论治三个阶段(即三个境界)的理论:第一阶段叫做“对号入座”,即初入门的中医,在临证时往往根据教科书的证侯分类、寒热虚实、阴虚阳虚来分证,叫对号入座;第二阶段由辨证的对号入座进入“机圆法治”,这是因为疾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疾病在变化,治法也要随之而变化,这是辨证论治的高一层次,也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提高了一个境界。对疾病的掌握,对疾病治疗的把握,能够“机圆法活”善于变化,疗效也会提高;第三阶段是“非法为法”(不以成法为法,不以现法为法)。更加运用自如,掌握疾病治疗的主动权,这是辨证论治的最高境界。应该说这才是中医的精华所在,这种境界才能把中医发挥极至。“上工治未病”,何谓“上工治未病”,一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以预防为主;二是治法先机,在疾病的每一过程中都能把握先机,治未病,治病之先。这就是不法为法。中医要立足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临证水平,必须在辨证论治上下功夫,力求更高第三境界。
在此必须指出,上述第一阶段,实际上就是目前风行的“辨证分型”。中医本来就没有“辨证分型”的说法,这个“辨证分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中西医结合的产物,它的思路是把中医的辨证按照西医疾病的分型来处理,结果就成了西医的辨病和中医的证型(即辨证分型)。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分型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没有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动态观、整体观,呈现的是西医认识疾病的定势思维,而不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辨证思维。中医从来没有“辨证分型”。因此,这个“型”是桎梏中医的枷锁,“辨证分型”与辨证论治不可同日而语。但自觉不自觉的还在讲“辨证分型”,这种分“型”成习惯了,中医就停止发展了,中医的水平也就到此为止了。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辨证分型”何止讲过一千次、一万次,现在真的似乎“辨证分型”成了中医的术语,多么可怕!若是把“辨证分型”成为国家标准,成为中医规范,那就真正置中医于死地了。因此,现在到了该彻底破除“辨证分型”,还辨证论治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2.2 深化中医辨证论治 中医辨证论治的研究应当深化,除了传统的望闻问切之外,还应当运用技术,将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结合起来。所谓宏观辨证是应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来辨别病位、病性及其变化,所谓微观辨证主要是指把西医的物理化学检查纳入中医辨证。
近30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医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现代生物化学、免疫学、影像学以及生物电等方面的发展,不仅为疾病的诊断与预后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中医学的辨证提供了新的资料。目前这些研究虽然是初步的,但不少已为临床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借鉴,比如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热毒证等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微观辨证的指标。应当指出,这些微观辨证指标还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创新,使之更具有特异性。毫无疑问,微观辨证的深入,将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深化和发展。
3 关于科研与
科研与教育,是促进事业发展和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科研与教育在规模上应当是史无前例的,但中医科研与教育仍是处在探索的过程中。
3.1 “研究中医”与“中医研究” 目前中医儿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概括起来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方面,主要是选用西医学的一些较为先进的指标来验证或探索中医儿科临床辨证论治;另一方面,是对某些方药制剂治疗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上述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有从中央到省市多层次的大量的立题或成果。这些研究统而言之可概括为“研究中医”,即是主要用现代医学来解释中医、研究中医,而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角度进行中医研究。即便是“研究中医”,但这里面仍然有值得深思的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目前虽然希望发现某些客观指标为辨证依据,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特异性强,是否真正先进,是否真正揭示中医辨证机制的实质,而且就中医辨证论治来讲,又是以“分型”为标准,这种“分型”能否真正反映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显然,这种“分型”过于简单化、肤浅化、程式化、固定化。如果说,研究的“起点”就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或其本身就不可靠、不可信,那得出的结论又能说明什么。再者,这种科研的思路仅仅在于应用西医学的指标(或者西医学的概念)来认识中医,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话是“中医的现代化”。如果说,这就是中医的现代化,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最多也是用现阶段的西医知识认识中医而已,而且认识的中医还不是真正的中医,“分型”不能代表中医。中医的精髓是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疾病、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而真正需要的科研,需要对中医学、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起推动作用的科学研究,不只是“研究中医”,更要做“中医研究”,是揭示中医学的本质,揭示中医对人体健康疾病的认识,必须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上去做科学研究。
至于另一方面对中药制剂的研制研究,大多是一病一方一药的研究,而且主要是西医药理药效方面的实验项目。这些也只是应用西医的药效学研究开发中药制剂的项目研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药学研究。
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深奥无比。因为中医学本身就是深奥的科学,人体科学、生命科学是十分深奥的科学,中医学是运用中医的基本理论指导来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借助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因为“研究中医”最多只是说明中医,解释中医,而要发展中医必须是“中医研究”。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入中医儿科学,使之转化为中医儿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研究中医儿科学术理论,提高中医儿科辨证论治水平,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的基本点,离开这个基本点将是舍本逐末。
3.2 “种树”与“养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基础。中医教育对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术的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医家朱良春指出,“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源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检测在于疗效,而疗效之关键在于人才”。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乏术、后继乏人。表面看中医队伍比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从业人员众多,但真正的中医、中医水平较高的中医仍然太少。这首先与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关。中医教育从广义讲应当包括入门(入行)教育和继续教育。中医的入门(或称入行)教育,主要是在中校进行的学历教育,中医教育应当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来进行、来管理,但目前中医院校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西医学的教育模式,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管理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医教育是培养后继之人,现在培养出来的人越多,却反而越造成后继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培养出来的中医不相信中医,不懂得中医的内涵,培养的不是真正的中医。因此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是后继乏术。
作者认为目前中医教育至少应加强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中医经典的学习,不能把中医经典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或者断章取义进行选编,或者任意套用时髦的名词进行解释,如果一位中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没有很好读过《伤寒论》,以后是很难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的;二是加强中医辨证思维的培养,忽略中医理论思维的培养,反而用西医的思维模式、教育模式来进行中医教育,是根本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来的;三是要注重中医临床技能的传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加强临床带教,特别要加强师带徒的教育传授模式,因为能够在临床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医药实践经验很难在课堂中学到。如果只强调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不会用中医中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先生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以师带徒、师徒传承的师承教育是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中国历史上,传承数代甚至数十代的中医世家也有不少。几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一大批医术精湛的名医,但现今的中医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执业资格与职称晋升制度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真正的中医越来越少。应当引起大家的反思。
“种树”与“养花”不同,这本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用种树的方法去养花,或用养花的方法去种树,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医教育亟待改革。中医儿科在整个中医界又是弱势群体,问题更为复杂,因此,中医儿科学人才的培养更应引起大家重视。
4 继承、发扬、创新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就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继承和发扬是中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没有好的继承,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更不能凭空而来”。我们要的是“推陈出新,而决不是弃陈出新,更不是灭陈出新”。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又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能急于求成。中医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临床、在于实践、在于疗效。现代临床由于环境的变化,更需要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以提高疗效。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曾强调指出,要切实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继承与创新是辨证的统一,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既不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也不能舍弃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和学术本质,要统筹兼顾整理、科研立项、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和中药研发,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二是必须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要通过临床实践筛选出有利于重大疾病的防治、独特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优秀临床人才的成长、具有良好疗效中药的研制等方面的课题,坚持医、产、学、研紧密结合,联合攻关,实现突破;三是必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要牢牢把握整体观、辨证论治等科学思维,认真挖掘整理、大力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独特诊疗技术方法,进一步做强做大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以及预防保健等方面的优势领域,注重从确有疗效的院内制剂中开发中药新药、注重对名优中成药的二次开发、注重挖掘和传承中药传统炮制技术。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仍然是继承和发扬的问题。继承,就是要发掘和整理中医儿科学固有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是使中医儿科学术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继承是发扬的基础,在继承中发扬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创新。更好地为亿万儿童的健康服务。
中医学的发展要强调继承,继承是发扬的基础,没有继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然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中医学如何在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健康发展,如何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嫁接,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摆在每一位中医药学工作者面前,义不容辞的任务。
现代生命科学前沿基因组学研究迅猛发展,对生命本质的揭示,已全面影响整个医学界,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为促进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的沟通,寻求新的研究和发展领域与途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于1999?03?14在北京召开了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提出以基因组学作为中医药学现代发展切入点的观点[3]。
这次会议在以下三大方面取得共识:(1)中医药学与基因组学研究相互渗透的可能性;(2)中医药学可与基因组学结合研究的领域:①中医证候学与相关(易感)基因研究;②中医药治疗作用与抗病基因研究;③中医药治疗作用与基因调控、修饰论;④中医药与蛋白质组学研究;⑤道地药材的基因组研究;⑥基因芯片技术与中医药学;⑦数学和信息分析技术与中医药学;(3)基因组学与中医药学交叉渗透的切入点:①证候发生与演变的基因组学研究;②中药复方作用机制的基因组学研究;③证候基因诊断与证候基因模型。
中医学与基因组学在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相互渗透是可能的。基因组学从整体上研究各个基因之间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与中医整体观相似;基因按功能分为结构基因与调控基因,基因组有“内含子”及“外显子”,“内含子”中又有“增强子”与“抑制子”,“抑癌基因”与“原癌基因”等都相当于一对对阴阳,基因之间也要保持动态平衡,与中医的阴阳学说一致。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有“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规律,基因组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搞清同组基因不同功能与不同基因功能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有助于中医科学深层次的内涵研究,对探索中医学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证候是内、外因相互作用导致的病机变化过程,依据多基因致病的关联特性,用基因组学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证候发生的基因表达调控规律、证候表现的基因特性、基因表达调控的变化及其规律,探讨疾病证候、亚健康状态(也有证候表现)与正常生命活动三种状态基因表达的差异性。证候发生的基因组学特征研究,为证候基因诊断、疗效评价指标体系、证候的动物模型复制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从基因表达谱或表达产物的差比性分析,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的基因调控、修饰过程,以期找出复方药物生物化学环境,对受体等靶点的基因表达及基因表达产物影响的生物环境与规律的作用。
“藏象”及“证”的生物基础研究、中药药理及复方作用研究,都需要样品中大量基因序列及表达信息,而基因芯片为中医微观整体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具,中医基于自身特点应抢先利用这一方法,以揭示中医辨证论治的实质和中药的有效成分,通过中医临床试验,并探析中医理论的复杂问题。
如果说过去引入现代科学指标的中西结合,为战术目标,是发展中医之“标”;那么把基因组学融入中医药学,对基础理论的突破性研究,可能才是战略目标,才是发展中医学术之“本”。基因组学有可能是中医学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中医药学以基因组学为突破口的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中医在引入基因组学后,将带来一次质的飞跃,中医药学将迎来一个以分子层次(主要是基因组学)为主导,全层次(包括整体和群体)发展的新时期。
【文献】
[1] 孟庆云.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M].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178.
[2] 吴仪.强调推进继承创新、坚定不移发展中医药事业[OL].新华网,2007?1?11.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教司.中医药与基因组学研讨会纪要[J].世界科学技术,1999,4(1):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