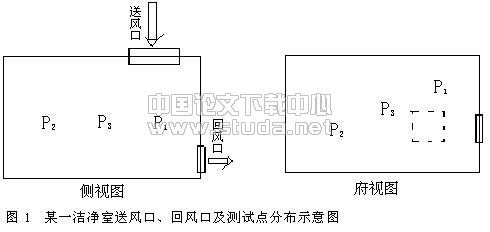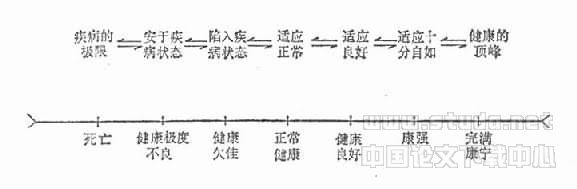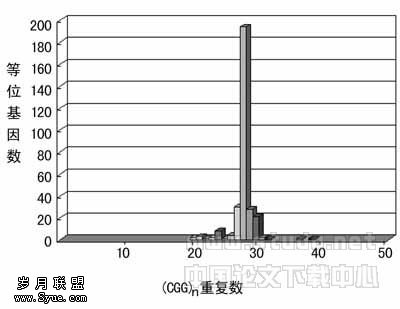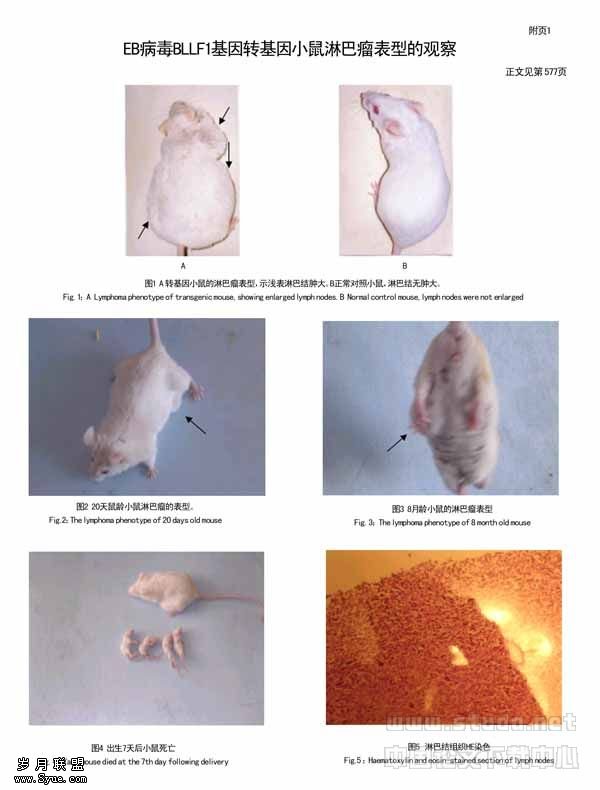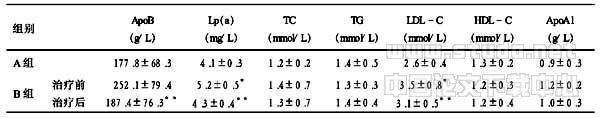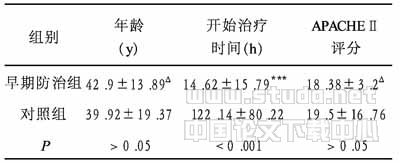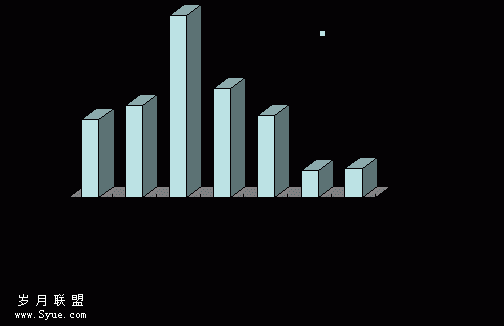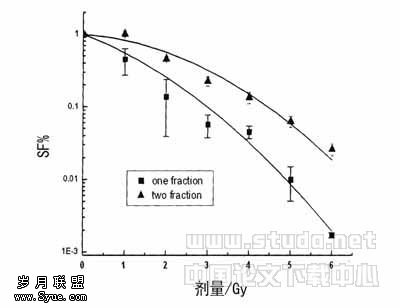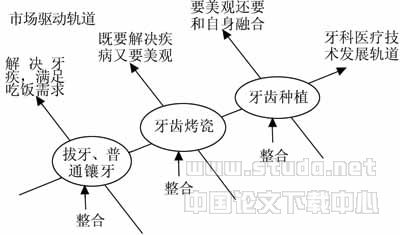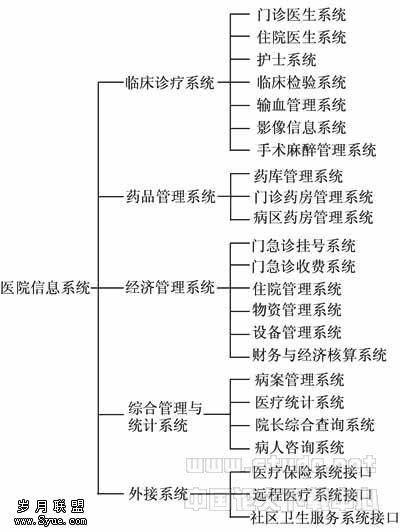从心痛的治疗观隋唐医学之特色
【摘要】 隋唐医学内容丰富且极富特色,就心痛及胸痹的而言,治疗方法较为完备,包括各种急救措施、常规的内服方药、导引行气、针刺灸疗以及外熨诸法,尤其是内服方药,其组方用药颇为新奇。隋唐医学对急救非常重视,博采众长的治疗方法及方药的运用都是其特色。
【关键词】 真心痛 胸痹 急救 针刺疗法
胸痹、心痛常并见于隋唐医籍中,但其内容大多重叠,故本文统称为心痛。对于心痛的病情及预后,隋唐医家有准确的认识,《病源》说:“心为诸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心有支别之络者,其为风冷所乘,不伤于正经者,亦令心痛,则乍间乍甚,故成疹不死。”[1]笔者现将隋唐现存部分医学资料中有关胸痹心痛治疗的内容作一整理研究。
1 急救措施完备
急救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急救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医疗水平的评价。隋唐医籍保存了较多有关急救的内容,有较为系统的急救方药及治疗手段,包括体位及手法、药物、针刺一系列针对性的治疗手段。
1.1 体位及手法 《古今录验》载治疗真心痛方法,“高其枕,柱其膝,欲令腹皮蹙软,爪其脐上三寸胃管有顷,其人患痛短气,欲令举手者,小举手,问痛差,缓者止。”[2]这是中医手法急救的较早记载。据其所述症状,当属心绞痛、心梗,以及并发的早期血流动力学紊乱范畴。“高其枕,柱其膝,”即是置病人于仰卧位,头和腿轻度抬高,“高其枕”则减轻心脏负荷,“柱其膝”则有助于保证重要腹腔脏器的供血,“爪其脐上三寸胃管”是说要按摩其心脏部位。这是最早的有关心痛体位及手法治疗的记载,实属难能可贵。
1.2 舌下给药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载硝石雄黄散[4]舌下给药,硝石、雄黄辛苦有毒,善于破积散结,祛瘀化浊,研极细末舌下含服与医学之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急救心绞痛、心梗不谋而合,却早其一千多年。《外台》广济方[3]以麝香、青木香之芳香走窜活血散结为主,当归和血定痛为辅,佐以槟榔之化积;《外台》深师方[3]则以麝香为君,牛黄、犀角入血解毒逐秽为臣;此三方或温一凉,皆以辛温或芳香等药效急骤迅猛者为主,可以在短时间内发挥通络定痛作用,对今日急救成药的研发颇有启迪。
1.3 吐法 吐法治疗心痛最早见于隋唐医籍记载,后世医家亦少有所及,吐法本《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之意,因此可以推测所治之证为邪处胸腔至高,清阳不宣,络脉痹阻之心痛。敦煌遗书《杂症方书第五种》[4]以瓜蒂、雄黄二味涌散闭阻上焦清阳之痰浊阴凝;芫花汤[2]用芫花、大黄、苦酒涌泻上焦之痰热积滞以宣阳气通络脉;一阴一阳,相映成趣。
1.4 针刺 针刺取效快捷,是急救的良法,隋唐医籍亦有所载,取穴依脏腑辨证,如肾心痛,取京骨、昆仑;胃心痛,取大都、太白;肝心痛,取行间、太冲;肺心痛,取鱼际、太渊[2]。
2 综合众法的治疗理念
隋唐医家认识到每种疗法都有其适应症与不足,不同病邪有不同的发病及传变,在选择治疗方法时强调根据综合众法选择最适合方法。
2.1 导引 最早的对于心痛的辨病施功防病祛病首见于《病源》,如“左胁侧卧,口纳气,伸臂直脚,以鼻出之,周而复始”[1]。类此者多,不一一列举。
2.2 食疗 隋唐医家还有不少食疗的经验,如饱食炙鳗鲡鱼,黍米沉汁温服[3]等饮食疗法。
2.3 外熨法 主于寒证,《千金》熨背散方:乌头、细辛、附子、羌活、蜀椒、桂心、川芎;上七味,治下筛,帛裹,微火炙令暖,以熨背上取瘥乃止[2]。《外台》蒸大豆熨法[3]等。
2.4 针灸 内容丰富,尤/其重视艾灸,如《千金》法:心痛暴恶风,灸巨阙百壮[2];《外台》法:疗胸痹胁满心痛方,灸期门随年壮[3]。隋唐医家重视艾灸是因为灸法较针刺更容易为劳苦大众所掌握,疾发时无须“外请名医,傍求上药…使人人和缓而家家有华佗”。
以上诸法,外熨法适应于寒邪初感牵及经络,针灸适应于邪在经络,药物则用来荡涤脏腑病邪,调整脏腑气血阴阳,食疗及导引主要用来预防及辅助治疗。孙思邈曾说过“且夫当今医者,未能综合众方,所以救疾多不全济,何哉?或有偏攻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唯行药饵,或有专于紧咒”[2],这句话批评了医者拘执于单一疗法的狭隘观念。
3 方药特色
3.1 和而不同的组方原则 从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和”的作用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之如何共处。这一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隋唐医家的诊疗理念中。隋唐医家认识到本病的发生往往是多因素多层次损伤所致,简单的不足以对应复杂的状况,虚与实、寒与热、多脏腑功能失调常常见于同一患者身上。如阳虚、邪热、营滞三种病机鼎足而立,三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难以辨识者,治以桂心散[3],温通心阳与清心经郁热同行不悖,以当归和血通络定痛,正阳复邪热除血脉通而心痛除;久而邪正混杂成积者,则以桃仁方[3]之人参、甘草、当归、赤芍补益气血,以桃仁、延胡索活血化瘀,槟榔、诃子化积行气,攻补兼施,用治久病气血俱伤而邪盘踞成积者;更有“久心痛…穷天下之方不瘥”者,《古今录验》之犀角丸[2]以麝香散结活血止痛,犀牛角、朱砂清心安神,附子、桂心温阳散寒,莽草、鬼臼破血散结通经,桔梗、芫花、巴豆祛痰逐饮,蜈蚣性灵走动以通经络,贝齿,味咸,能利水散结解毒,甘草、蜜调和诸药。所治之证不外阳虚寒凝,兼以痰饮热瘀停滞,此方融清、镇、温、芳香、飞虫、介类、逐饮破积攻下于一炉,繁复异常而并行不悖;多脏腑经络牵掣者,不离于心经亦不隅于心经,或赤芍桔梗杏仁方[3](赤芍、桔梗、杏仁)气血并调,宽胸理肺而行血脉,理肺以调血,或以千金治寒气卒客于五脏六腑中,则发痛方[2](柴胡、芍药、黄芩、升麻 桔梗、大黄、朴硝、鬼臼、鬼箭羽、桂心、朱砂)少阳阳明同调而通血脉。
要达到和的境界,第一,必须谨守病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不能自凭想象,脱离患者个体真实病机的治疗对患者医者都是危险的。第二,要遵守临床理法方药的基本原则而不能随意增减。
3.2 擅用峻、重剂 从现存可以看到,在治疗用药上,隋唐时代医家的一个特点是擅用重剂,大攻大补。在心痛治疗中,散寒温阳则如《千金要方》九痛丸[2]之附子、干姜、巴豆、吴茱萸、生狼毒并用,《外台秘要》之茱萸丸[3]中附子、吴茱萸、干姜、肉桂、蜀椒同投 ,邪甚则以毒药攻之,鬼臼、鬼箭羽、乌头、巴豆等虎狼之药亦为其时医家所习用;清热则黄连一味用至8两,不可谓不重;补则如《外台秘要》之茱萸煎[3]用干地1斤、麦冬5升、阿胶1斤、白蜜6两、石斛5两,补益阴血,以吴茱萸、蜀椒监之,大补阴血而逐寒凝,较复脉汤犹有过之。病重势急之病,平和之剂显然难以奏效,非大攻大补大毒不足以挽千钧于一发。
3.3 单方验方,自创新方 隋唐医家在熟练应用经方的基础上,接纳当时医药学新的成果并结合具体实践创制了很多新方,如前述之犀角丸、桃仁方、桂心散等,鬼臼、莽草、贝齿等药物的应用,从这些方药中不但可以直接领略组方用药之特色亦可一窥医家对疾病的总体认识。
当疾病的病机单一而不复杂时,简单的用药反而胜于诸药配合的复方,因此数量众多的单验方见于隋唐医籍之中。《千金》之大小槟榔丸化积行滞[2];桂心末温酒服以逐寒通络[3];当归末或桃仁枝酒服以化瘀[3];灶心土以温中[3];黄连煎[2]清心,类此者极多,不作详述。然亦有不经者,如驴粪绞汁[3]服,其效未知,却秽恶不堪。
4 结语
毫无疑问,上述一些具体内容对心痛具体的治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者疑问也更有意义。首先,完整性是医学作为学科的基本要求。隋唐医学治疗手段从预防、保健、急救到常规治疗是比较完备的,今日中医尚需努力以完善。其次,大胆的用药理念。病重须用狠药,不可为求平稳而弃用毒剂、峻剂、重剂。最后,要求医家具备勇于临床实践,勇于进取的求真创新之精神,硝石雄黄散舌下给药以及祛瘀法及虫药、毒药的使用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清代名医徐灵胎曾经评价唐代医学云∶“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处。”[5]
【文献】
[1]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498?503.
[2]孙思邈.千金方[M].北京:中医药出版社,1998:218?228.
[3]王 焘.外台秘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81?207.
[4]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124?486.
[5]徐大椿.徐大椿医书全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