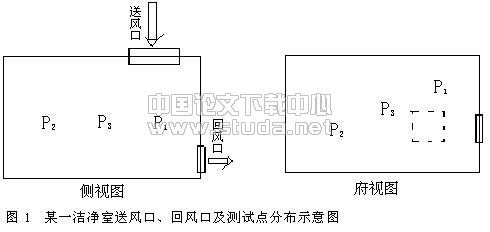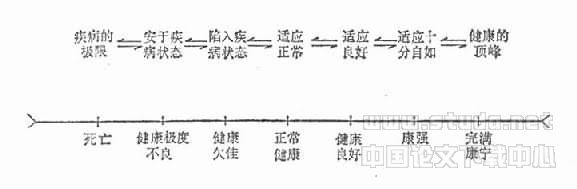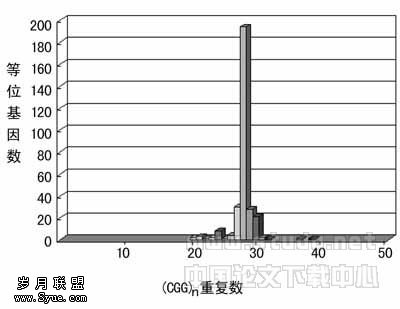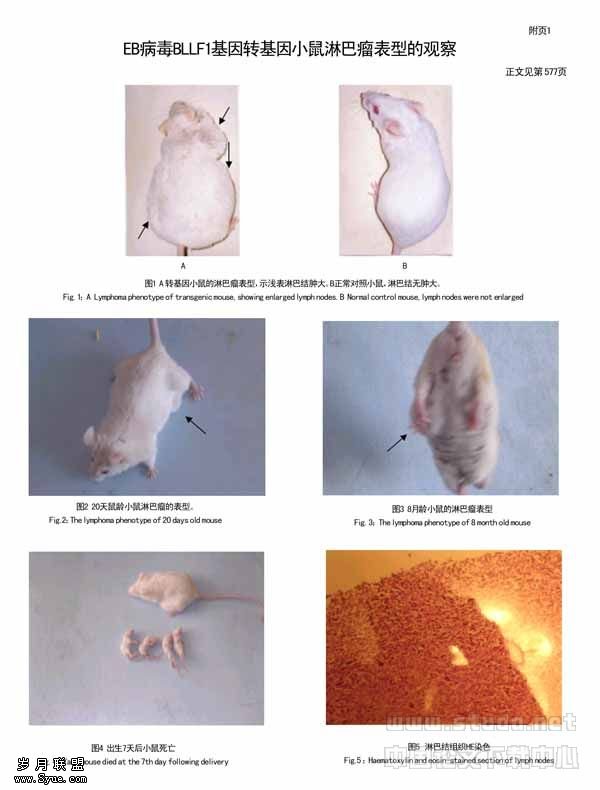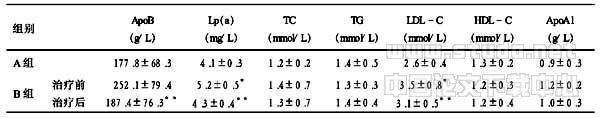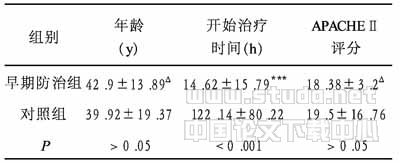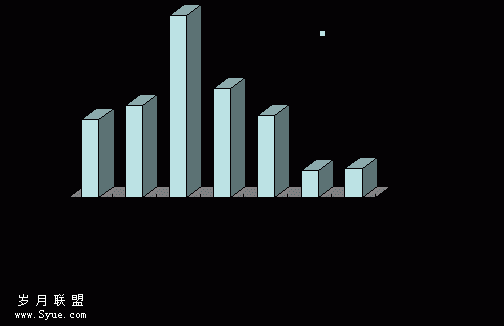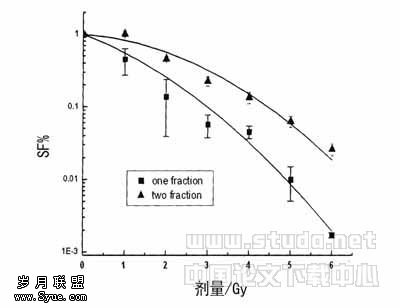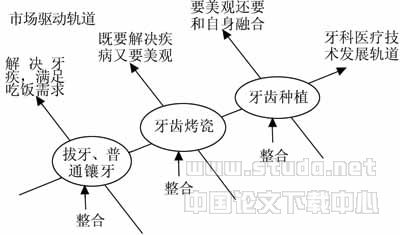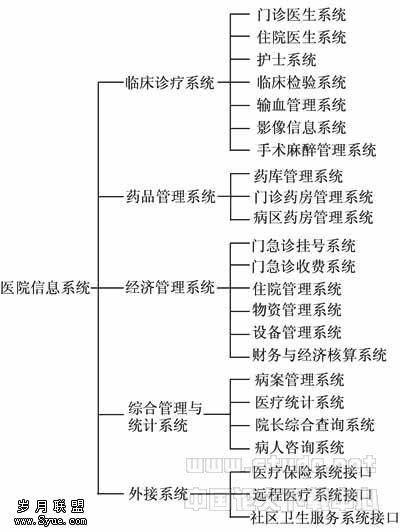从生物医学的观点看藏医药疗效的复杂性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12
在美国当代的研究范围内试图对藏医进行了解的想法,是在公众为寻找一种替代或“补充”医学的条件下开始的。在为了研究其临床疗效的众多“民族医学”中,较普遍的替代医学是中医以及以“四部医典”为基础的藏医学。那些由生物医学文化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其他替代医疗技术,它们应用生物医学的解剖学、生、效应(如螯合术、维生素、捏脊疗法),与此不同,民族医学由于其与生物医学极为不同的理论的作用,对生物医学工作者提出了特殊的挑战。研究者为了使研究和一般资料能简化进行以证实其疗效之有无,并克服这些困难,他们转向方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研究应用标准的生物医学研究准则,基本上集中在治疗的临床结果,而避开阐释为什么这些方法有效或无效的问题。这样一来,理论的问题(如解剖学、生理学、治疗机制)基本上都被忽略了。例如,对于针刺术,就只研究对特殊疾病的好处,并没有标准的对照组(对这患者是按中医认为有益的治疗),然后与那些用有效方法治疗的患者进行对比其结果)。在替代医学临床研究中,另一创新之处是那些从事治疗垂危病症的病人做替代医学的临床研究(这种方法是由艾滋病流行而引发的),对这些生物医学束手无策的垂危病人,迅速进行了替代医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非西方制剂,而不是用通过完事而昂贵的,并由联邦食品药品局(FDA)批准(有时需时数年)的试验来治疗;这是经临时批准的,目的是对生物医学认为无可救药,即生物医学认为没有把握的病人来进行的。
对于把民族医学的好处融入生物医学中,对结果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步。然而,这种对结果的研究从长远观点看也有一种简化论和排队性的问题,他对于亚洲医学体系及其医者们,包括藏医在内是不利的。这里的简化认是指一种步骤,他把医疗理论原则和实践加以忽略,或者简化成在生物医学临床中得以容易实践的简单的技术;而排队性则是指这种替代形式的知识,如埋藏在对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中的藏医学方法,被用盛行的西方或美国框架加以排除或替代了。
我将在六个人种学方面的例子中阐述这些步骤,以阐明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性。
1、翻译诊断法的复杂性
①在最早对临床疗效研究的复杂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生物医学框架中找到与藏医诊断一致的翻译疾病的方法。如我本人在研究藏医妇人疾病时,收集了一般妇人病的资料。在一般的问题中,一种叫“mngal nad mkhris rgyu”的是最普遍的,如果从文字上对译成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仅以病名而论,生物医学中并无与此相同的病症,在门诊中,每年要治疗3040个这类病人。另一种常见病是“子宫内肉赘”(sha skran phembo),我从资料中看到,也听说藏医对此病疗效很好,在对藏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疗效进行观察研究时,我要向生物医学的医生们请教,以便决定这些病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何种病。
②在确定临床疗效的努力中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藏医学与生物学中好几种病症,反之亦然。例如:“妇女子宫与胆有关的病症”可相当于生物医学一类疾病,包括盆腔炎、性病、严重霉菌感染、月经不调及子宫内膜炎。就藏医学而言,生物医学诊断为盆腔炎症的可以有不同的诊断,如mngal nad mkhris gyu或mngal nad rlung rgyu等。而在子宫内赘生物(sha skran phembo),是否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子宫内可认定的新生物则尚不清楚,有别于血液的新生物(trag skran),后者可以或不能相当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就生物医学而言,西藏医学对子宫肿瘤、癌症、囊肿和子宫内膜炎——这些可引致子宫和生殖管道中新生物是否能进行鉴别,也不得而知。
③另一个有关的复杂问题是,当对不同医学体系进行翻译时,在一个系统中称为症状者,在另一系统中可能称为疾病,反之亦然。因此,月经不调在生物医学中是一种疾病,而再加上一些其他症状在藏医学则有可能是一种症候。这与以下事实有关,即藏医学对一种“疾病”的确定,是基于对体内某些模式的失衡,意味着鉴别一种症候群或模式的紊乱,它可对全身产生有症状的影响。反之,生物医学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把疾病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它可以作为体内一种独立的病症加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听到说藏医治本,而生物医学则治标(症状)。
④最后,藏医依据经验把证据按疾病的严重程度把它分成原发病与继发病,这种把不平衡和疾病加以精细的模式造成了一种情况,即患有同名的原发病的患者,可能也患有一组不同的相关的继发病。换言之,藏医学对任何一种有名的疾病可以有较多的不同的内部(或近似的)病因。例如,原发的mngal nad可以与胆失衡、风或痰有关,造成同一疾病具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情况。或者说,患有mngal nad mkhris rgyu的妇女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继发病,如trag tshab或rlung tshab。。由于藏医考虑每个人的体液体质不同,每一个病人可能有同一基本疾病而各有不同的诊断,而这些不同可以影响其。
⑤鉴于这些复杂情况,探寻一下对当代关于结果的研究如何进行将是有益的。一般说,结果研究从生物医学的一种疾病,而不是从民族医学系统中的一种疾病开始。然后,利用生物医学诊断技术对疾病的生物医学诊断加以确定,最后用民族医学的方法来治疗,以决定其疗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从生物医学的疾病分类出发是否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由于生物医学对藏医学的精细变化无法驾驭,对病因方面和治疗方面差异的研究可能失去方向,而能够在疾病诊断中包容不同变异的藏医对结果的研究很可能产生可观的结果,这将加强对藏医学的认识。然而,这又需要比从一个简化的“结果”模型出发走得更远些。必须把藏医的医学理论也考虑进去,而不只是实践的问题。
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对结局的研究如何把藏医理论知识排除在外,以便进行临床试验的做法将潜在地把藏医能有效地工作的能力埋葬掉。在生物医学和藏医在疾病一对一相对应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将会被规避掉。但是,如果用于决定病因的诊断手段及其适当的治疗是由对结局研究所决定的话,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对藏医的声誉产生损害。因此,重要的是要提倡能容纳不同的诊断的灵活的对结局的研究模式,并努力了解和利用象藏医学这样的民族医学理论。
上一篇:试论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实现
下一篇:大型公立医院面临改革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