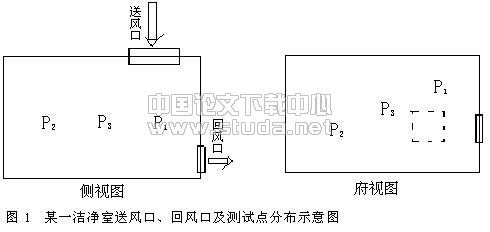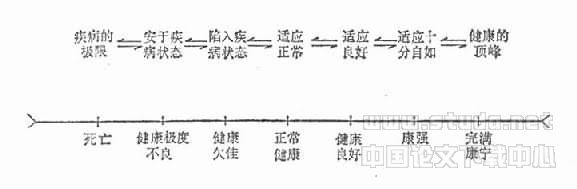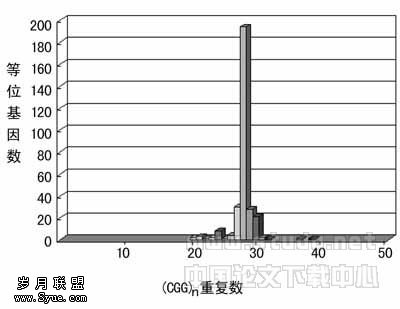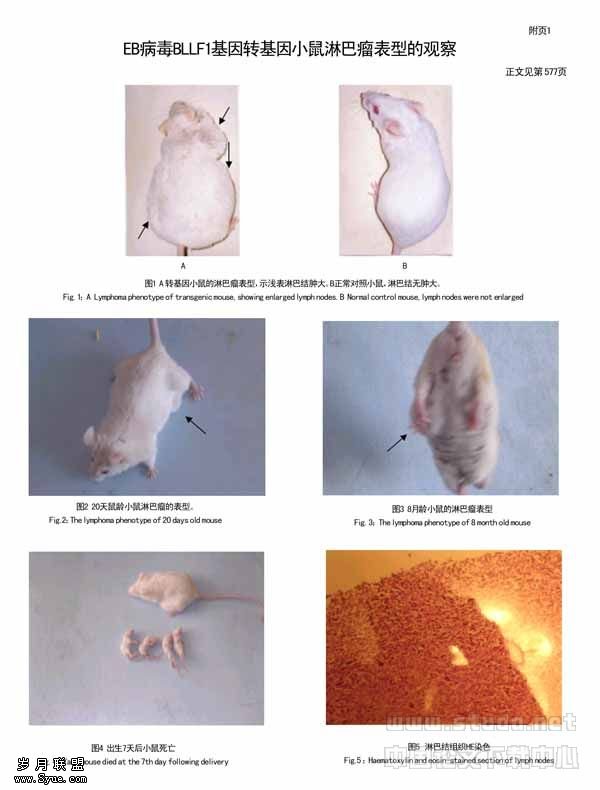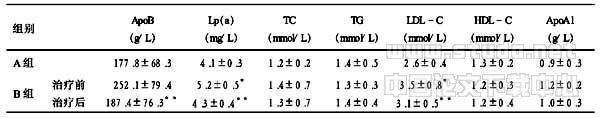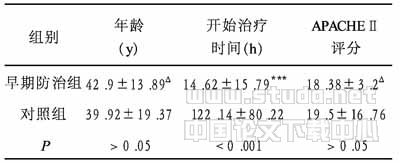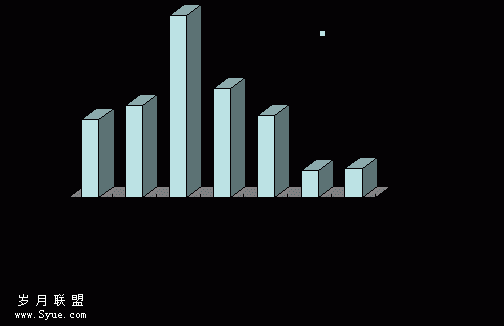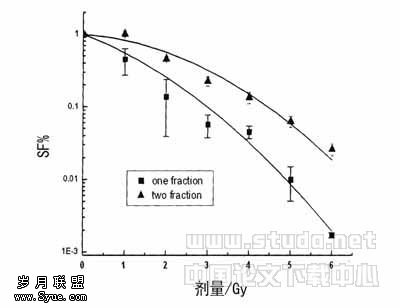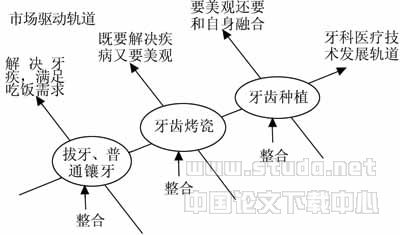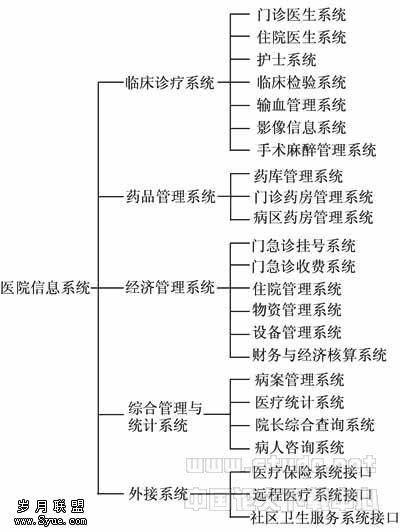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7-12
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的,而且最初的疾疫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因此,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此后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和疾疫史的开山之作(注: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84年)。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阅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以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国疾疫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3期)。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立足于明清疫病史,结合医疗史从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
一、医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国疾疫史研究,基本上一直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附庸,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 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疫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进入19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参阅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
陈邦贤等人对疾疫史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在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疾病史,特别对明清时期的疾病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在第三篇,专立一章梳理近世——主要是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的揭示。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注: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疯、疟疾、黑热病、住血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前揭著作,第361-385页。),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的重要传染病。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明清时期,尤其是传染病,其中不少疾疫,比如鼠疫、梅毒、烂喉瘀等,记载始于明清,故更偏重于明清。当然,在开创之初,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加以征用,另外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也仍具有价值。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疫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仍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和猩红热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 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 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年;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 《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年;《霍乱的流行史》,《健康医报》1946年第4期;郑伟如《霍乱史话》,《申报》1946年7月26 日),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3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新医药》1934年第2期;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国医导报》1941年第2期;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这些研究虽没有表明时段,但由于这些疾病有关记载基本限于明清以来,所以实际上,亦可看作对明清疾病史的探讨。另外,井村孝全对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瘟疫资料进行了钩沉与考略(《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新医药》1937年第4期;《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3年第12期)。
1949年以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一定的。1953年,范行准的《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一书出版,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功力,使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在1950年代,有几篇关于明清传染病的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 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 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己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己,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期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玺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作了探讨(《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新中医药》1954年第11期)。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作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 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作了探讨(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 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 姜春华等人探讨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 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 这些探讨也多有涉及明清时期的内容。
1960至1970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有少数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老大夫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特别在明清时期预防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高辉远整理《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进入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1980 年代在大陆和出版的两部疾病史的专著, 即: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陈胜昆之《中国疾病史》(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范著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注意较少。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在明清以来。全书共21章,其中有九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二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给人一种简单地叙述某种病的起源,然后十分突兀地跳跃到近代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什又有辗转抄袭之嫌(注: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50-71页)、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第204-206页)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除了疾疫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疫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对明清时期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作了重要探索,提出了明万历期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雷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有较多有关历史上包括明清时期疫病的记载。张志斌出版了《古代中医妇产科疾病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明清时期是妇产科疾病认识的理论发展时期,并从病名认识、病因病机认识、诊断学和学等几个方面对此做了探讨。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作简单的概述。
这一时期有关疾疫史的基本都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 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历代疫情发生情况作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尽管从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还显得粗疏。其他纯技术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明清瘟疫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5年第3期),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 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真正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清代“外来传入说”。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年第3 期)。此外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明清以来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效果是好的(《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第1 期)。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赖文等《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年第5 期)。
总体而言,有关明清时期的疾疫,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还非常有限。
二、历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明清疾疫史的发端,应属于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The Late Ming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 Shih Wen-ti, Vov. 3.3,1975),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读书札记性的短文《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以及陈高傭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本)。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19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开始出现;19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研究的渐趋热潮,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大陆地区的研究则始于1990年代,虽然目前还较少受到关注。
历史学者关注的大多并非疾疫本身,而是疾疫造成的社会影响,目前史学界对疾疫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其中除综合性(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整个明清时期或其中的某一时期中的疫病所作的总体性研究)的探讨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一定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作一梳理。
(一)综合性研究。1998年,张剑光出版了48万字的《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是目前唯一的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其中第7至第9部分分别对明代、清前期和清后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作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的疫病资料作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非常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著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明清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的一部分("Diseases of the Pre-modernPeriod in China", in K. F. Kipleed.: The Cambridge WorldHistory of Humam Dise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3),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等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中国疾疫史作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对18世纪以来出现的人口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前揭疾病社会史研究的论文中,对此持相当审慎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初步探讨了通行的和政府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瘟疫论》就中医关于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在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 期)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作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余新忠相继发表了《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2001年第2期)、《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论文。
(二)鼠疫、天花和霍乱。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以及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Carol Benedict关于19世纪鼠疫的新著(Bubonic Plague in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该著是在作者博士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Bubonic Plagu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China, Vol. 14.2; 1988; "Policing The Sick: 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4.2,1993),作者强调从、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著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著作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六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作了估计,指出,在云南19世纪50-60年代回乱期间,大约有五百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暴发期间,大约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必要性。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Carney 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作了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鼠疫》,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研院所,1995年),认为自1800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型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化计划一部分的主张,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凭藉这些措施,他们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曹树基、李玉尚近年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 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荡及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他们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活动出发,在疫病对人口损失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活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们还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关于天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和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文在范行准己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作了论述,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霍乱在(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尹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人的研究。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由江苏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己有之的地方病的几种观点,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作出断言,可能跟作者审慎态度有关。但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的。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虽与西疫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海上和内河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
(三)麻风病及其他。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稍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作了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余新忠通过对医籍所载和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比照分析,对烂喉痧传入中国的年代作出了新探索,认为雍正十一年苏南发生的大疫,有较大可能是伤寒流行,即使有烂喉痧,也绝不存在烂喉痧首度流行的事实。实际上,康熙晚期,烂喉痧已被当作过去较少见的疫病在苏南出现(《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Organized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al China,Vol.8.1,1987:《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l," History of Science., xxxi, 1993; Wilt Idems: "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 A Very Prc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Related Plays." Chinese Science, 1977,2),韩嵩(Mari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Inventing a Tradition in ChineseMedicine: From Universal Canon to Local medical Knowledge inSouth China,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博士学位论文,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7" (注:该信息由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博士提供,谨致谢忱。)Robust Northerners andDelicate Southerners: "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 Positions, Vol.6.3,1998)。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应是历史学者所长,就明清时期而言,由于历史资料的丰富,这一工作无疑是大有可为的,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某种那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显然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未能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暴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作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有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知识,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个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很少作出自己的探索。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
上一篇:新形势下医院人才培养的思考
下一篇: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