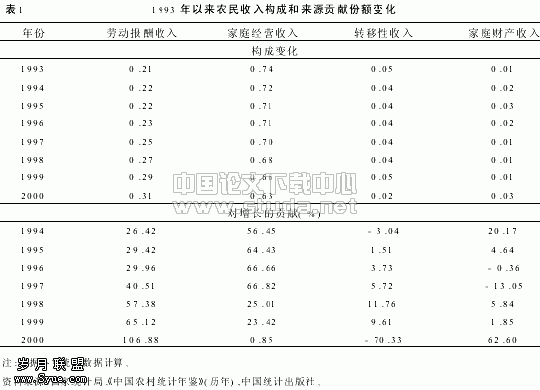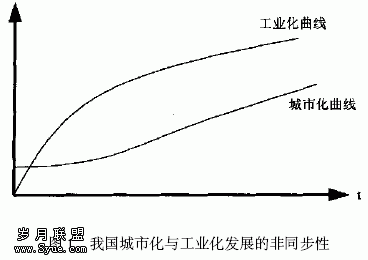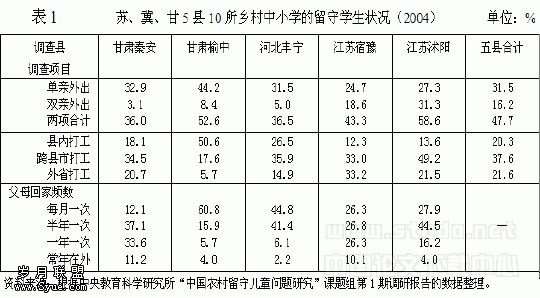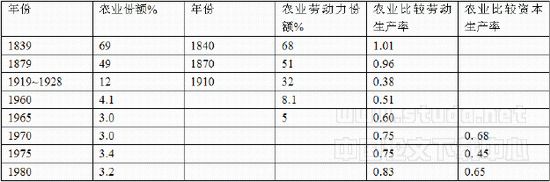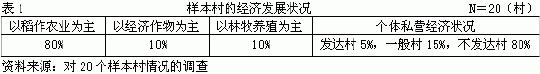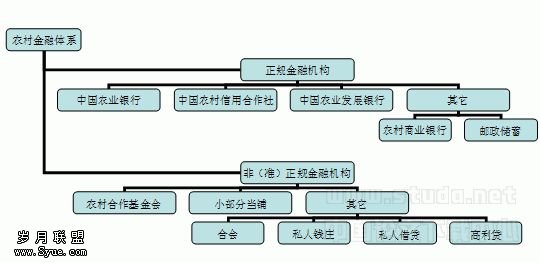论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论文内容提要]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性隐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文化大革命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 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 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11](美)艾尔东,莫里斯等主编.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译.世界文化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下一篇:我国农村发展社区教育途径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