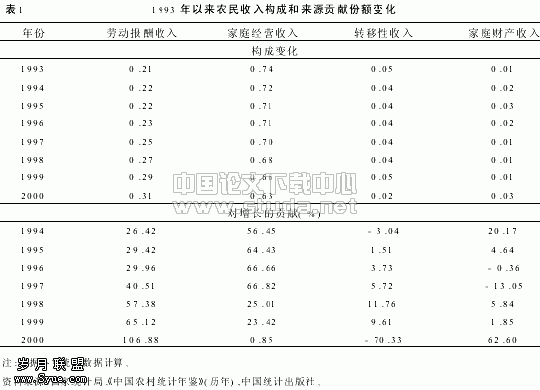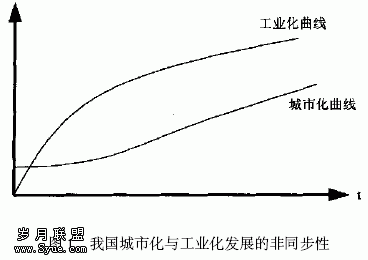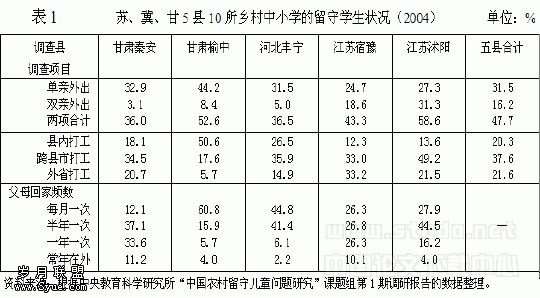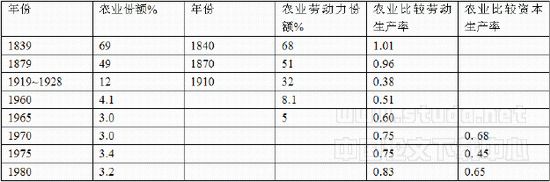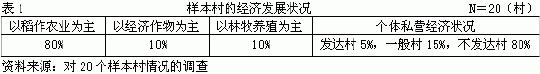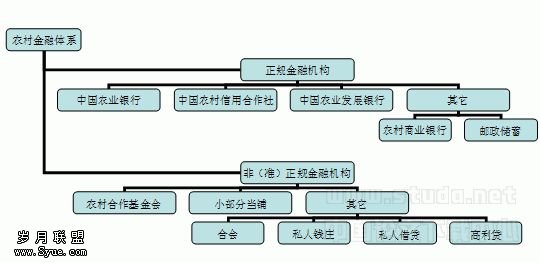新农村建设权力结构、赋权与组织化
新的“二十字”描述即“生产、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我们勾画了未来新农村的蓝图,对非领域的乡村治理、社会及环境发展用了三句话,使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的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是务实的。新农村建设事实上是要解决乡村的有价值的生活问题,也必然是在外来者协助下村民广泛、积极参与解决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中央号召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类型的支农活动。不管是政府推行还是民间行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都必然面对与乡村的关系、如何推进农民主体性、村庄组织化等方面的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在以往政府和民间作过大量的乡村发展工作,这些工作中出来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好的经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反思与回应的问题。
一,外来者与乡村的权力结构问题
外来者参与到农村社区综合发展或者是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势必因为国家权力、挟带资源或者是以专家、志愿者的身份对乡村发展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也势必因为这些原因而与乡村形成不均衡的权力结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来者对乡村是有各种权力的,而这些权力的运作与使用,对乡村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什么是权力?韦伯把“权力”定义为:“一个行动者能够任凭反抗而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论这一可能性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简单地说,权力使一个人得以控制他人,是一种支配力。韦伯还将之分为合法支配和非合法支配两种类型。笔者基于对乡村社会的调查,在合法性支配的条件下,对乡村权力结构中权力的理解为:权力可以是一个人/团体可以对他人/另外的团体作什么或者是不作什么的能力,也可以是对公共事务与公共资源的支配与控制力。反应于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活动中,乡村权力结构则表现于各种利益群体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支配与服从,控制与反抗,裹胁与迎合,分化与合作等的可能关系(笔者将另文专谈),是乡村内部搏弈的基础,同时也是制度的、传统的产物,并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以笔者的调查来看,外来者从事乡村工作,与乡村形成了一定形式的权力结构:作为政府主导型的乡村发展,因为国家暴力的原因,其权力结构的可能关系往往是控制与反抗,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处理不好,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民主体性会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反而会加剧乡村的原子化;而一些从事乡村发展的民间组织及志愿者与乡村形成的权力关系,因为资源与智识的原因,则多可能表现为裹胁与迎合、分化与合作的关系,虽然多数民间行动都将人的权利平等作为行动的基本价值观,但价值观第一的行动在现实的活动中,因为其活动与裹胁的不可持续性,有时也容易造成村庄的分化,从而造成新的乡村社会问题。外来者与乡村的权力结构关系,对乡村发展和农民主体性的确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没有一条真正合适有效的道路。笔者看来,可能的好的途径在于相关资源处分与分配权力的重新确定,以使权力结构中的各种可能关系渐趋平衡,建立政府与村庄,外来者与村庄的真正的合作与支持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新农村建设的成功。
二,农民主体性的建立不等于放权/授权乡村组织
国家推进的以农民为主体进行新农村建设和民间行动的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本的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都离不开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与发展能力即赋权农民的工作。现时条件下,赋权农民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是通过村民自治、农民组织化(村庄组织化)的途径,并且看起来,也是唯一的途径。新农村建设的五个目标,也正是在村民自治/村庄组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的。如何推进好的村庄组织的行动研究与机制探索,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成败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中国乡村组织化工作,政府权力的控制与影响还很大,这是政府退不出乡村的原因,也是政府权力退不出乡村的结果。一些地方也对这种关系作了些改善,村民自治的推行往往成为扶植村庄的强人与能人体系,之后简单化地把属于村庄的事务处理全部交给村庄即交给这些扶植起来的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建立了合谋关系,实际控制了乡村的各种有价值的发展资源。村民自治在中国的实践本身因为种种原因,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就算实行得较好的地方,也往往是彻底的多数决。中国的“村”除了自治功能外,本身还兼有独立社区、经济组织、文化个体、发展主体等多种角色(参见笔者“村的性质探讨及新农村建设”一文:三农中国网),原子化的乡村还要解决组织资源的问题,另一些乡村内的传统宗族力量的影响也会铁忽略到边缘社群的利益,更为令人担心的是,乡村的灰、黑、恶势力也正有逐步强大的趋势。如果赋权仅仅是放权,这样的组织化工作是令人担忧的。
民间组织在乡村的工作,由于无法理清“村”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更难于将实际作为政府职能延伸并对乡村有控制力的“村委会”视为村庄的组织,乡村发展多选择走“村庄”(村)而不是“村”(行政村)的道路。通过建立“社区组织”的形式来推动村庄组织化和乡村发展工作。笔者了解的大多数此类项目的着眼点在于培植村庄的“有公心”的能人并支持他们的能力增长,将社会运作及发展事务的管理交给他们,以领导村庄的发展及其他工作。这同样面临的问题是,村庄组织的合法性将导致其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其对于社区公共资源整合的能力也是不足的。并且,村庄组织的选举是在大量社区工作之后进行的,事实上也是经过外来者控制的的选举。如果要因此得出一些模式出来,在乡、村关系还没厘清、基层政府职能转变还未实现的今天,这种经验的推广与复制会很困难。同时,村庄组织化及组织运作往往建立在道德诉求的基础之上,这对于多数价值伦理体系解体的原子化的村庄而言,实现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乡村民间发展行动很多都简单的处理为通过资源分配“授权”村庄组织的方式,结果同样有可能导致村庄内部的公平问题,从而反制了村庄组织的进路并使一些最势弱人群的发展受到限制。
三,村庄组织化与农民组织化的问题
新建设都在讲农民组织化,各领域专家都认可并支持农民组织化的作法,并且认为,农民主体性体现于组织起来的农民。几年前政府就开始大力推动农村合作组织的产生,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农民维权组织,农民以集体行动主张权利并推动着自身的发展,让一些人看到了农民行动的力量。
但笔者认为,在现实中国里,要推动以农民身份为前提的农民组织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有危险的倾向。虽然笔者也反对“农民不懂民主”的说法,但现实情况下,抛开区域的界限,发展以身份为前提的农民组织,如果是经济合作组织,则要考虑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对比。笔者在贫困地区了解的情况是,跨村的农民经合组织,农民的参与动机是不足的,参与成本的高昂与收益的低下,使得农民的实质参与远远不够,大大影响了自治的合作组织的治理与决策机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不足,使得经合组织成了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导致的问题对合作组织而言是致命的。这样的组织要么名存实亡,要么靠一些强人和能人控制,反而会挤占其他人的生存与展空间,或者是加重农民的负担。至于农民维权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悲情意识,也容易演化为对内对外的双重暴力,对农民而言,对社会和国家而言,都是危险的。当然,农民维权组织的产生,其根源并不在于农民,而是各地政府行政的问题,所以要解决维权组织问题的前提,是要解决政府行政的问题。
笔者赞同的农民组织化形式实质是村庄组织化,是在以村庄共同体建立为目标、整合村庄资源为村庄发展服务的基础上,推动村庄内农民的协作与合作,共同解决生产、生活的成本问题。只有协作与合作的问题解决了,乡村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得到重建,从而重建伦理基础与软约束机制,使得和谐乡村成为可能。事实上,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通过大幅度货币增收来解决农民的幸福问题,从理论及实际情况来看都无可能。村庄组织化固然可能通过合作与协作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另一层面的增收,但更大的增收却是在于农民通过组织协作的方式,通过投工投劳,实现劳动力物化,可以解决村庄公共设施的不足从而大大增加农民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的享有量,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增收。同时,组织化的村庄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村庄认同,这样的认同正是乡村生活价值最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乡村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这正是笔者理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所以,以村庄组织化为途径、也是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要建设“我们的生活”。回到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正是针对生活价值、共同体价值与伦理基础的。
但是,村庄组织的发展在目前还面临其它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乡、村关系及村两委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通过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来回应的,乡、村之间、村两委之间的权力结构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问题,也会成为新农村建设迈不过去的一道门坎,这一点,是民间行动无法解决的,也正是考验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智慧与勇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