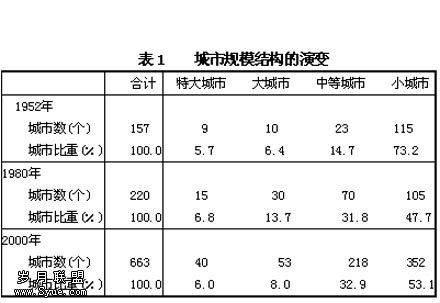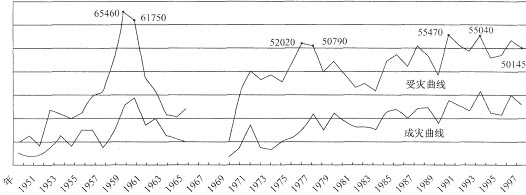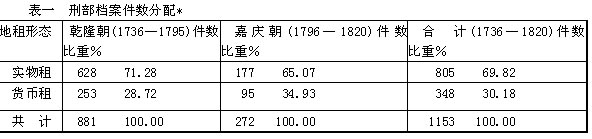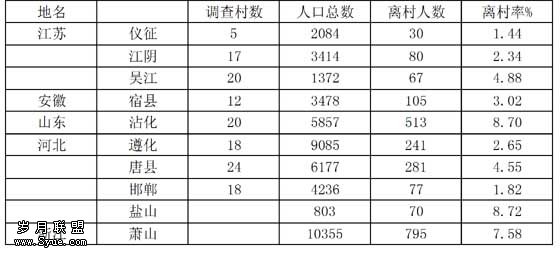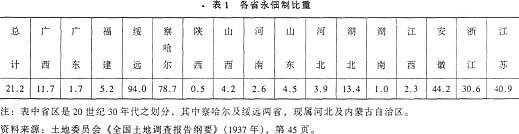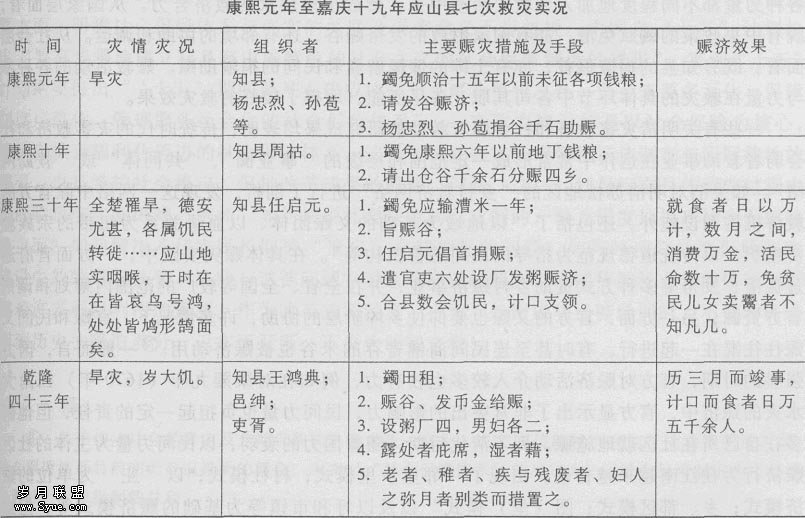试析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论文摘要: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一、宗族家庭的源流与嬗变
(一)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
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结束了被动的采集农业,开始原始的种植农业。这种农耕的方式使得人们定居形成村落,而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随着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的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对偶婚”不断增多并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标志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从此,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为了实现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有效管理,一套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的宗族制度,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在地缘上便成为了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
(二)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
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明。在父系氏族末期,随着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的联合,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时期的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它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由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周天子利用公社形式,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邑里村社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力象征、大宗小宗分别继承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强迫性。
(三)制度的瓦解与意识的延续
从春秋初年开始,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瓦解过程。如宋代陈祥道说,周代宗族制度盛行,到商鞅变法,人们早已不知道敬宗收族了J。直到战国中叶以后,经过各国的变法运动才彻底瓦解。在宗法制度之下,周王室是天下同姓诸侯的大宗,周王是大宗的大宗子,诸侯对周王惟命是听,不敢有缺,但随着分封制的混乱和瓦解,周王已无力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失去了大宗的大宗子地位,宗法制度消失殆尽。而在周天子之下,大宗、小宗关系混乱颠倒,许多强大的异姓大夫起来控制国君,最后夺取国君的位子。在孔子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家庭之间的地缘关系在一定关系上还客观存在,因此敬宗收族、宗族团聚、族众互助的宗法意识不但没有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扫地以尽,而且“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抑,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二、宗族家庭与乡里制度的亲和
(一)宗族家庭的作用与功能
与古希腊的海商文明不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种植文明,种植业的特点使得人口束缚于土地,罕有流动性,进而在中国形成了聚族而居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主的血缘。因此,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保持农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一方面,从宗族的功能需要来说,大体可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来概括。“守望相助”为的是应对社会风险古代的农村地区生态不稳定,耕作方式粗放,往往需要靠天、靠地吃饭,再加上纷争不断、战乱频仍,村庄安全成为很大的问题。因此,村民聚居就容易形成规模巨大的村庄,以此来增强防御人祸的力量。从“疾病相扶”来讲,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户十分脆弱,非常需要得到超出家庭力量的扶持,而人们的祖先崇拜情结使得族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并且这种朴素的利他主义逐渐地成为宗族族约中普遍的规定。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外,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集中个体的力量,进行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这些都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
另一方面,从规范来讲,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组织制定有大量的族规家法。这些族规家法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以协调邻里关系、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由族人自行制定或自愿接受,共同遵守,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这些族规家法不仅仅是民间的,而且获得了国家的默认甚至支持。它们不仅是劝导性的,而且往往是惩罚性的,比如对于违反族规的人,可以责打、罚物,甚至逐黜族籍,即使将不法族人处死,国家也不会轻易干涉。还有的族规规定族内发生纠纷必须通过宗族内部解决,不许向官府提起诉讼。可见,族规家法是以义务为基础的规范,在国家一般不介入基层社会尤其是宗族内部事务时,可以有效约束族人内部的争斗及少数人的越轨,约束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的偷懒行为,从而使宗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秩序。
(二)国家治理面临两难抉择
村庄最早是家族的自然聚集,是原始公社转化而来的宗族组织,并随着宗族组织向国家转变而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在农业时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源来自于土地,因此迫切需要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和控制。然而,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却使国家面临治理的“两难抉择”。
国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治理成本的问题。我国地缘辽阔,当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国家与乡村的社会距离自然拉大。同时,农耕生活天然的独立性,使得乡村成零散的点状分布,使中国的乡村彼此分离,相距遥远。 “虽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细胞化社会”或“化社会”。如果国家权力渗透到广袤的乡村,将乡村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必然要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用较大成本换取的却是极低的运转效率。再次,由于宗族是封闭的、排外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组织,国家治理乡村必然要遭到家族势力的抵触和挑战。宗族势力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当国家权力下沉时,必然和家族势力产生治理冲突。国家有限的控制力和以宗族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力量的不断抵制,使中国历代政权都难以把乡里社会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中来。
(三)成本思想催生乡里制度
为了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统治阶级只能采取官民共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方面,国家政权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依托乡村内生的民间权威,把宗族的首领培植成皇权的代理人,通过他们实现对乡村的控制,进而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这种治理模式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宗族权威的交汇地带,“王权”和“族权”在乡村既斗争又合流。当两股力量比较协调时,乡村稳定,国家可以从乡村获得大量的资源;当两股力量发生冲突时,就可能出现乡民造反,进而导致王朝更迭。
三、乡里制度的特点与功能
(一)宗族势力强大
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时没有清算氏族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了起来。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使中国人的家族概念很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家族兴旺曾一度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儒家思想中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乡村,大的家族人多势众,具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小的家族单门独户,常常没有什么地位。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存在,调解了族人争端,维护了社会治安。当外族入侵时,家族势力还能够保护乡土。为了促进乡村的发展,家族势力还注重对家族成员进行,组织乡民建设公共福利事业。面对强大的宗族势力,皇权统治没有动摇它的根基,而是将其作为专制统治的基础。当然,随着王朝变迁、人El流动、异姓杂居等因素的影响,家族势力盛衰与社会的变迁交相关联。乡里组织作为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最底层,它与家族宗法有某些分离,其性质也有不同。但是,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关系最近也最为密切,也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乡里制度不仅不能完全割断与宗族家庭的脐带关联,而且其中还有着较强的宗族家庭意识。宗族家庭虽然不属于官僚组织系统,但它有着与官僚机构相近的一套制度,加上它分布广阔、凝聚力大,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可以说,宗族家庭式乡里社会是最大最稳固、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团体与组织单位。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乡里社会进行的任何运动都与宗族家庭势力有深刻的关联。乡里制度是中国官僚制度在乡里社会的延伸,它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也是中国官僚政治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的影响史。 (二)政权间接渗透
自秦朝建立郡县以来,历代王朝县以上各级行政区划通过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层层控制,获得了较强的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皇权不下县”,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生活,政府管理乡村的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管理户籍,督导生产,教化民众。但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是以县令为终端的,在县以下的乡里通过“有官衔无俸禄”或“无官衔无俸禄”等方式,让宗族领袖充任代理人,国家权力以间接的形式进入乡村,由乡里制度对乡村进行了有效管理,即使在县衙,官员数量也很少。朝廷官员上收不等于削弱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相反,政府通过培植民间力量,沟通了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将村落社区整合进国家系统,完全控制了对乡村资源的调配,实现了“小政府大管理”的目标。乡里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工具,无论它的执行愿望和执行形式如何,都要保证它的强迫性,而这种强迫性来自国家的授权。在“王权”和“族权”的共同统治下,乡村社会形成了服从管理、认同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虽然上王朝兴衰不断,但民间对公共权力的尊重和认同的价值取向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J。
(三)乡绅有限自治
政府在乡村选择的管理者主要是有德行的长者、有名望的乡绅、有财产的地主及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人往往都读过书,拥有较多的知识和财富上的资源。他们不但在宗族内部拥有家长式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在文盲为基础的古代乡村社会,乡绅的有限知识能够获得平民的敬仰和尊重,从而提升他们的号召力,因此,乡绅能够比较从容地创制和解释乡规民约,用低成本的道德感召力维持乡村的秩序。乡绅的利益离不开乡土,因此他们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他们要帮助国家做事;作为乡村的代表,他们又需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乡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当分散,村庄之间相互隔绝,面对散漫的、平铺的“蜂窝状结构”的社会,皇权并不想无所不至地对其进行绝对控制。只要乡绅能够服从国家管理,他们在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之后,可以获得有限的自治权。当然,国家也始终注意宗族势力的消涨,防止宗族势力越过国家能够容忍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乡绅自治”不是“乡民自治”,在家族色彩和血缘意识的作用下,乡村自治逃不脱宗族势力、传统伦理的范畴,乡村的社会控制权和资源配置权实际上掌控在宗族豪强手中,他们制约着乡村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向。
四、结语
一部乡里制度的和嬗变历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影响渗透的历史。通过乡里制度与宗族关系,尤其通过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何以宗族家庭会对中国的乡里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认识这些,既是我们理解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关系的前提,同时对我们思考如何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乡里制度建设,实行有效的乡村治理大有裨益。
概括来说,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乡里制度与宗法精神的同构性和一致性使得乡里制度不得不依赖宗族制度。宗族制度的职责原本是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实施对宗族家庭的治理,但由于传统中国的蜂窝状结构和熟人社会的性质,宗族制度的功能扩展到维护宗族以外的乡村社会。正因为宗法思想不仅符合官方尊祖忠孝教义,而且宗族可以约束其成员,使其言行更符合封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所以宗族才成为村庄公务活动的合法组织者J。其次,从现实层面而言,宗族家庭势力强大,它是乡里社会的政治、、司法、思想和文化的中心与堡垒,不管乡里社会的人户有多少,他们通常归于有数的几个大家族,封建国家无法回避或绕开宗族组织而将权力深入到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基层控制工具,至于官僚机构则因人手不够,通常不想去干涉宗族的事务,统治者看到了宗族制度与乡里制度功能的一致性而利用宗族的力量,承认族长有权在族内执掌刑罚,默许其作为最低一级司法机构的地位。最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使得宗族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愿意自发地维持乡村安宁,才使得历代乡里制本身虽不健全,但仍能在乡里社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宗族和乡里制度能够得以亲和与延续的深厚文化背景。
通过对宗族家庭与乡村制度关系的考察,结合当下乡村熟人社会并未完全消解,宗族观念影响依然存在的现实,在对现代社会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的过程中,正如赵秀玲所认为的那样,既要避免完全抛弃宗族家庭在乡里社会的影响力,因为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有数千年宗族家庭发展和统治的历史;又要淡化宗族家庭对乡里社会的控制,强化乡里制度的建设功能,因为传统乡里社会有的地方出现国家权力真空,这些地方完全被宗族家庭操纵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