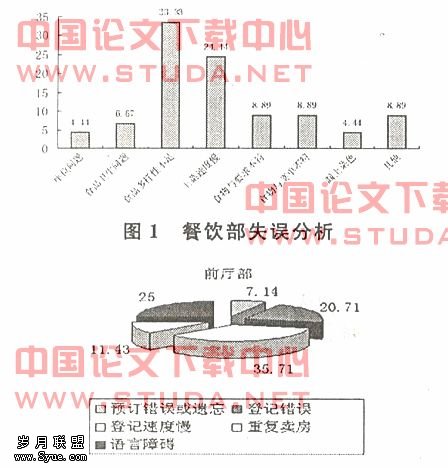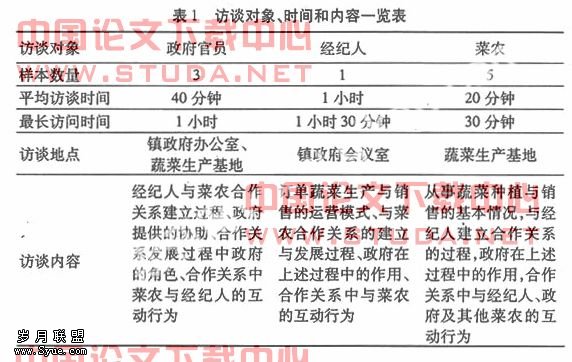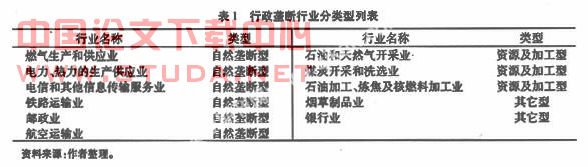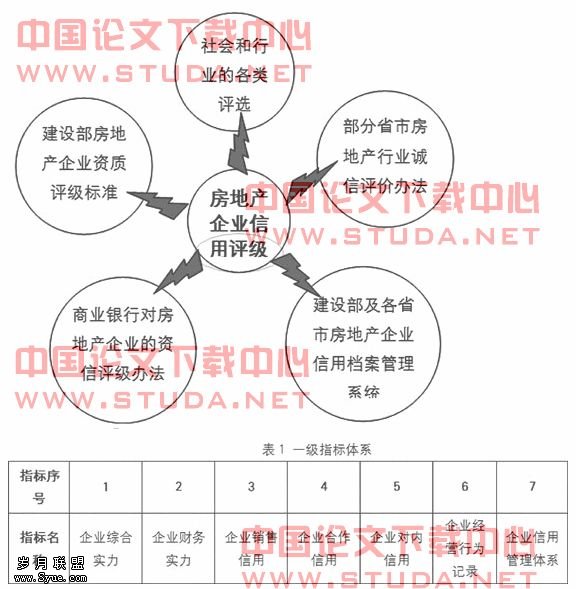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近代农业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近代农业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注:Ramon Myers,"North China Villag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Socioeconomic Relationships,"in Modern China,1980,vol.6.no.3,pp.243-266.)
由于马若孟、黄宗智和其他参加1970年代辩论的学者们都各自利用了不同甚至相同的资料引出了各种数据,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激起了周锡瑞(Joseph Eshrick)在1981年写了一篇题为“数字游戏”的文章,对各方所使用以及他能搜集到的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作了各种对比,对参加辩论的学者作了批评。周指出:取决于每个学者的立场和每人研究的区域,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在做出修正值后几乎可以游戏般地让每个学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些数据资料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于中国近代土地分配的真实状况,虽然周本人倾向于认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有很多地主,这些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不能简单被视为是一个小自耕农充斥的国家。(注:Joseph Eshrick,"Number Games".)
三、中国农业改革的影响和1980年代以来的辩论
19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辩论,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根本性问题的新的理解。首先,1970年代的辩论显示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根本性问题、土地分配、租佃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消解分歧不仅需要对这些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并且还需要另辟蹊径,开拓视野。同时,通过1970年代的辩论和对话,学者们也需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修正或检验自己的理论。比如马若孟就承认自己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没有给予土地分配问题以应有的考虑,并指出土地产权制需要改革。(注: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2页。)
第二,1979年以来的中国农业改革使一些学者对近代土地产权分配和租佃制度的重要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30年内一些重大的农业政策是错的,造就了许多悲剧,以致于1970年代末不得不采取农业经济的改革政策,把土地的使用权交还给农民。
第三,19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著作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革命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在这些背景下,黄宗智在1985年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他的两本经典性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两本书都大量地使用了满铁的资料。在《华北》一书中,黄的核心概念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由此而派生出“社会分化”,不再以土地分配和租佃关系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和革命。黄认为,明清以降,华北的农业生产有了增长,但却没有赶上人口的增长,因此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农业生产的总量增长了,但人口增长更快,对土地造成了压力,使得人均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递减。但在这没有发展的增长中,近代的农业经济由于商业化而起了变化,出现了经营地主。他们通过购买或租佃建立起了规模为100-200亩地的经营农场,通常雇佣3-8个劳动力,以远高于普通农户的效率进行生产。此外,他们的农场通常以市场为取向而进行专业化生产,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以远高于普通农户的效益进行生产。结果是,这一部分经营地主富裕了,但更多的农民变得没有地种,沦入贫困化。因此近代商业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经营农场在华北导致了社会分化。(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21-137,155-168,293-310.)
在《长江三角洲》一书中,黄宗智更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内卷化”、或有时被称做“过密化”的核心概念。黄反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依据西方经验所表述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看法,认为商业化并不一定会导致斯密和马克思所相信的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黄指出,从明清开始,江南出现了高度的商业化,但商业化导致的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反而是它的巩固和增强。明清之季江南的农业已面临强大的人口压力,而商业化造成了市镇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对花纱布和丝绸形成了很大的需求,因此而促成了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给农业的多余劳动力带来了出路。然而这发展和出路却使得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经济更为凝固。在男人种地时,妇女和家庭的其他辅助劳动力通常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劳动力高度集约化的花纱布和蚕桑业的生产。这些家庭劳动力一般不经济学上的工资报酬,但为家庭带来了收入;由于没有劳动力成本,他们的产品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是市场上机器所生产的同类产品所难以竞争的。这种亦农亦副的生产在家庭内部形成了劳动力的分工和农副业收入的互补,巩固了小农的家庭经济,使得工业革命没有可能和必要。但也正由于他们不计劳动力成本并常常增加工作时日,他们的生产率和劳动力的日平均报酬则是边际递减,使江南的家庭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下降的内卷化发展。瓦解这一小农经济的凝固力需要靠增加“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小农经济中的大量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虽然黄并没有指出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怎样才能发展起来。(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pp.1-5,11-15,77-92,137-143,161,305-324.)
黄宗智的这两本书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问题贡献了新的看法。通过否定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适用性、证明中国是一个例外,黄宗智为“中国特色的道路”从学术角度做了最好的注脚。
但黄宗智的理论也激起了辩论,其核心是人均收入问题,因为黄是从农民的人均收入递减的角度建立起他的理论的。1989年,布兰特(Loren Brandt)在其《商业化与农业发展》一书中指出: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东部与中部5省中,农民的人均收入在1870-1937年中有了增长,其原因是商业化导致的市场的专业化发展。这一专业化导向农民为市场而进行生产,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收入机会,又反过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投入。比如在1930年代5省中已有40%的农民使用了商业肥料,显示出较高的再投入。因此,布兰特认为,商业化的发展正是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原因。(注:Loren Brandt,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78-180.)在同一年,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付大伟(David Faure)也分别出版了《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解放前中国的农村经济》。两位学者都各自论证和指出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注:Thomas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80-329;David Faure,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193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2-211.)这三本书表明,黄宗智的理论没有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并且,由于黄的两本书都已译成了中文,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辩论。吴承明1989年在《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中赞成黄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所做的“内卷化”的分析,而慈鸿飞在1998年《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中则指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农民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并因此而增加了人均收入。(注: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63-77页;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1998年,第1期,第91-106页。)
如果中国近代农民的人均收入没有递减,那么黄宗智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整个看法失去了基础。另外,黄的《华北》一书中提到经营地主的农场只占整个华北农业生产的10%,以这样的比例来论证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化论据显得不够充足。白凯(Kathryn Bernhardt)在黄的《长江三角洲》之后所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地租、田赋、农民抗争》一书中指出,自清明以来,江南永佃制度盛行,地主纷纷进了城,结果是佃户和地主通常互相不认识,而地租通常由官办的租税谘议局等机构代收。这种永佃制对佃农有利,它使佃农完全控制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在民国期间,官办机构常以对佃农有利的方式来议定地租,在灾年时为佃农争取减租免租。(注:Katyryn Bernhardt,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2,pp.225-232.)
如何认识近代农业的基本问题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黄宗智指出,中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决定了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西方经典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经济来促成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中国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模式。(注:黄宗智:《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89-94页。)马若孟则认为,日本和以人均算比中国大陆更加人多地少,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使它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为什么不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会使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注:Ramon Myers Interview,June 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