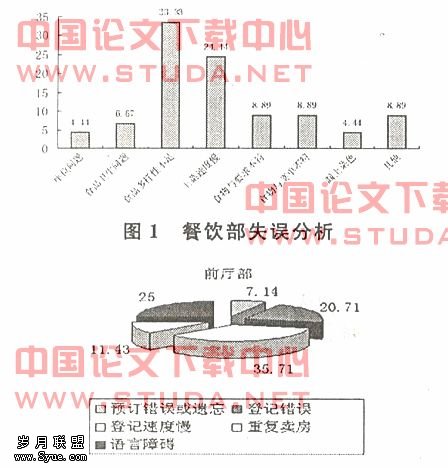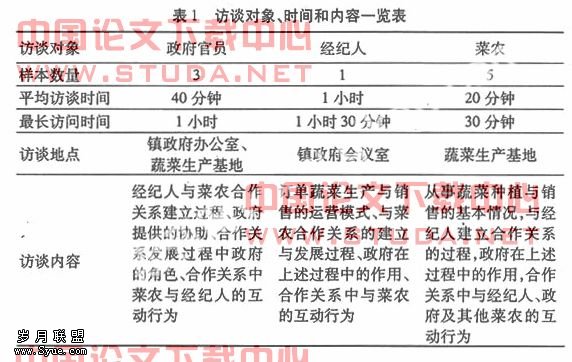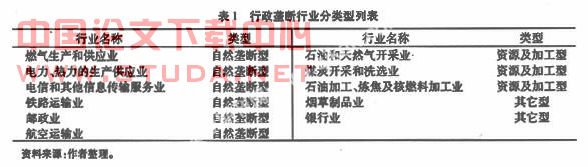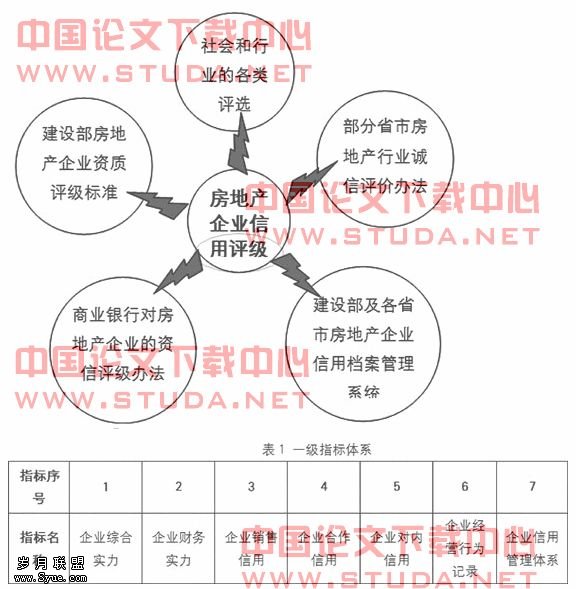关于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若干思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关键词:生态问题;农业开发;环境变迁;传统农业
随着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渐趋于白热化。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诸种危机,诸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的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而表现出的“人祸”,即是人类自己所亲手酿造的恶果。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对历史时期人类自身开发方式、生存方式的深刻反省。作为一个农业素称发达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的许多学者在追溯生态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的时候,也自然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所关注,甚至远溯至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奠基形成时代,认为此即祸患之始也。这些认识的产生,在当前生态问题空前严峻的背景下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相当的警示意义;但仔细推究,这一结论似乎缺乏充裕的事实依据,而其研究问题的方式与思路也似乎与历史研究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种结论与思路的产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生态问题产生主要原因与时代的关注视线,虽然减轻了今人的内疚与自责,但却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
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
正确地认识与估价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孤立地从其某一个方面简单地臆测或武断,而是要系统地、全面地分析考察,即需建立一种“整体史观”。对于古代农业开发经营中的生态问题的认知,也同样需要如是视角。在古代社会,在农业生产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条件下,认识农业经营开发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必须把其放在一个长时段下系统地考察。也就是说,我们在注意农业开发经营所产生的诸如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等消极影响同时,还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其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尤其是从社会时间这一角度权衡把握二者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传统时期的农业开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前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其一,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先民赖以生存延继的最主要方式。“民以食为天”,生存是人类诞生以来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人类诞生之初,其最主要的经济方式是采集与渔猎,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茹毛饮血,生存条件相当的恶劣,故此,探寻新的生产方式就成为了人们的共同愿望;而农业这一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正是在这一探寻过程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完成的。应该说农业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不仅使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亦加速了“人猿揖别”的历史进程,也因为如此,其在传统社会一直是绝大多数民众的衣食之源和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也是农本观念最基本的含义。以之为基点,还衍生、引申出许多的涵义:“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谐辑睦于是乎兴,财用番殖于是乎始,敦庞憧纯固于是乎成。”[1]
其二,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华民族兴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和重要纽带。中华民族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以辉煌的文明成就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成就的获取,不能不说与农业的开发经营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反顾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炎黄部落的率先崛起是得益于对农业的关注,而此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也是以传统时期农业的开发经营为主要载体与途径的一个逐渐凝聚的过程,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与农业开发经营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三,农业开发经营是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基础。正是以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文化的发展迈进为基础,我们的先民不仅率先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而且创造了一系列的灿烂辉煌,使得古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不惟如此,中国的农业文化还是构筑中国传统文明最基本的要素与基础,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理论、价值观念、思维以及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农业文化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基。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忽略和否认的事实,也应该成为我们探讨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农业开发经营中生态问题的历史性
生态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不可辩驳地说,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与历史时期若干生态问题的逐渐积累密不可分;而当时生态问题的产生也是与农业这一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联系。譬如大量原始森林的破坏,即与原始农业时期“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3] 这一刀耕火种式的农作方式相关,与传统时期农业区域性拓展过程中的与山争田、“斩伐林木亡有时禁”[4] 相联系。再譬如生态脆弱地带的土壤荒漠化问题,也是与历史时期农业发开之触角延及诸多生态脆弱地带,破坏其植被相关。考究史册我们也不难发现,由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经对当时的生产与生活产生诸多的危害,而且亦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如秦汉时期的贡禹在探究当时灾患频仍原因时的“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之谓、刘向在《别录》中的“唇亡而齿寒,河水崩而其坏在山”之喻,等等。明清时期类似的记载与言论则更为丰富。对于这一点,不仅已为众多的学者所充分地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历史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踪迹,故此不再赘述。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问题过分地简单化。既然其是一个历史过程,就意味着传统时代面临的诸种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如我们今天一样如此严峻;而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对环境作用程度相联系,还可以看出不同时期所面临生态问题的内涵也是有所差异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环境史研究的成果,把其放置在整个世界文明史发展进程的长时段中加以分析。环境史研究成果表明,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环境与前文明;人类中心主义——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而其分界点分别为1492年和1969年。[5] 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而言,生态问题的严峻以及人类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是始之于近代化,这同样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历史事实,所以有些学者就曾明确地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产生于市场机制”。回顾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严峻,同样也是始之于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及其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日增相一致的。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不宜对传统时期生产经营方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过分的夸大。
再具体到中国古代历史内部来看,我们也同样不难发现,真正的、整体性生态问题的凸显也是始之于明清时期[6]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明代以后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从各个角度、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总量的方式与方法。人们一方面从提高单产的角度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提升精耕细作程度,这是使得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在这一时期迅速达到了巅峰状态的基本动力之一;掀起了又一次的水利开发之高潮,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设施与环境……等等。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纵深的、内涵式发展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因此,农业横向的、外延性开发,即地域性的拓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高潮。同时,由于宜农之地早在历史时期就已经开发殆尽,所以其触角亦不可避免地延伸至陡峭山岭、草原牧场、水泽湖泊,宋元而始的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趋势至此而达到高峰:长江中下游河湖纵横地区,人们围垦湖面及滨江濒湖之洲滩,以致出现了“江右产谷,全仗圩田。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7] 之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则大量围垦荡地,至明中叶已是“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再掀高潮,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全无耕牧”,但“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人烟稀少乃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更是当时开发之重点区域,“国家承平,二百年兹矣,各省生齿繁盛,浸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开垦”[8] ,尤以鄂豫陕交界山区之开发最盛,“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师承瀛:《浙西水利备考》杭嘉湖三府三道总说),“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清·嘉庆《建始县志》)
明清时期的大规模农业垦殖,虽然有充分利用土地、缓解需求压力之利,但又因其重点区域大都为生态脆弱之地带,且开发经营也往往缺乏规划、不计后果,所以也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9]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此前大都“林木葱茂”,但由于明清时期的不断垦殖樵采,至清代已“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以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为主,故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则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故明代后期以后,许多河流“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使得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其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
总而言之,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传统农业经营时期的生态问题总体上不宜过分地夸大;而在其内部,也经历了由区域性到整体性、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微到渐次严峻这样的过程;是明清以降,这一问题才真正显现,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三、农业开发中生态问题的区域性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地理、气候、资源等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有不同的自然带之划分;而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环境,又与一定是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带。因此,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结合的农业生产,其开发经营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性,也明显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也就说,农业经营方式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否相适应、和谐,这是最终是否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之大小的关键。具体到古代社会,也同样是如此,农业经营在一些地区引发了生态问题,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恰恰相反。
在一些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带,农业的过度开发的确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甚至有些真是所谓万劫而不复。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区域的不断拓进、即其横向性的,是中国农业历史发展中最为主要的内涵之一。可以看出,在这一进程之中,中原农业民族以农业技术体系的率先成熟为动力,以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依托,以体系强劲的政权为后盾,使得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在各核心农区内大致呈现出一个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很早即把开发之触角延伸到了诸多非宜农地区,实质上历史时期以农牧分界线迭移为标志的、农进牧退之历史巨剧,即是这一进程的反映表征。在农业经营方式扩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态意识的缺乏和经营中的某种无序性,自然带来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文我们所提到的明清时期山地开发所引发的森林缩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尤其是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其生态环境总体上就相当地脆弱,而过度的农业开发又很容易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典型如秦汉时期盛极一时的河套平原开发,当时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屯垦等举措,很快将阴山以南、乌兰布和沙漠以东的广大农牧交错地带发展成为了新的农区,“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10] ,富庶几欲关中相媲美,故号之曰“新秦中”。然而今天的这里则是黄沙漫漫,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早已成为了历史遥远的回忆。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都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农业具有自然再生产因素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得农业经营在诸多宜农地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自然环境。譬如水利的兴修,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相当的显著,甚至可以说,水利从伊始就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著名如大禹治水、关中水利网的形成、四川盆地水利的兴修……等等,其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不容低估。史载郑国渠渠就之时,“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 ;都江堰修成之后,“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故成都平原遂有“天府之国”之谓。除此之外,具体到农业技术体系内部,也存在一系列的改善微观生态环境的措施与意识,对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做专题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四、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多元性
诸多的事实表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个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人类生产、生存方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包括了自然环境自身的变迁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地质变迁、气候干湿变化、气温的冷暖更替等因素,都可能引发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之后的结果。
首先,从长时段来看,自然环境及其变迁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基础和最主要因素。一方面,相对脆弱的环境基础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研究表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就与早在末次盛冰期就已形成的范围广大的古沙源相联系,虽然其在全新世适宜期发育了一定的草原植被,但却相当脆弱。正是因为这种固有基础的脆弱性,所以当农业开发的触角延及这一地区之后,便会很容易破坏这种区域性的生态平衡,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而且其恢复也往往是相当的困难。另一方面,所谓的沧海桑田这样的巨大变迁,实质上更多的是自然使然,而其中人为的因素是间接的、细微的。众所周知,与人类历史发展演替一样,大自然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变化过程,这其中包括了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地质变迁等诸多方面,其势必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时期诸多的生态问题,实质上很大程度的与这些自然因素变迁相联系。典型如楼兰古国的突然湮没,世人就有诸多的推理与猜测,如战争说、过度开发说、气候变迁说、冰川说、沙漠风暴说、河流改道说……等等[12] ,其中大都归因于自然因素变迁。有些学者还运用卫星遥感考古资料从环境地质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楼兰古国消亡的原因是由于古城所在地——孔雀河上游先后出现过两次滑坡崩塌而造成堵江,形成了堰塞湖切断供水源而导致[13] 。另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西北的气候环境在经历了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恶化事件之后,就大致呈现出一个由暖湿而干冷的变化过程,这一点也似乎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这一变化发展事实上与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应该有必然的联系[14] 。
其次,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从历史时期生态问题的产生、发展来看,的确大都如此。如上文我们所谈到的西北地区沙漠化发展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诸种活动破坏了原始的自然植被而引发,并伴随人类活动的深入而加剧的;而这一进程似乎又以农业的开发与发展为其最主要诱因。史籍记载中反映农业开发过程中伐木毁林的史料就相当地多,如居延汉简中的所见的“官伐材木取竹箭”、“二人伐木”等记载,就是一个例证。也因为如此,“加大了对植被的破坏程度,导致历史时期西北生态状况每况愈下,呈逐渐恶化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北地区后来出现的大沙漠即肇始于此。”[15]
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诸种人为因素中,除了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的长期积累之外,也包括了诸如战争、建筑兴修、城市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诸多文明的陨落更多地与战乱直接相关,典型如东汉时期西域屯田的“三兴三绝”,即具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北农牧交错地带,自秦汉始即为战乱纷争之地,因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一定的自然因素和农业开发的破坏外,可能也与战乱戕害联系。应该说,战争的破坏作用,除了表现在、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之外,还应该包括生态领域。此外,与农业经营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历代的大兴土木,即对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史籍中同样有相当集中地反映,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谓:“宫室奢侈,林木之蠹。”《山西通志》卷66也引明代学者阎绳芳文曰:“嘉靖初,元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于“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总而言之,对生态环境问题致因的诠释,不能仅仅关注于某一点,而应该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
五、农业经营中的生态思想与经验
农业生产是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一个生产过程,因此其与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势必对自然环境产生诸种影响,客观上改变着生态环境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农业生产作为一种利用、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地面临着环境问题。从这一特点出发,农业生产者必然会在主观上产生改善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某些意识,并以之为指导而注意把握自然、生产经验。探究传统的农业技术与文化体系内涵,实质上也的确不乏类似的诸多内容。
首先就是思想层次上的“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一种自然观,即《吕氏春秋·审时》所谓的:“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可以看出,其是把农业生产看作“天”(气候、季节)、“地”(土壤、地形)、“人”(农业生产主体)、“稼”(农作物)等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深刻地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依相亲、协调统一的关系[16] 。这一认识,不仅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内涵,而且也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渊源。因此,以之为指导和基本出发点,即有了所谓的“时禁”与“三宜”,即不仅要求开发中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而且还有必要树立一定的生态保护观念、明确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17] ,以达到永续性利用的目的。郑玄注《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伐山林”时说这是“顺阳养物”,可谓深得其旨。这一天人观,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思想。
其次,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也包含了诸多改善生态环境的具体技术与环节,典型如改土肥壤技术、农田水利环节。伴随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的扩展,农业生产的环境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必然会面临不同的一些壤土,因此,如何改土肥壤以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8] 。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先民不仅很早就认识到土壤性质的多样性,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分类体系,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土肥壤的观念和技术措施,如观念层次的“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说、“地力常新壮说”;如技术层面上以恢复地力为宗旨的轮作制度、用肥技术等等。这些技术措施与环节,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必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此外,我们上文所涉及的农田水利之兴修,其所产生的生态效益也同样是相当显著的。
再次,我们就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趋向而言,实质上也是在朝着对环境有利的方向发展,耕作制度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回顾中国农业科技史之演进进程可以发现,耕作制度大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原始撂荒制——三代时期的休闲耕作制——春秋战国时期的连种制度——秦汉魏晋以降的复种制度、套作制度、轮作制度。与耕作制度变迁的这一取向相适应,实质上还包含了耕作技术发展的取向,即是由原始的粗放耕作逐渐向精耕细作迈进,这些无疑也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因此,继承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农业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与借鉴。
结 语
总而言之,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其的分析与认识,应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并放置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下系统的考察:既要关注其消极影响,也要尊重其重大贡献,有必要权衡比较二者在谋求人类的生存及生存条件改善这一内在统一中的关系;既要注意历史时期生态环境问题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要适度考虑传统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其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与程度;既要注意农业开发在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略生态问题的产生从来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这一基本事实;既要看到开发与生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也必须注意二者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互动统一关系,等等。只有这样历史的、系统地考察这一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归因于历史、归罪于先民,这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中的生态问题给予的分析与评价,也才能真正地直面目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与途径。
注释
[1] 《国语·周语》.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
[2] 张岱年:《<农业文化>序》,见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3] 《盐铁论》卷一。
[4] 《汉书·禹贡传》。
[5] 包茂宏:《环境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6] 确切地讲,早在宋元时期,由于社会与的不平衡、尤其是区域性人口分布不均的影响,在江南一些人口密集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水争地、与山要田”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农业开发趋势,但其规模化、持久性的发展则是真正始之于明清两季,尤以清代最为显著。
[7] 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留致江西新抚部陈玉生书》卷27。
[8]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9] 高寿仙:《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与环境恶化》,《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0] 《汉书·匈奴传》。
[11] 《史记·河渠书》。
[12] 中国社会院新疆分院考察队:《罗布勃地区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
[13] 何宇华、孙永军:《空间遥感考古与楼兰国衰亡原因的探索》,《考古》2003(3),77~81。
[14] 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问题,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卓著的研究成果,如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等等,都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大致经历一个由暖湿而干凉的过程。
[15] 陈业新:《秦汉时期西北开发史鉴》,《光明日报》2003年2月25日。
[16]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化中的价值》,《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7] 倪根金先生《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一文从土地资源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特殊自然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污染防治等方面系统探讨了秦汉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详见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2),3~13。
[18] 曾雄生:《 适应和改造: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略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