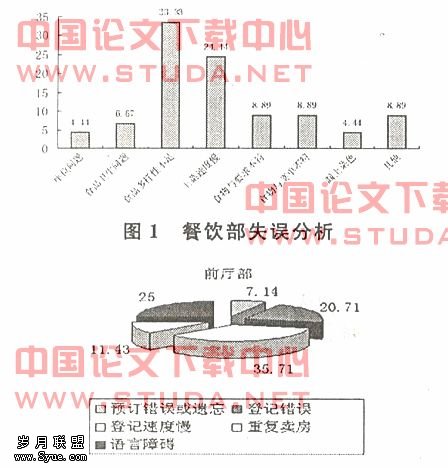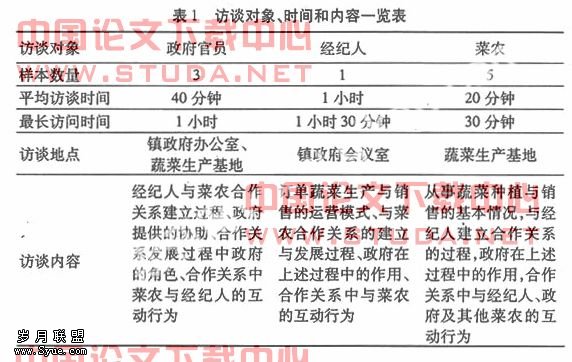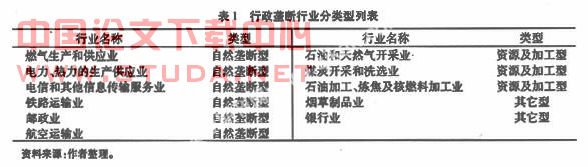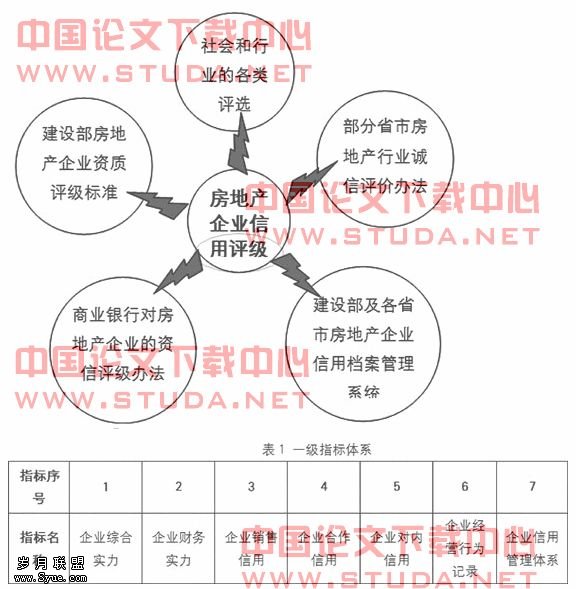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2)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通俗实用读物,包括各类“通书”、农书、尺牍、旅行指南等。此类书籍的出版,亦大盛于明清。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商业的发达,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万宝全书》、《水程一览》、《示我周行》、《天下水陆路程》、《客商一览醒迷》等,不断推出,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我在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人用书),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余英时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1] 。江南是明清商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大量的“商业书”刊行于此,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此外,江南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又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鲤飞样《雷公炮制药性解》,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唐翀宇镌徐氏《针灸大成》,三多斋刻《针灸大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2] 。
(三)童蒙课本教材
由于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的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续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等。因此同一书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3] 。其次,除了“三、百、千”外,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一方面,旧有的教材大量刊印、翻刻与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有《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另一方面,新编的教材也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据熊秉真统计,明代以后中国常见的童蒙教材,种类多达百种以上。第三,出现了大量采用故事、歌诀、图本形式的童蒙教材(如《新刻联对便蒙七宝故事大全》、许贯日《新镌注释故事白眉》、《金璧故事大全》、《书言故事大全》、《绘像注释日记故事》、《绘图蒙学歌》等)。第四,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教材也大量出现。在这些教材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后来还出了《绘图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也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方面专门知识的启蒙教材[4] 。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的产物,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商业化出版业中心的江南,这些教材的出版也以江南为最多。这类课本教材市场不小,江南商家不会坐视不动。因此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也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5] 。
(四)时文选本、文士诗文
明清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虽然有种种弊病,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十分规范化的考试方式。由于其规范化,因此相对于以往的考试形式来说,这种考试形式显然更为公平。同时,因为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较为固定,因此精读范文是成功的最佳捷径,而此前成功者的考卷又是最好的范文。为迎合这种需要,书商便雇人收集以往的中式应试文字,加以选择乃至评点,印刷出版。这类时文选本因出于书坊,故又称为“坊选”。《儒林外史》中的马纯上(马二先生)、匡超人等,就是受雇于书坊的职业选家。由于明清江南科举极盛,因此对此类应试书需求量也很大。不仅如此,因为江南是当日中国教育的中心,江南出版的时文选本在外地的名声也很大,因此造成对江南时文选本的更大需求。顾炎武引用杨彝(子常)的话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问”。这些书大多出于江南,“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6] 。
时文选本最早出现于江南,大约是在弘治朝,不过为数尚不多。到了嘉靖朝则大盛,以致李翊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7] 。上元、江宁为应天府附郭之两县。两县刻有不少八股文,即所谓“时义”。当时有人建议要把这“两县及建宁书坊所刻时义,尽数烧除”。两县所刻时义,与建宁书坊齐名,可见其产量之多[8] 。到了清代,愈加兴隆。《儒林外史》中对此多有描写,从中可见当时江南时文出版中心之一的杭州,此项事业规模已颇大。例如该书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由于坊选泛滥,引起国家的重视,清代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坊选本流行,但都无济于事,以致国家甚至考虑自己来精选范文出版。
此外,明清士人,趋名若骛,多有自费印刷文稿,传播士林以求名者。此风又以江南最盛,明清之际小说《鸳鸯针》卷三《双剑雪》,就描写一个山东假名士卜亨,到南京坐监。到南京后,即将以前自己所作、央人代作以及剽窃他人的诗文,编成诗文集各一部,叫刻字匠刻了,印了千余本,逢人便送,居然骗得盛名,“借此声势,重新开辟乾坤,又在南京摇摆起来”。此后继续行骗,将枪手代作的八股文字,又刻成《南雍试草》、《乡试朱卷》,招摇撞骗,以致“三吴地方的名士,无不闻风相思,见面恐后。……那江楚远来地方,求诗求文的,堆架满案,应酬不暇”。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已成为制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
事实上,在明清江南,不仅文人依靠刻书印书以沽名钓誉,而且市井小民也用印刷品传播丑闻,中伤他人。明末江南小说《贪欢报》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中就讲道明代杭州人朱芳卿、龙天生,都私通对方之妾,但是又害怕“播扬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街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刊行这些沽名钓誉的文选或者传播丑闻的文字,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动机各异,但从出版业者的角度来说无非是为了赚钱。因此这类读物盛行于江南,也证明了江南商业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
(五)宗教书籍
宗教书籍的印刷在江南有一定规模,例如上述藏板于大报恩寺的《南藏》,后来一直在使用。郑和曾利用该刻板先后印造10部,而到了万历时代,更“广为印行”,每年约印20藏。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和尚,可在印经铺内住宿,每印一部,须付报恩寺板头钱二十两,该寺靠这副经板,每年可得到几百两银子的收入[9] 。明代后期南京来宾楼姜家似为专印大藏经的经坊。此外,万历初西方传教士在南京建立天主教,江西人周用印书为生,在南京开设书铺,被诱劝入教,在教堂内翻印经卷;曾被官府逮捕。南京教堂重刻了利氏《交友论》(1699年)、《畴人十篇》(1609年)。利氏《万国舆图》(又名《山海舆地全图》),也有吴中南京翻刻本(1600年)。不过,宗教书籍的印行受到种种限制,出版数量不会很大,特别是在清代更是如此。
(六)年画、日历、迷信用品
年画、日历、迷信用品等印刷物,出版数量也不小。清康熙以后,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已名扬海内,与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年画,并列为南北三大民间年画流派。乾隆时,苏州阊门外山塘街和阊门内桃花坞有画铺多家,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日本。桃花坞年画主要面向中下层社会,作品题材广泛,为一般民众喜闻乐见,印刷量当不少。与此同时,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10] ,大概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日历印刷,亦以清代中叶苏州为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这种历本也常常由城乡里正地保强行摊派人民购买,他们于腊月间“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加市价而倍之,号‘送历本’”[11] 。如此“逐户分送”,其发行量自然甚大,非一般书籍所能及。苏州玄妙观,亦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由于“乡村人家,新年贴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借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12] ,因此印刷数量肯定不少。迷信用品的印刷量也很可观。康熙时无锡锡山印制的门神极为有名,“天下以锡山所出为最,丹青人物极工。自京师以下,贩鬻无远不暨”[13] 。乾嘉时的苏州,腊月间各纸马香烛铺也“预印路头财马”以售之[14] 。黎里镇上则“有印神佛纸马者,用油纸雕穿为范,以苏墨汁刷印,谓之‘榻马’。其精者用笔勾清,饰以金采”[15] 。此类印刷品之盛行,当时的小说中说得更加透彻。清代江南小说《山水情》第六回中,讲到有两位苏州郊外的尼姑,商量说:“我这里施主少,斋粮淡薄,昨夜困在床上思想,不若印些佛图出去,沿村一派,做各西资会儿,收些钱、线、米、麦之类,混帐混帐”。“主意定了,停过一日,买了纸张,印就无数佛图,出去沿村派过”。可见这类印刷品的销售,一直深入到乡村人家,城市中就不用说了。此外,明清江南民间盛行斗纸牌,纸牌印制也应运而生。雍正时,镇洋人钱三即因印售纸牌而获罪[16] 。
最后,我们要强调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的主要特点,即高度的商业化。
首先,明清江南民间出版印刷业既然完全以牟利为目的,故往往急于求成,刻工多不精。谢肇淛指出在万历时情况已如此,“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因此之故,刻书滥恶,而“近来吴兴、金陵駸駸蹈此病矣”[17] 。田汝成则说:“杭人作事苟且,重利而轻名。但顾眼底,百工皆然,而刻书尤甚”[18] 。湖州凌氏是有名的出版商,所刻经史子集之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19] 。以往史家往往对此予以恶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出版印刷业商业化的表现。
其次,明清江南书坊主为了牟利,使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多、快、省地出版能够赚钱的畅销书。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明代无锡华氏是一例子。华珵用铜活字版翻印秘笈,“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20] 。明季“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剿闯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21] 。江南书坊刊行小说之快,实在惊人。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清代苏州书贾鉴于江南劳动力价格较高,在本地刻书不够划算,于是“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就[顺德县]马岗刻所欲刻之板。板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见者以为苏板矣”[22] 。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还拥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为其创作,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冯梦龙。时人张无咎在《平妖传》序中称冯氏“著作满人间,小说其一斑”。可见他的文名通过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而举国皆知。更令人叫绝的,是书商为了赚钱而雇佣落魄文人编写畅销书。“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23] 。甚至有公然伪托当代名人之作,以“取悦里耳”者。当时人云:“比年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画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数年前温陵事败,当路令毁其籍,吴中锓藏书版并废。近年复大行,于是有李宏父批点《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红拂》、《明珠》、《玉合》数种传奇及《皇明英烈》,并出叶笔,何关于李!”“坊刻《大唐西域记》,后乃杂三宝太监下西洋事,令元奘绝倒地下矣”。此外还伪造《琅环记》、《缉柳编》、《女红余志》、《黑旋风录》、《顾氏诗史》等多种。不仅坊刻如此,官刻亦倚此规利。“近吴中官刻几汗牛,滥用责人千金,以冯观察诸公言之,并是伪托者”。这些伪书畅销外地,有远销至太原者[24] 。由于商业化的出版印刷业在江南迅速,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书商绞尽脑汁以求牟利,以致盗版猖獗。冯梦龙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25] 。袁宏道则说:“往见牟利之人,原板未行,翻刻踵布”[26] 。具体的例子如万历时杭州书商刻印《月露音》,于书后加盖朱印,称“如有翻刻,千里究治”;崇祯时南京书商在其出版的《道元一气》书前也附有告白:“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27] 。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商业化出版印刷业中竞争的激烈。这些行径,虽然为今日产权法所不容,但也表明了明清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是一种完全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大众的。
四、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
所谓外向化,是我在一部在海外出版的拙作中创造出来的一个名词[28] ,意思是一个地区工农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以及肥料、燃料、材料等)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则要依赖外地市场。这种外向化表现了较高水平的商业化,因此一个产业部门的外向化水平的高低也更充分地体现了该部门生产的商业化水平的高低。而就是在明清时期,江南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一)原料输入
出版印刷业的主要原料是纸张。虽然江南造纸业在明清时期颇有,但是由于需求增长更快,因此仍然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纸张。对于江南纸张的输入情况,吴承明、范金民已有颇多研究[29] ,兹亦主要依据他们的研究进行归纳。
明清江南从外地输入的纸张,来源地颇广,名目也颇多[30] 。但是从大宗贸易来看,明清江南输入纸张的主要来源地是皖南、浙东、江西与福建。其中特别是江西和福建,地位更为重要。
皖南的宣纸是著名的名纸,明清徽商、宁国商人将宣纸贩运到江南的记载颇见于史籍。此外也有皖南池州商人将纸运销江南的记载[31] 。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苏州修建徽郡会馆,皮纸帮是三个发起商帮之一,可见其生意不小。浙东的常山县所产纸也颇为有名,“凡江南、河南等处赃罚[用纸]及湖广、福建大派官纸,俱来本县买纳”[32] 。
江西向江南输出纸张的规模比皖南更大。明代松江名笺潭笺(谈笺),就是以江西荆川连纸加工而成的[33] 。浮梁的楮皮纸、南昌府的奉新火纸、瑞州府的新昌火纸与表心纸、高安县的青纸等,也运销江南。嘉庆元年江西旅苏各行业商人在苏州共同捐资重修江西会馆,其中就有南昌府纸货众商(捐银700两)、山塘花笺纸众商(捐银300两)、德兴县纸货众商(捐银75两),桐城县纸商(捐银80两),在捐款的11个行业的12个商帮中,纸业商帮就占了4个,捐款总数(共计1,155两)也仅次于麻货众帮(1,200两)[34] 。清代中期南京状元境的书坊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35] ,其纸张供应也主要来自江西。
福建在明清时期一直是江南主要的纸张供应者之一。三藩之乱时,福建纸输出受到影响,于是江南纸价骤涨,乱平后方逐渐平落[36] ,可见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福建纸之输入对江南纸张供应已有重大影响。康熙六年,旅苏的汀州上杭六串纸帮于在苏州成立了汀州籍纸商会馆--汀州会馆。直至道光时,福建永安纸商仍活跃于福建与江南之间[37] 。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由于江南对纸张的依赖日甚,为保证纸张供应,江南出版商还到江西、福建等纸产地去专门订购或包买纸张(即“压槽”)。明代后期江南著名出版商常熟毛氏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38] 。福建著名的建阳竹纸(建阳扣),自康熙以来,被“吴中书坊每岁以值压槽,禁不外用,故闽人不得建阳扣”[39] 。
(二)产品输出
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产品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还大量运售外地。明末毛晋所刻之书,“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故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40] 。不过比起通俗文艺作品及时文选本等畅销书籍来,汲古阁所刻之书的销路又差多了。到了清代,江南出版的畅销书的输出,成了一项重要的生意。反映乾隆时代山东民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其第三十三回说:“这穷书生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夥伴,自己亲身子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沿途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生意?……至于什么缎铺、布铺、紬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为官府赔垫”。《儒林外史》第十八回中,书坊文瀚楼主人雇不第举子匡超人批点一部考卷,说:“我如今扣著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回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第二十回中匡超人对人说:他选点的时文,“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著买,只愁买不到手”。
除了国内各地外,江南书籍还大量输往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特别是日本,已成为江南书籍的重要市场。在此方面,除了吴枫、山脇悌二郎等的研究外[41]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庭修的研究。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18世纪初期江南向日本的书籍输出规模颇为惊人。例如1711年(日本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商船共54艘,其中有6艘载有书籍,各船载书数量为:15号南京船--93箱,51号南京船-40箱,25号南京船-1箱,19号宁波船-4箱,37号宁波船-1箱,10号宁波船-2部。次年到达长崎的中国船中,载书船的数量略有增加,其中40号南京船载书82箱,57号南京船载67箱。有意思的是,在此时期到达长崎的载书船基本上是南京船与宁波船,福州船不见有载书之例,而广东船载书也只是例外情况。在南京船与宁波船中,宁波船载书数量很少,多则数箱,少则数部,因此大量运载书籍到日本的基本上是南京船。日本当局鼓励中国书籍进口,1691年(日本元禄四年)曾向长崎的“唐船头”(中国商船船长)发出求购中国书籍的命令,“若明年出船渡海,应载来书籍等物”。1709年(日本宝永六年)还具体指定了购书内容。因此尽管清代政府有时对中国书籍输出日本有限制,但是输日书籍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例如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在前述正德元年到达长崎的21艘南京船和14艘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船只总共是6艘(南京、宁波船各3艘);而到文化元年(1807年),进入长崎港的11艘船中就有10艘载有书籍[42] 。从上述51号船所载书籍目录来看[43] ,南京船运载到日本的书籍,主要为经学、文学、、医学、本草等书籍(其中以文学类尤多),与江南流行的书籍无大差别。这些书籍都是在江南(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印刷出版的。大庭修认为从航行天数,从南京到北京的航程与从南京到长崎的航程大致相等,由此而言长崎在获得江南书籍方面的便利堪与北京匹敌[44] 。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所需要的纸张,越来越严重地依赖输入,而所生产的书籍则越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因此江南的出版印刷业的外向化水平也日益提高,日益成为一个“两头在外”的产业部门。这一点,也有力地证明了明清江南出版印刷业商业化水平的提高。
以上四个变化,表明江南的民间出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有了重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已不再是一个生产能力狭小、仅只为官府和上层社会服务的行业,而变成了一个按照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商业化的产业部门。由于出版印刷业的特殊功能,因此上述变化,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明清江南发展的特点,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探讨明清江南的社会生活与大众文化的变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 余英时:《思想传统的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7年,第363-364页。
[2] 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3] 例如《三字经》,仅目前可见者就有宋末元初的1,068字本、明代的1,092字本、明末的1,122字本、清初的1,140字及1,170字本等多个版本。见梁其姿:《‘三字经’里时间的问题》,收于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台北),1999年4月出版。
[4] 参阅熊秉真:《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0年,,第144-153页。
[5]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433页。
[6]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条。
[7] 《戒庵老人漫笔》卷八。
[8] 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9] 张秀民:《明代江南的印书》。
[10] 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年,第92页。
[10] 《清嘉录》卷十二“送历本”。
[12] 《吴门岁华纪丽》卷一“城内新年节景”、“春牛图”。
[13] 康熙《无锡县志》卷十土产。
[14] 《清嘉录》卷十二“年市”。
[15]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16] 乾隆《镇洋悬志》卷十四逸事。
[17] 《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18]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19] 《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20] 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十五人物。
[21] 《历年记》上。
[22] 咸丰《顺德县志》卷三。
[23] 《水东日记》卷八。
[24] 《戏瑕》卷三“赝籍”。
[25] 冯梦龙:《智囊全集》,第569页。
[26] 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刊于《浙江学刊》1989年第3期。
[27] 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
[28] 原文为externalization。见拙作《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Macmillan Press (England) and St. Martin’s Co. (USA), 1998。
[29]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416-417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第89-90页。
[30] 例如清代前中期通过浒墅关输入江南的外地纸张中,仅有名者就有光古、灰屏、黄倘、连史、元连、白鹿、毛长、对方、毛边、江连、黄表、桑皮、碑色、东坦等(见道光《浒墅关志》卷五小贩则例)。
[31]康熙《池州府志》卷三物产
[32] 光绪《浙江通志》卷一○六物产六。
[33] 项元忭:《蕉窗九录》。
[34] 《重建江西万寿宫会馆碑记》(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223页)。
[35] 《白下琐言》卷二。
[36] 《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37] 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九风俗志“商贾”。
[38] 例如汲古阁刻书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见《书林清话》卷七。
[39] 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
[40]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41] 参阅吴枫:《中国古典学》,齐鲁书社(济南)1982年,第253-254页;山脇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吉川弘文馆(东京)1964年,第245页。
[42]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61、62页
[43] 该船运到长崎的书籍共40箱,86种,1,100余册。见前引大庭修书,第68-70页。
[44]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62页。
上一篇:试论清代农业的成就*
下一篇: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