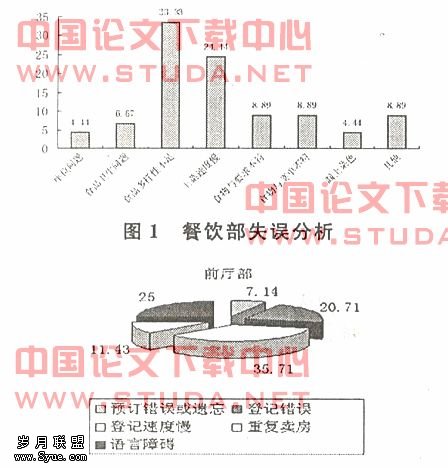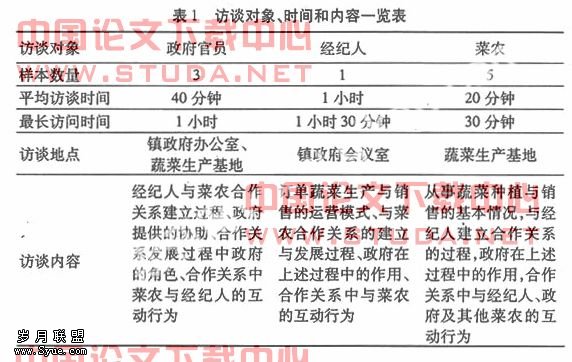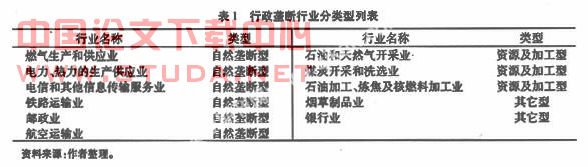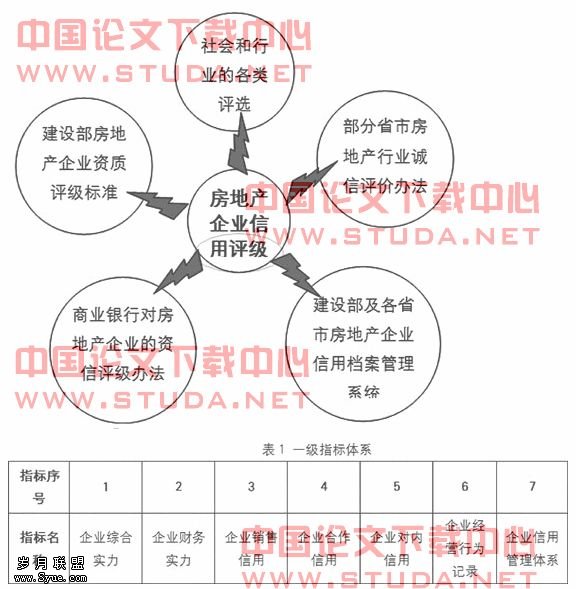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道光《苏州府志》卷10说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虽然这个说法无疑有夸大,但城市人口在苏州府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高则是可以肯定的。苏州府本是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之处,而苏州地区(即吴、长、元三县)又是苏州府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仔细来看,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人口有很大变化。对于这个变化,我们也从府城与郊区市镇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府城的人口变化
明代后期苏州府城(城内及城厢附郭)人口的数量,以往学人的估计颇为悬殊,但近来渐趋一致。例如刘石吉估计16世纪末府城人口有50万人(86)。曹树基在其较近的研究中,也估计明代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人(87)。清代的府城人口,王卫平估计在康熙时应在70万左右(88);嘉、道时,据时人所言,已达百万以上(89),这个估数在学界已无多争议。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府城的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从50万左右增加到100多万。
(二)郊区市镇的人口变化
由于史籍中所保存的市镇人口数字非常有限而且不很明确,因此要依据这些人口数字的零星记载来重建明清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量并以此为据观察人口的变化,非常困难。这里我们将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考察。
1、使用现存明清记载推测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史籍中保存着一些关于明清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数字的记载,其数量虽然不多,而且大多不很明确,但毕竟是比较直接的记录,应当认真加以分析,然后充分利用。据刘石吉统计,居民户数在1,000户以上的苏州郊区市镇有2个,即吴县的光福镇(居民“聚于镇者千余户”)和元和县的周庄镇(居民“不及五千户”),时代都是清代中期(前者是道光时,后者是嘉庆、道光时)。此外刘氏还指出:吴县枫桥镇在民国初年有1,890户。该镇在清代中期是江南最大的米谷贸易中心,因此其极盛时代的人口应当多于民国数字。还有些大聚落虽名称不叫作市镇(例如同治时吴县的徐墅村,有居民3,000余户),但事实上也属于市镇(90)。除了刘氏所谈及的情况外,还可从明清史籍中发现一些史料,表明苏州郊区市镇人口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有明显的增加。例如唯亭镇,在乾隆时代已是“比屋万家”。浒墅镇,在万历时居民已达数千家,入清之后更趋繁荣,因而镇上居民数量肯定更多(91)。甫里(又名*[上为撇下为用]直、六直)在明末才成镇,但到了康熙中期,镇上居民已有1-2万户(92)。因此仅只是上面提到的光福、周庄、枫桥、唯亭、浒墅、甫里等6个市镇,清代中期盛时的总户数就应当在3-5万户之间,居民人数则在15-25万之间,从其他关于苏州郊区市镇的记载来看,许多市镇如虎丘、木渎、甫里、陆墓、陈墓等,到了清代中期工商业都十分繁荣,拥有颇大数量的工商业人口,因此其市镇人口数量应当不在少数。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有关苏州郊区市镇的人口数字,基本上都是清代中期的。以前的数字未有记载,原因大概是以前居民较少,因此未能引起时人的注意。这也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市镇人口确有明显的增加。
2、从城市化水平推算市镇人口及其变化
虽然上述记载表明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郊区市镇人口有迅速的增长,但是仅仅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仍然不可能全面了解市镇人口的变化情况。因此这里我们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探讨。这种方法即: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的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来推算苏州地区(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这样做的理由是:即使除去府城居民后,苏州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属于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县份之列,其城市化水平肯定高于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93)。之所以选择吴江县作为参照的原因,一是据现有的材料,只有吴江可以作这样的数量估计;二是吴江也是苏州府属县,又毗邻吴、长、元三县,各方面的情况彼此相差不甚远。但是由于吴、长、元三县的城市人口有很大一部分住在府城内,因此除去府城居民后,这三县的城市化水平略低于吴江县(94)。因此,这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应当在除去苏、杭、宁三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与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之间。下面就此进行分析。
(1)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按照我的估计,除去苏、杭、宁三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总水平,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分别约为9%和15%(95)。
(2)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用明初吴工人口数字和3.4‰的年平均增长率,出崇祯三年(1630)前后时吴江县城市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1%,略低于他对扣除府城人口后苏州全府县城及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11.5%)的估计(96)。到了清代中期,依照刘石吉对乾隆九年吴江县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所作的估计,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5%(97)。换言之,在这三个世纪中,吴江县的城市化程度提高了1.7倍。
(3)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以除去苏、杭、宁三个大城市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总水平为下限,而以吴江县的城市化水平为上限,那么可以得知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即吴、长、元三县除去府城居民后的城市化水平),明代后期应在9-11%之间,在清代中期应当在15-35%之间。如果取其中数,那么明代后期当约为10%,清代中期则当约为25%,即分别约为吴江县相应水平的90%和70%。这个估计距离实际情况应当不会太远。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估计,那么在这三个世纪中,苏州郊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大约1.5倍。
(4)苏州郊区市镇人口估计:明代后期吴、长、元三县的人口总数不详。曹树基估计明初人口约为60-66万口(98),按照明代江南的人口增长率,到了1620年时应为86-94万(99)。而从当时的一般描述来看,苏州人口应当偏于曹氏估数的上限,再考虑到这三县有不少外来人口居住,姑以100万计。除去府城人口约50万,尚余约50万。依照上述10%的城市化水平,市镇人口总数大约5万。道光20年这三县共有居民300余万(100),其中府城居民为100余万,郊区人口约200万。依上述25%的比例计,可知市镇居民总数约50万,亦即比明代后期猛增了9倍。
(三)苏州新增城市人口的来源
在研究明清苏州城市人口变化的时候,一个重要问题是增加的城市人口来自何处。依靠现有的人口史料,我们无法得知明清苏州城乡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方面究竟有多大差别。如果没有很大差别,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就是因为外来人口移入城市所致(101)。因此是否有大量外来人口移入,就成为判定明清苏州城市人口是否真有明显增加的关键。
明清苏州府城人口的增加,颇大程度上是依靠从较远地方来的移民。据可靠的记载,康熙末年“苏城内外踹匠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系外来”,“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102)。这些工匠主要来自数百里外的江宁、丹阳,“孑身赤汉,一无携带”,“食力糊口,俱系愚民”(103)。到了雍正初,苏州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104)。府城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乾隆时府城有纸匠800人,都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105)。玉器工匠原来主要是本地人(后称“苏帮”),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称为“京帮”。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106)。而苏州府城的制烛业,则几乎完全由绍兴人把持。外地商人侨居苏州府城的人数,其数也很大。明代后期人郑若曾说当时在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107)。而乾隆《吴县志》更说“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 闠者,半行旅也”(108)。府城的阊门一带,更是外地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说:“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109)其中仅是聚居于南濠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110)。因此在府城中各种外地移民的总数,当然很大。
郊区市镇的情况可能与府城有所不同。从江南其他地方的情况来看,不少工商业市镇中也有很大数量的外地劳工和商人(111)。但是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尚不能得出苏州郊区市镇的情况也如此的结论。对于苏州郊区市镇而言,更可能的情况应当是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周围。如后所述,苏州府城与郊区市镇工业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体系,而市镇工业处于这个体系的下层。由于这种分工,市镇工业可以主要依靠本地的人力资源,而无需引入具有更高技能的外地劳工(112)。
由上可见,在本文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人口数量增加颇大。首先,郊区市镇人口与府城人口合计,明代后期这三县的城市人口总数55万以上,占总人口的一半略多;清代中期增至150万以上,也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两个比例虽然相近,但是城市人口的总数却增加了近两倍。其次,虽然从绝对数字来说,府城人口增加了50余万而郊区市镇人口只增加了约45万,似乎二者增加相差不多而府城还略占上风;但从增加幅度来说,市镇人口增加了9倍而府城人口只增加了1倍,亦即前者的增加速度远快于后者。在此意义上而言,郊区市镇人口的增加对苏州城市人口的增加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六、明清苏州的城市及其
在像牟复礼所说的苏州这样一个城乡相互开放的社会中,城乡工业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市镇工业与工业之间,更是如此。这就出现了一种可能:一些工业虽然地理位置是在市镇上,但是其性质却与周围的农村工业无异。换言之,所有位于市镇中的工业未必都是城市工业。因此在讨论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之前,我们还必须对市镇工业的定位作一讨论。
(一)市镇工业是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
在明清江南,农村工业和市镇的兴起是两个同时出现的重要现象,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市镇常常扮演着农村工业产品的加工与集散的角色(113)。因此之故,在以往的研究中,市镇工业常被视为农村工业的延伸。这种看法与近年来西方的“原始工业化”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114)。而在西欧的“原始工业化”中,农村工业与城市商人的接触点就是农村集市(或者小市镇),因此这种集市(或者小市镇)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村工业提供服务。由此而言,把市镇工业视为农村工业的延伸,也并非没有道理。
明清苏州郊区市镇工业究竟应当定位为城市工业还是农村工业,关键是弄清市镇工业与府城工业及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没有一条清楚的界线,并不意味着市镇工业与农村工业没有差别。我认为: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别,不仅在于地理位置方面,而且也在于生产的性质和方式等方面。从生产性质上来说,农村工业基本上是一种很小范围内的地方自给性工业,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原料和市场;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一种“外向型”工业,即其所使用的原料较多来自外地,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外地市场。在生产方式方面,农村工业主要是农家副业生产,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都较低,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工匠的专业生产,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以及产业层级等方面都处于较高阶位。
这些差别在明清苏州地区的工业中都表现得很清楚。大体而言,在生产的性质和方式方面,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分别处于两极。典型的例子例如纸张加工业。在此工业中,烧纸、油纸的制作主要在农村(115),主要依靠农村自产原料,产品主要供给地方市场,生产技术较为简单,产业层级也较低,相反,笺纸制作位于府城内,原料来源与产品市场都主要在外地,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产业层级也较高。前者属于农村工业,其生产规模扩大十分有限;而后者属于城市工业,发展颇为迅速,在清代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业。郊区市镇工业所处的地位大致在农村工业与府城工业之间,但更接近府城工业。
首先,从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来看,郊区市镇的主要工业(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草编业)所使用的原料(稻谷、油菜籽、大豆、席草等)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本地农村,而所生产的产品(食米、油、油饼、草席等)也有一部分供给本地居民(包括农村和市镇居民)。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市镇工业似乎与农村工业无多大差别。但是到了清代,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所使用的原料已有很大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来自远地,产品也绝大多数输往府城和更远的地方(116)。即使是依靠本地原料比较严重的草编业(117),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向。虎丘织席业所需的席草早在明代后期就已不能自给,要从吴江等地输入。到了清代,因为生产扩大,席草输入也随之大增,因而康熙时虎丘镇已有席草行专司其事(118)。其所产草席则远销各地,“南津、北津、通安等席市,每日干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浒墅]关者亦必买焉”(119)。因此虎丘的织席业到了清代已经是一种原料和市场都主要在外的工业了。
其次,市镇工业的生产专业化程度也明显高于农村工业。即使是同一行业,市镇上的专业化生产与农村里的农家副业生产,无论是在生产的工艺水平上,还是在生产的效率与产品的质量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这种情况在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等工业中都很清楚。即使在农村工业具有较大优势的草编业中,情况也大致如此。史称清代中期“席萆之肆、席机之匠,惟浒墅有之……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浒墅]关者亦必买焉”(120)。亦即专业化的织席作坊,只是浒墅镇上才有,四方商贾和过往宾旅都在镇上购买这种以样式好、品质佳著称的“浒墅席”。乡下生产的草席如果要以“浒墅席”的名义出售,那么在产品的样式、质量标准等方面就不能不唯镇上草编业的马首是瞻(121)。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了市镇工业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且也表明了农村工业在生产上对市镇工业处于一种从属地位。
因此,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郊区市镇工业仍然属于城市工业,而非农村工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工业的发展状况。
(二)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
关于明清苏州工业的发展,史坛研究已多。兹以我在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为基础(122),从苏州众多的城市工业部门中,挑选棉布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草编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以及珠宝制作业等12个主要行业,对苏州城市工业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的发展情况作一略述。
1、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
棉布生产包括棉纺织业与棉布加工业两大部门,而棉布加工业又主要由踹压与染色两个部门构成。同明清江南其他地方一样,苏州地区的棉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农村,而棉布加工业则集中在城市。但是不同的是,苏州的棉布加工业基本上位于府城内外,而松江的棉布加工业却主要是在专业市镇上。
与松江、太仓等地相比,明清苏州地区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小得多(123),发展速度也慢得多。苏州向外地输出的大量棉布,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江南其他地方收购坯布来进行加工后再输出的。因此苏州的棉布加工业的规模,远大于其棉纺织业的规模。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世纪中,苏州棉布加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到了清代初期,“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124)。江南棉布踹染业的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了苏州。到了雍正、乾隆之际,府城的踹染业集中到了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棉布加工业区。以后由于污染问题引起官司,大部分染坊又被勒令迁至娄门外。
2、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
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大体可分为官营和私营两个部分。嘉靖时官营苏州织染局额设织机173部,各色工匠共计667名,岁造紵丝1,534匹(125)。到了清代初期,苏州织局的额设织机增至800部,雍正时减至710部。乾隆时再减至663部,织造匠役为2,175人,岁造缎匹大约3,500匹。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时代(126)。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官营丝织业的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在此同时,私营丝织业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万历29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127)。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128)。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1,500-3,400部,织工达5,000-10,000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129)。按照同样的比例,织工总数当为36,000人。加上丝织品加工(主要是染色)的从业人员,则直接从事丝织品生产与加工的人员的总数,还要更大得多(有关讨论见后)。
3、成衣业
苏州地区生产和加工出来的棉布与绸缎,大部分以布料的形式输往外地,但也有一部分在府城制为服装,供给本地和外地市场。由于苏州成衣具有广阔的市场,因此成衣业也成为苏州府城的一项重要工业。从有名布号“益美号”的故事来看,清初府城内成衣业一年所使用的布匹就多达百万匹(130)。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是,但此时府城成衣业规模已经很大则是可以肯定的。到了清代中期,府城成衣业继续发展。乾隆45年成立了成衣业行会——成衣公所(131),此后经营特种服装的行会也相继建立(132)。这标志着成衣业已成为苏州城市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4、碾米业
明清苏州府城及郊区市镇居民所食用的稻米,基本上都是在本地碾坊脱粒,因此碾米业也是苏州的一项重要的城市工业。该项工业主要位于枫桥、浒墅、月城、虎丘、甫里等郊区市镇。其中虎丘在清代中期已成为江南著名的碾米业中心(133);甫里也以碾米业发达而著称,其碓坊并成为江南各地的楷模(134)。苏州的碾米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虽无直接记载,但可从稻米消费量与碾米工效来推算。明代后期苏州府城人口达50万人左右,清代中期更达百万以上。苏州居民人均年食米量,据包世臣说,是男女合计“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135)。据此,则明代后期府城人民年食米约150万石,而清代中期300万石以上。仅就此一项而言,自明末至清中叶,碾米业的生产规模就扩大了1倍。郊区市镇居民食米也要依靠碾米业加工。由于郊区市镇居民的人数在此三个世纪中增加了9倍,因此食米数量也要相应增加。此外,酿酒业也消耗颇大数量的稻米。如后所言,在本文所研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地区酿酒业的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扩大,清代中期每年酿酒所用稻米数量与府城居民食米数量不相上下(136)。因此碾米业生产在此三个世纪中的扩大幅度,远比府城人口的增加幅度大。
5、酿酒业
酿酒业也是苏州地区的一项主要工业。这项工业至少自明代中期起,就主要集中在郊区市镇。府城近郊的新郭、横塘、李墅等诸村,在正德时就已是“比户造酿烧糟发客”,横金一带并出现了专业的酿酒工,“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远近皆用之”(137)。到了明末,横金镇成了酿酒业中心,“中人十金之产,亦必为之,大力者用秫数千斛,俟四方行旅之酤”(138)。到了清代,横金的酿酒业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道光时出现了“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麦,负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139)。毗邻横金的木渎镇在清代发展更快,成为江南最大的酿酒业中心。据乾隆初年苏州巡抚张渠在一份奏报中所说,在木渎镇,“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纵非日日举火,然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他市镇糟坊,间有私相效仿,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140)。
6、榨油业
明清苏州的油坊,包括位于农村、季节性开工的“乡作车”相位于城镇、常年性开工的“常作车”两种。后者专业化程度较高,明代主要分布在府城近郊,而清代则集中在郊区市镇。明代中期府城阊门外的上塘可能已出现商业化的专业油坊。但是一直到明末,府城近郊的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油坊榨菜、豆油”(141),才形成了较为集中的榨油业生产地区。到了清代,设有油坊的市镇不仅为数更多,而且有关的记载也更加详细。在清代前期的周庄、陈墓等镇,“每至春间,堆贮菜子,用以压油”(142)。到了乾隆时代,甫里镇的油坊更成为江南各地油坊的表率(143)。
7、纸张加工业
早在正德时,府城内的大众化笺纸生产已颇盛。到了清代中叶,生产更为兴盛。至乾隆中后期,府城内印纸作坊已有30余家,并合建了同业会馆——仙翁会馆(144)。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府城内印纸作坊的规模已颇大,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水平也颇高。例如乾隆时代的30多家纸坊雇佣工800余人,平均每坊20余人;生产的笺纸,有丹素、胭脂、红金、砂绿、山木红等色,工艺颇为复杂,有推、刷、洒、插版、托边、裱、拖、刀剪、杂等十余个工种。这些纸坊中工作的工匠“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他们在苏州纸坊的工作是专业性和常年性的。
8、印刷业
明代后期苏州的印刷业基本上集中在府城内,书坊已知其名者就有37家,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145)。清代府城内的印刷业更加兴旺,因而在康熙十年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146),道光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147)。除了这些书坊外,清代中期还出现了许多印制节庆民俗文化用品的作坊,例如各纸马香烛铺在腊月间,都“预印路头财马”售之(148);著名的玄妙观亦于元旦“设色印版画片……乡人争买芒神春牛”(149)。城厢附郭的印刷业在清代也发展了起来。例如著名的苏州木刻年画的印制,康熙时主要集中在阊门内的桃花坞。但是到了乾隆时,阊门外山塘街成为与阊门内桃花坞齐名的年画印制中心,有画铺多家,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制品远销江、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甚至日本(150)。日历印刷,清代中叶府城附近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151)。
9、草编业
苏州地区的草编业集中于虎丘、浒墅、甫里等市镇。这些市镇早在正德时即以产蒲席著称,“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为廉或坐席。又一种阔经者出甫里”(152)。直至嘉靖时,仍然是虎丘席名列第一,浒墅次之(153)。到了清代,织席中心转移到浒墅,“今种席草织席者,浒关为甚”,“虽虎丘亦以席多,不及也”(154)。甫里自正德以来,草编一直不衰,“概四栅之民,工商佃田外,大都织席。西南二隅暨迤甫迤西尤甚”,而“迤西北多业草蒌”(155),已有进一步的分工。此外,清代的唯亭、黄埭镇亦然,也成为新的草编业中心。唯亭镇“南隅业织蒲篓,西南隅业织芦席”(156)。黄埭镇所产草席,“或染色相间,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阔狭花样,无不如其式而为之”(157)。
10、砖瓦石灰业
明清苏州的砖瓦生产,以陆墓镇与徐庄镇最为著名。明清皇宫正殿所用细料方砖及工部所用官砖,大都在此二地烧造。特别是陆墓镇,所产砖瓦“坚细异他处,工部兴作多于此烧制”。清代发展更为兴旺,“陆墓窑户如鳞,凿土烧砖,终岁不绝”(158)。在清代,陈墓则是著名的石灰生产中心。宜兴的石灰业兴起后,陈墓石灰业受到强烈冲击,曾一度陷于困境,“在镇窑户几至失业”。但到了乾隆中期,“陈墓灰又大行矣”,陈墓镇也恢复了其作为江南石灰主要产地之一的地位(159)。
11、铁器制作业
苏州府城的铁器制作,虽然规模不大,但明代中期就已颇为闻名。正德《姑苏志》卷14中记载苏州有针作,嘉靖时有日本使臣数次来苏州采购针(160)。城厢附郭也是铁锅的重要产地。嘉靖时备倭,苏州城郊冶坊被官府借去铁锅400口(161)。到了清代,苏州的铁业更盛,故“冶坊”成为一重要行业。乾隆六年冶坊工匠闹事,坊商联名上诉者即达14家之多(162)。这些冶坊,有专门“成造田器”者,有专门制作钉者(163)。制作铁锅者更多,“六门附郭共十六房[坊]”(164)。
12、珠宝玉器制作业
早在明代,苏州府城的珠宝玉器制作水平就已领先全国各地,故宋应星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165)。在清代,苏州的珠宝玉器制作也一直以高工艺水平著称,史称“珊瑚玳瑁等物,追琢极精”(166);乾隆帝亦赋诗赞之曰:“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167)。此时的珠宝玉器制作都在府城内,主要集中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玉器制作已形成细致的行业分工,因此出现了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冬作坊生产也各有特色。玉器工匠主要是苏州本地人,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据后人追溯,“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者则三千余人”(168)。对苏州城市工业在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期间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个概述之后,我们接着要问的是: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86)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的专业市场》。
(87)曹树基:《人口史》第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88)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第62页。
(89)沈寓:《治苏》(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吏政守令下)。
(90)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91)参阅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250页。
(92)康熙《(吴郡)甫里志》(抄本)卷首程大复序:“去[县]治西南三十余里,见灯火万家,云树苍茫,市廛 杂,拟于 邑,意即震川集中所称甫里者欤?询之从者,果然”。《公呈汤抚院稿》:“烟火万家”卷1地里:“镇以蕞尔,兼隶长、昆仑[按:仑字衍],其形如上字,计其户则逾万家……甫里民廛占中市暨西栅、南栅得十之七八,六直民廛占东栅,得十之二三。居民万户,近复倍之”。因此可知,上面提到的居民,都是镇上居民。依照最末一条,其数在1-2万户之间。
(93)吴建华使用刘石吉关于明清江南市镇数量的统计和江南各府的面积,出江南各府及江南全地区的市镇密度(吴氏称之为“市镇率”)。其中,苏州府的市镇密度为每100平方公里404个,在江南八府一州中名列第三,仅次于松江府(721个)和太仓州(585个),而大大高于江南全地区(286个)(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刊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可惜的是,吴氏所用的市镇总数似乎是整个明清时期(1368-1911)内曾经出现过的江南市镇的总数,因此从该计算结果无法看到市镇密度的时间变化特点。姑不论此,从这个结果也可见苏州府市镇密度在江南处于高水平。而在苏州府属县中,吴、长、元三县的市镇密度又属于最高者之列。
(94)大体而言,在这三个世纪中,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首先,在人口密度方面,吴江县与吴、长、元三县相近,道光时都为每平方公里1,540人左右。其次,就市镇数量来看,吴江在正德时有市镇7个(镇4,市3);嘉靖时有市镇14个(镇4,市10);康熙时有市镇17(镇7,市10);乾隆及道光时有市镇16个(镇6,市10。吴江、震泽合计)。而吴县在正德时有市镇6个(镇5,市1),崇桢时有市镇7个(镇1,市6),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有市镇8个(镇6,市2);长洲、元和两县的市镇,明代中期(正德)和后期(隆庆)为9个(镇4,市5),清代中期(乾隆至道光)为17个(长洲镇5,市3;元和镇7,市2)。从市的数量来看,吴江比吴、长、元三县中任何一县都多;但是从镇的数量来看,吴江县与吴县相同,略多于长洲县而少于元和县。一般而言,镇的规模比市大,人口也比市多(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第103页)。因此总的来说,吴江县的市镇人口可能多于吴、长、元三县中的任何一县的市镇人口,但不会多出很多。此外,吴江县虽有相当数量的居民生在县城,但其数不大。弘治《吴江县志》卷2说县城及其郊区,“民生富庶,城内外接拣而居者烟火万家”。据此似乎居民数量不少。但是据曹树基估计,明初吴江县城人口仅为1万人左右(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24页)。到清代,据乾隆《吴江县志》的数字,吴江、震泽两县“县市”人口为2,000户(参阅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按一户5人计,也仅有10,000人。因此除去府城人口后的吴、长、元三县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低于吴江,但也仅只是略低而已。
(95)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化》,第414页。明代后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2,000万,其中城镇人口总数约为300万。在城镇人口中,苏、杭、宁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50万。因此三大城市之外的城镇人口约为150万,占其时除去三大城市后江南人口总数(1,700万)的8.8%。
(9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24、325页。
(97)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市镇之数量分析》。
(98)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310页。
(99)江南的人口总数,在1400年前后约为1,400万,1620年前后约2,000万(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396-397页)。
(100)正式居民297万,加上外来人口,总数应在300万以上。
(101)这里所说的外来人口,不仅包括来自较远地区的人口,而且也包括来自附近地区的人口。
(102)康熙五十九年《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86页)。
(103)康熙三十二年《永禁踹匠齐行增价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55页)。
(104)《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凤@④huī奏。
(105)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7页。
(10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107)郑若曾:《苏松浮赋》(收于同氏《郑开阳杂著》)。
(108)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
(109)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184-185页。
(110)《雍正朱批谕旨》卷200,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苏州织造胡风@④huī奏:“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
(111)外地劳工在市镇的情况,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外地商人在市镇的情况,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章。
(112)与此相反,在那种“群芳争艳”型的城市化发展中,各个较大的工商业市镇都力争扩大自己的工商业规模并确立自己在产业层级上的优势,因此大量引进外地劳工是不可避免的。
(113)这一点,在苏州地区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典型的例子如浒墅。该镇是一个草编业中心,但那里出售的草席,却有颇大一部分是农村工业的产品,故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称浒墅“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光福一带山中,妇女隙时皆织席,较之宁波诸处为上。近称浒关细席者即此”。
(114)该理论认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有重大发展;农村中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家庭,大多并未脱离农业生产;农村手工业常常位于城市附近,大多与纺织业有关;生产过程的若干重要部分位于农村。这种“原始工业化”也并非与城市无关。不仅某些农村工业生产的产品仍然需要在城里进行最后加工,而且农村工业生产所需的资金也经常由城市商人提供,产品也总是由城市商人收购并运销外地。参阅Maxine Berg,Pat Hudson与Michael Sonen- scher:《Manufacture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5)例如乾隆时元和县唯亭镇的悬殊、荡上村,“家家切纸阡”,“比户切纸为业”(《元和唯亭志》卷3物产)。
(116)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2章第1、2、6节,第8章第1节。
(117)《桐桥倚棹录》卷11“席”说:“环山居民多种 草,织席为业,四方呼为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
(118)康熙十二年《长洲县严禁诈扰虎丘席草行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01-202页)。
(119)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
(120)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
(121)顺便说一句,正因这个原因,光福农妇织席,“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这里所谓的“式”,就是镇上的标准样式。由于农村草编业在生产上受到市镇草编业的强烈影响,而在销售方面更要依赖市镇,因此可以说成为了市镇工业的附庸,而非相反。
(12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2-6章。
(123)从现有史料来看,只有周庄、陈墓等镇附近的农村的棉纺织业在清代较为发达。
(124)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总督李卫折(收于《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
(125)正德《姑苏志》卷15田赋。
(126)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162、177、187-188页。
(127)《明神宗实录》卷361。
(128)顾炎武:《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副使寇公墓志铭》(收于顾氏《亭林余集》)。
(129)参阅范金民与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5-456页;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00-201页。但是据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所引用的《东西商报苏州市情》,此数为乾隆时的数字。
(130)据道光时人许仲元所述,明末清初徽商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许仲元:《三异笔谈》卷3“布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段文字末说的“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前面已说到衣工有缴益美号机头者给银二分,又说论匹赢利百文。因此要销售布100万匹才能派机头2万两,而增息20万贯则须销布200万匹。可见有一半布是在本地加工为服装的。许氏又说;“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布]为美也”。而益美号在康熙和道光年间的苏州碑刻中曾多次出现,确实是清代著名的布业巨子。因此上述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
(131)《长洲县禁止无业游民在成衣公所寻衅滋扰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25页)。
(132)例如寿衣业的云锦公所、估衣业的云章公所亦分别创建于道光二年与咸丰六年。
(133)顾禄:《桐桥倚棹录》。
(134)乾隆《吴郡甫里志》卷5物产·储用之属:“油坊、碓坊,各处有之,具以甫里为式”。
(13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农二。
(136)据包世臣说,嘉庆时,苏州府每年用于酿酒的稻米就不下数百万石(《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二农二)。而本文所说的苏州地区又是苏州府内最主要的产酒地。仅只木渎一镇酿酒业每年所耗稻米,就达百万石之多;横金亦达数十万石。因此苏州地区酿酒业所消耗的稻米数量至少应在150万石以上,与其时府城居民食米总量相埒。
(137)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
(138)崇祯《横溪录》卷3风俗。
(139)金文榜:《榷酤说》(收于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5户政)。
(140)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
(141)崇祯《吴县志》卷1。
(142)乾隆《元和县志》卷16物产。乾隆《陈墓镇志》卷4物产。
(143)乾隆《吴郡甫里志》卷5物产·储用之属。
(144)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145)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9-372页。
(14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第72-73页。
(147)道光二十五年《吴县禁书坊印手把持行市碑》(收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7页)。
(148)《清嘉录》卷12“年市”。
(149)《吴门岁华纪丽》卷1“城内新年节景”、“春牛图”条。
(150)段本洛、张福圻:《苏州手工业史》,第92页。
(151)《清嘉录》卷12“送历本”。
(152)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
(153)嘉靖《浒墅关志》卷4土产。
(154)《桐桥倚棹录》卷11“席”,道光《浒墅关志》卷11土产。
(155)康熙《(吴郡)甫里志》卷3风俗、物产,乾隆《(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物产。
(156)《元和唯亭志》卷3物产。
(157)民国《黄埭志》卷2物产。
(158)正德《姑苏志》卷32物产;乾隆《长洲县志》卷16物产;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7卷“砖”;顾炎武:《肇域志》第1册苏州府;民国《吴县志》卷51及卷22下引同治府志。
(159)乾隆《陈墓镇志》卷4物产。
(160)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页。
(161)《筹海图编》卷12“严城守”。
(162)《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54-155页。
(163)据徐扬《盛世滋生图》,乾隆时苏州城内有“钉锬”店铺或作坊。参阅李华:《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刊于《文物》1960年第1期)。
(164)《娄关小志》。
(165)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玉第18卷“玉”。
(166)乾隆《苏州府志》卷12物产。
(167)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2页。
(168)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