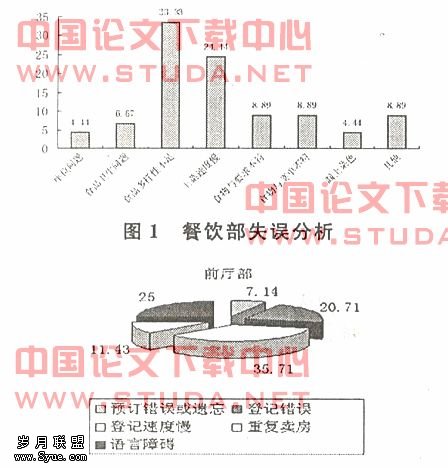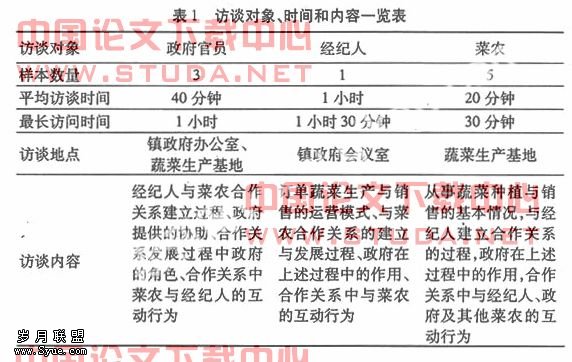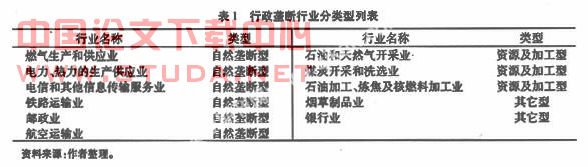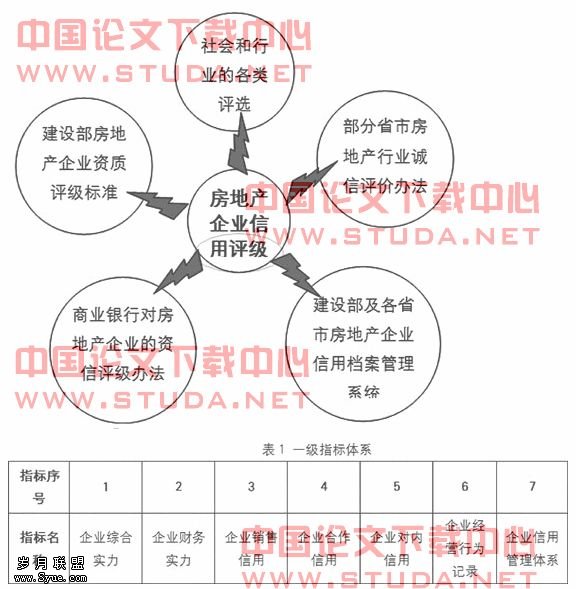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一个比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在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比俄罗斯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在体制转型中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之一,而俄罗斯的经济却陷于严重的衰退。这个事实,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和两个国家的相对国力地位,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问题是,中俄之间以十年为期的GNP 增长的成绩对比,真的就已经为比较这两个国家不同改革模式的长期经济影响提供了可靠的判据吗?具体一点问,中国连年的高速增长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真的就意味着中国被叫作渐进主义的改革方略一定比俄罗斯的激进私有化改革更优吗?或者,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已经解决了俄罗斯改革想要解决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地,中国是否可以保持她的渐进主义改革策略而走向新的成功?最后,俄罗斯是否有必要改变其激进路线转向跟随中国的渐进主义?
毫无疑问,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的学者们对上述问题有着及其不同的见解。本文选取中俄农业改革的案例来进行一番探察。这样做的理由是,第一,农业在中俄两国的改革中分别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而已经可以看到改革的某长期结果;第二,中国的农业改革被公认最为成功,而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差不多最为糟糕,因此如果在农业改革问题上显示中国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农业转型中的一些要害问题,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只谈论中国改革的成功奇迹而对其短处视而不见。本文的中心论点是,虽然渐进主义改革可以带来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但其短处已经并将进一步侵蚀长期经济的基础。在通过转型促进经济增长的比赛中,“先进的”的中国不但没有理由骄傲自大,而且似乎有必要向“落后的”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中学点什么。本文以下部分首先分别概述中俄两国农业改革,然后选取了一个“经济和市场的规模”角度来解释和比较中俄两种改革路线的区别,最后从比较中得出结论。
中国的农业改革
绝大部分早期的改革是在地方和基层发动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变革集体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家庭生产责任制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家庭生产责任制是这样一种制度:集体在名义上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在一个满足国家和社区税负要求的合约下归属农户。家庭生产责任制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农地使用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的经营者。中国自集体化以来第一次全面确立了农民家庭为基础的耕作体系。最初,家庭生产责任制是一种短期的、只有一到三年的制度。1984年后,为了激励农户爱惜地力并对土地投资,家庭生产责任制合同延长为15年,后来,在1994年,又正式延长到30年。这标志着集体的土地产权制度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其中土地的使用权完成了由集体向农户的转变。
产权制度的实际变化,引起激励机制的变化,对生产行为和交易行为都有深刻影响。包产到户使中国农业生产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最初的产出增长除了保证完成国家和社区实物和非实物税负之外,主要用于满足农民家庭自己的消费需要。但是很快地,生产的增加在市场上有了表现,农民开始大量出售农产品。政府单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不得不发展成为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和减少对农产品市场交易的控制。但是,与土地使用权的变革不同,价格和市场改革遭遇到严重的利害冲突。
对于农民而言,农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意味着更完整的产权:他们可以最终决定怎样执行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比如说种什么、种多少、卖多少和怎样卖。农民当然要面对所有市场的风险,但是他们同时也享有市场活动的全部收益。对照于原先强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体制,自由的市场交易对农民意味着一场伟大的解放。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集团要求并欢迎市场改革的原因。早期的市场开放,在村庄、集镇和城市造成了活跃非凡的农产品自由市场。这些小市场支持了农民的家庭生产。通过这些自由交易的“小频道”,农民将上缴有余的产出品卖给了市场;同时,农民也从这些“小频道”里得到家庭生产所必要的技术和投入品。
但是农民的家庭小生产,却没有通道与所谓的农产品的大规模分配(mass production )相连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生产和农民交易,既没有能力从事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和糖类的远程和大规模交易,也没有能力从事主要农业投入品的大规模供给。所有这些“大买卖”连同批发系统和长途运输系统,都控制在国家所有的“商业部门”手里。在改革过程中,国有的商业部门一方面开始具有盈利动机,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以行政手段控制市场的权力。他们一身而二任:又是球员,又是裁判。于是出现了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或一个“官僚的商业部门”,这个特殊的组织控制着所有商业化的“大频道”。
在农产品市场的另一端,特别是在城市的食物市场上,消费者不能按照完全的市价购买农产品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也并不按照市场的原则决定。没有国有的全面改革,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食品市场。不幸的是,中国的城市经济至今被未经彻底改革的国有部门所主导。政府不得不继续在城市补贴食物消费,虽然补贴的品种在改革后有所减少。政府一手应农民的要求而放松了对农业生产者价格的控制,一方面又应城市消费者的要求继续补贴食物,这导致了中央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样,中国试图深化农产品的价格和市场改革就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当政府试图缩减食物补贴开支时,城市居民、特别是国有部门的工人就“有理由”抱怨市场的食物价格水平太高了。这种抱怨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例如在转型期的高通货膨胀的环境里,会成为社会紧张的一个根源。政府只好在农产品价格改革方面叫停,继续在某种程度上维持某些农产品种类的低价统购,直到农民作出“减少生产”的反弹,政府再重新提价或重新高喊改革。事实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宗农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已经经过了数次“开放-重新控制-再放开”的周期。1993年以后,国家又垄断了区际粮食贸易、全部棉花收购和化肥农药供给。行政指令的力量在这几个领域里比以前大大加强。
在如此的“改革循环”中,最困难的事情是吸引投资在农民家庭小生产和城市大食品市场之间修建一些新的商业通道。尽管在这个领域里投资的潜在获利可能性极高,但对于投资者而言,关键的限制性因素是缺乏稳定的回报预期。相比较而言,小额投资和小组织在一个政策摇摆的环境中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但大投资和大组织却不能不要求更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我们看到,跟随着地方自由集市和小商业组织在中国的恢复和活跃而来的,并不是资本积聚和规模扩展,而是商业组织结构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一种不配合:“眼对眼、手对手”的小额农产品交易在任何地方都发展的过熟,但是既缺乏有效的“大家伙”,也缺乏远程的、大规模的和高级的农产品交易方式。后者的短缺,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大尺寸”市场的经济更为致命,因为它无法有效地节约通常会比小市场更为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有“盈利的官僚部门”在政策摇摆中感觉良好。他们永远不会输。当政府无论是因为通货膨胀还是因为财政补贴过多而试图控制农产品价格时,国有的商业部门是其唯一的“政策工具”。当然,各种“控制的收益”——从采用紧急手段管制市场的“权威”到享有财政为管制市场的支付——至少其中的大部分都归这个部门所有。在另一种情况下,当政府无论为了深化改革或为了减少城市食物补贴而开放市场时,“官僚的商业部门”的盈利又最为可观:他们可以凭借控制的“大频道”和雄厚的资本在一个扩张的市场里大发其财,而市场风险,比如说对供求形势的错误估计、过多的库存和不当的进出口决定等等,即使发生也可以向财政和消费者两头转移。谁也无法分清,这个部门的“利润”中哪一部分是基于其从事市场活动的能力,哪一部分是基于垄断性的、“代表全社会的”权力。“盈利的官僚部门”不言而喻地拥护半管制、半开放的市场,因为正是这种特别的市场向这个部门提供着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提供不了的特别利益。在一个完全管制的经济中,“管制”没有市价,因为没人为买通管制者而付费;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里,“管制”无价因为没有容其生存的制度空间。
有效的土地产权变革对农民生产行为全面的、持续的激励,离不开一场必要的商业革命。这是因为,离开了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本身并不能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界定产权是为了市场交易,同时也只有在市场交易中,产权才能够真正得到清楚和明确的界定。产权束中的使用权,其经济意义是使用资源获得产出。如果使用者对其产品的交易没有决定权,他的使用权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在农业改革这个例子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讲到底是离不开充分的产品的交易权的。离开产品的交易权,土地的使用权就只有在自给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比如改革的早期,我国农业高速增长的基础其实只是农民家庭(在上缴之余)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超过了这个限度,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就要靠产品的市场交易权来保障。但是,在农村小集市的发展达到这种交易形式的顶点之后,农产品的交易品种和交易形式的进一步开放就成为必要了。偏偏在这个关节点上,中国农业改革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没有实质的突破。包产到户虽然普及了,但是土地产权的“残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试想占绝大部分播种面积的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市场还没有放开,交易权还由行政权力控制,强调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长期不变,到底还有多大的意义?意义是有的,只是限于农户自给性生产和由集市贸易自由调节的狭小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还是“部分残缺”,虽然形式已经与前大不相同。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增产的减缓和90年代初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有一部分可以在市场改革滞后、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的市场化进展迟缓中得到解释。市场改革迟缓的要害问题是,“盈利的官僚部门”在渐进的、两轨长期并存的改革途中“硬化”成为我想称为的“反市场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社会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在不损害反市场既得利益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平滑道路。渐进路线似乎生出了渐而不进的实际效果。
俄罗斯的农业改革
俄罗斯的农业改革从前苏联时期就开始了。对于从产权的角度研究改革的学者来讲,俄罗斯农业改革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全面学习农业改革的经验,试图从农民家庭的土地使用权入手重建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二)为土地产权改革提供了远比中国完备的构架。关于第一点,戈尔巴乔夫时代就通过了以中国农业改革经验为蓝本的改革决定,其主要内容就是允许农民家庭租赁前苏联的国有和集体农场的土地。关于第二点,1990年代以后,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土地产权的法律框架,承认并规范土地的私人占有、出售、购买、股份、租赁和抵押等行为。到1995年,俄罗斯国家和集体农场的土地已经通过法律的途径分配给俄罗斯农民家庭和农场工人。
但是,俄罗斯的农业改革,始终没有取得过中国式的早期成功。
首先,家庭化的个体农场缓慢。首先是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租赁政策,当时只得到不足总农户的2%农户的响应。即使到1994年,在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法律通过之后,个体农场也只拥有6%的农户和5%的农用土地。这同中国在1980-84年几年时间之内,99%的生产队都在当时一个短期的允许土地承包经营的政策框架下变成家庭为基础的承包农户,构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家庭为基础的农场个体化进展不顺利,俄罗斯才转向推进国家和集体农场的股份制,即由农场工人成为国家和集体土地的股份持有人,并因此将国有和集体农庄所有的土地,改造成为股份制农场。1995年俄罗斯国有农场所有的土地从1991年的58.2%降为16.5%,集体农场从40%降为17.2%,股份制农场从0.3%上升为53.9%,个体私有部分(包括私人农场、私人的联合农场和家庭自留)从1.8%上升为12.5%。换言之,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俄罗斯土地真正由农民家庭经营,而绝大部分土地(87.5%)由国家、集体和股份制农场进行式的经营。
其次,更为严重也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俄罗斯土地产权的改革不但没有能够扭转其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而且农业总产出在激进的地权结构改造之后大幅度下降。例如,1994年俄罗斯农业总产出只相当于1990年的75%,其中畜牧业减少29%,种植业下降16.8%。同中国农业总产出在改革早期年代里每年平均递增10%相比,俄罗斯农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
通常的解释是,俄罗斯农产品需求的剧减导致了农业产出水平的下降。农产品需求减少的原因是,俄国丢失了原先受保护的经互会农产品市场,国内需求因为居民收入减少和国家的食物补贴取消也大大减少,部门间和国家间贸易条件的改变,等等。但是世界银行1996年关于转型经济的发展报告却指出,俄罗斯农业的衰退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原先农场的规模过大,平均每个农场达到6000公顷,而在1987年的美国,也只有3%的农场超过840公顷。这些超大规模的农场无法得到有效管理,过去之所以生存下来,是因为可以轻易地得到国家银行的贷款和国家给予的大量补贴(包括消费者补贴)。大农场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恰当,因为农场企业股票的二级市场即使在美国也闻所未闻,其演变和重组没有现成的机制可循。总之,“将国家和集体农场农场公司化后形成的农场结构,在市场经济中找不到对应物”。世行报告主张在农业中执行“更加个人化的土地权政策”,例如中国农业土地的明确或不明确的家庭长期租赁。
但是,俄罗斯不正是在推行农地家庭租赁制得不到预期的响应之后,才转向农场的股份制改造政策的吗?目前俄罗斯土地股份制产权安排其实是量化到个人的,如果在其现实的环境里,“更加个人化”的经营模式确实可行,农场工人——股东们——为什么不实行农业的小规模经营,而非要保留超大的农场规模并委托给农场经理去管理呢?因此,实质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在中国农业改革中更加个人化的家庭承包经营策略,在俄罗斯那样难于见到成效?
在有机会实地考察前苏联式的农场并与研究苏东农业改革的学者交换意见之后,我认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中俄之间的经济规模、特别是市场规模和结构存在着重要区别。俄罗斯不但平均的农场规模大,而且由于地广人稀,农场与农场之间距离很远,地区没有密布的居民点、集镇和城市,因此俄罗斯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无法依托“一放就活”的农村小集市来作为其投入和产出服务的“支持系统(suporting system)”,而必须要依靠“大量分配(mass distribution )”。就是说,小交换不灵,大交换才能普遍解决问题。俄罗斯农业投入和产出服务的系统,在原来体制下由国家垄断。这一点与中国是相同的。但是区别在于,中国早期的农业改革可以通过快速放活的农村集市小自由贸易支持农民家庭小生产,而俄罗斯没有这个条件。因此,俄罗斯农民对土地的家庭租赁制反应不积极,可能并不是象一些人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七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苏联农民不会种地”,而是由于农民在得不到有效的投入产出服务的预期下对产权和经营组织形式的一种合理选择。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同样七十年的集体化,为什么地处欧洲、靠近大城市的俄罗斯农民选择家庭经营的比重高,生产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呢?多数俄罗斯农民,还是不得不依靠原先国家或集体农场在支持系统方面的一点规模经济,然后在农场之内把精力投放到家庭自留经济里。1994年,国家、集体和股份制农场占用88%的土地生产了60%的产出,私人农场用5%的土地生产了2%的农业总产出,而家庭自留地只占用2.8%的土地就提供了38%的总产出。这说明,虽然产权的法律框架已经不再构成俄罗斯农民选择私有化农场模式的制度障碍,但缺乏有效的生产“支持系统”,还是会迫使农民在现实的生产贸易条件的局限下作出抉择。产权改革不是可以孤立进行的。
但是,这同时也迫使俄罗斯农业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下决心根本改造原来国家垄断的大量分配体系。俄罗斯农业改革没有尝到中国农业改革早期效果的甜头,但是她把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农业改革在中期以后才遇到、而至今没有解决的要害问题——按照市场化原则全面改组农业和城市食物市场之间的技术和其他投入品的大分配通道。Wegren(1996)最近调查了俄罗斯从农场到消费者餐桌整个食物供应系统的状况。他看到,(1)俄罗斯的食品贸易政策是开放市场的充分竞争;(2)国家从食物分配过程中大步退出,例如1992年经过“国家频道”经营的粮食占64%,但到1995年只有3%;(3)即使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的食物系统目前也以很少的政府管制和保护为特征。由于连接部位的机制改变,农业供给开始适应市场购买力的变化,所以虽然俄罗斯农业的总产出在总的需求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降低,但综合要素生产率却有了提高。这些证据当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可靠地估计俄罗斯农业的未来走向,但是至少,俄罗斯在国有商业通道里大刀阔斧的改革,没有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的形成、扩张和硬化提供土壤。
市场半径、产权和新商业组织
中俄农业改革的经验一致表明,一场在工商业部门里进行的根本改革对于农业重组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在一个大半径的市场里,除了被叫作“自由企业制度”的体系,即在竞争中追求利润的商业组织,没有任何其他有效的方式可以把农场和大城市农产品市场连接起来。缺乏这样的体系,无论是中国农民的家庭小生产,还是俄罗斯的大农场,都不能有效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都不能有效地从外部获得性的投入品和服务,都不能有效地形成一个现代的食物供应系统。按照Coase 的术语,就是单靠农业本身的改革决不足以节约一个巨大的市场所必然带来的昂贵的交易费用。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农业改革成功主要来自前期的经验。不同凡响的农业生产增长的真正基础,是农民为自己温饱和在小自由集市支持下的家庭生产。这种增长模式以土地使用权的改革为前提,其优点是改革易于发动和推广。但产权方面局部的和渐进改革的脚步,到了土地产出品自由交易权面前就迟缓了下来。市场和行政控制长期双轨并存,占用大部分农业资源的农产大品种的市场化改革进退反复,没有实质进展,特别是形成了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堵塞了把家庭小农业与大市场连接起来的通道。在此约束之下,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并重组农业产出结构,面临重重障碍。可以估计,包括国有商业部门在内的中国国有经济的改革滞后,已经并将继续拖住中国农业重组的步伐。总的画面是,与一个家庭为基础的、以集市为主要交易形式的活跃的市场相并存的,是一个大规模的、国有的或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控制的官商部门。如果说前者没有能力有效地节约大半径市场的交易费用,那么后者不但不可能提供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反而是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更困难的是,上述两元格局好象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均衡,因为改革再也做不到可以不触犯一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就增加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趋易避难的改革策略,看来收到先甜后苦之效。容易的改革没有了,只剩下两件事可以选择:要么冒风险战略攻坚,要么喊口号就地打转。
在俄罗斯,农业改革求易未果,继而碰难。所谓求易,就是仿照中国农业改革的路线,从释放农民家庭经营的潜能出发。但是,在中国生效的事情到了俄国就不生效。公道一点讲,从前苏联到现在俄罗斯的农业政策当局,推行农业家庭经营可是不遗余力。读读他们关于土地制度的政策文件和法令就可以知道,其书面的完备性远在中国达到的水平之上。但是,俄罗斯农民似乎就是不欢迎这一套。这件事情,在本文作者看来,同集体化搞了多长时间没有关系,却同资源结构、市场半径和城镇布局的密度等等有关。从一开始,俄罗斯农业离开了有效的“支持系统”就寸步难行。家庭农业玩不转,后来搞股份制大农场其实还是玩不转。改革不能快速生效,因为没有类似中国“小市场支持小生产”的早期改革效应。食品形势进一步恶化,逼得政策当局选择推进国有部门改革的激进策略。情况反正已经糟糕透了,不会因为激进改革而变得更加糟糕。激进策略也许有百害,但至少有一利,就是国有部门的改革不会在渐进中“夹生”、特别是不容易夹生出一个“盈利的官僚部门”来。这样,俄罗斯改革就大刀阔斧直指要害。
毫无疑问,中国与俄罗斯在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社会和传统等许多方面迥然相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发现两个国家在转型中有一个相似的关键。这就是原来体制下行政等级制的大分配系统如何被自由企业制度所取代。这是有效整合大市场的关键,因而也是农业改革持续深入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开始得早些,但似乎至今还没有投入真正的战斗;俄罗斯晚些,但已经跨进了急流。虽然还需要追踪观察,俄罗斯的激进改革策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全面改善其农业的“支持系统”,以及当“支持系统”进一步改善以后,俄罗斯农业生产效率是否可以持续提高,但我们已经可以结论:俄罗斯农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农业改革的早期成功经验所不能回答的。倒是中国农业改革在早期成功之后的某种停顿,表明中国有必要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有部门方面,在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必要的营养。众所周知,“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准则。80年代以来中国摸到了一块大石头,这就是在渐进主义双轨并存下日益坐大的反市场既得利益。石头摸到了,我们可以过河了吗?
上一篇: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农业的发展
下一篇: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