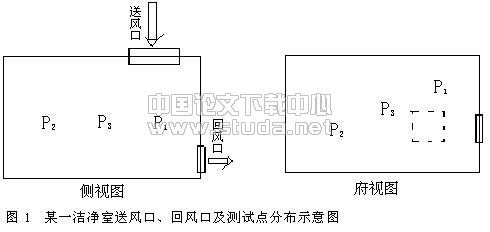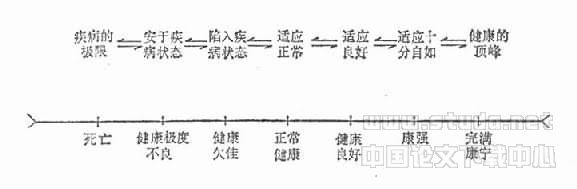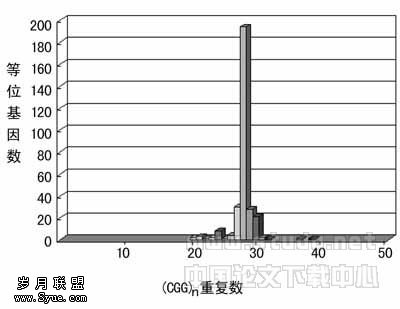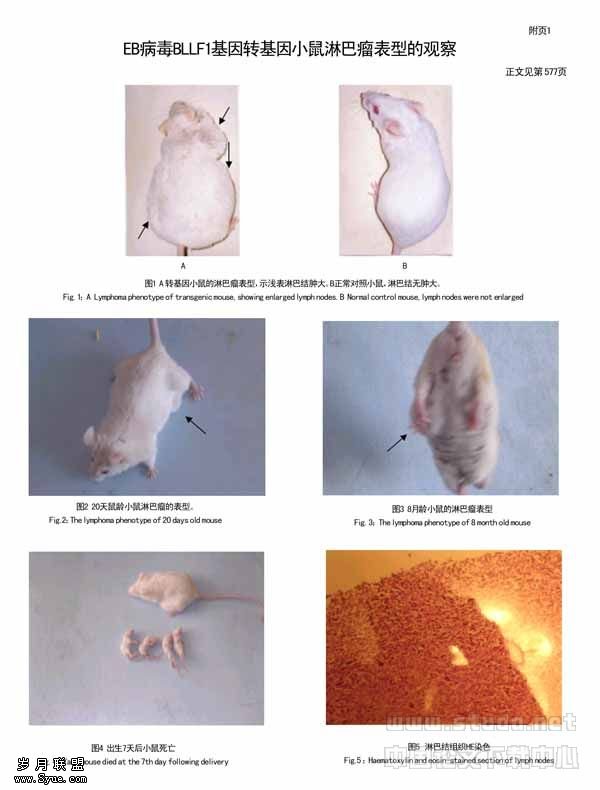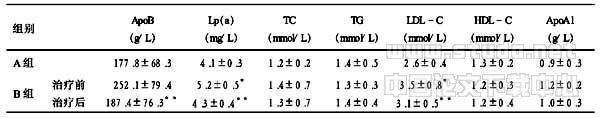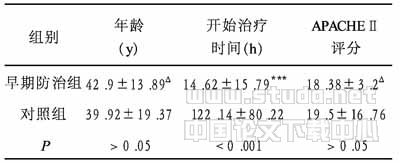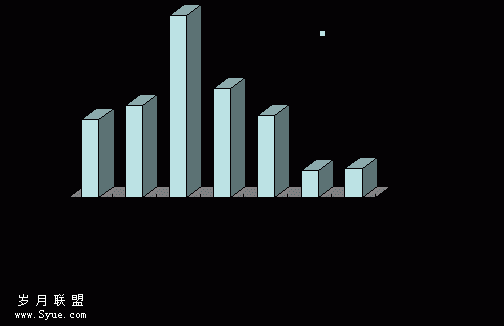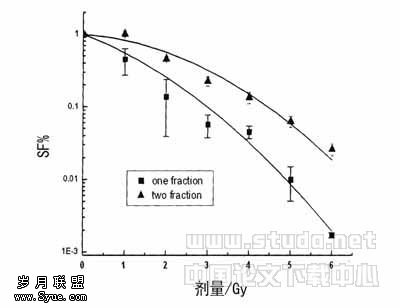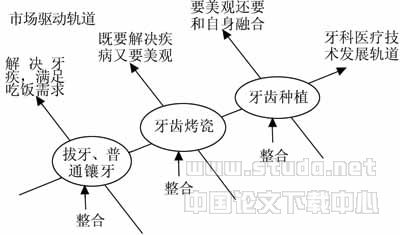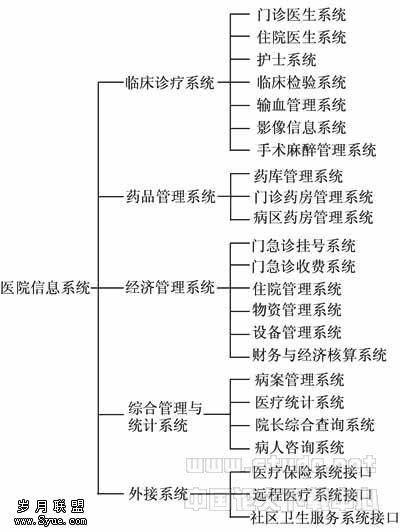论绍派伤寒的学术创新与薪传
【摘要】 《伤寒论》代表了前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温病学代表了后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在伤寒与温病的论争中,绍派伤寒又代表了对外感病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时期。绍派伤寒的寒温一统说可谓异帜独张,它与温病学派的主张存在多方面的不同,并在不断的学术争鸣中得到完善。
【关键词】 绍派伤寒;寒温一统说;伤寒学说;温病学说;通俗伤寒论
Abstract:“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 represent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xopathy disease of the times before;Epidemic Disease represents the theory of later period.In the dispute between febrile disease and epidemic disease,the “Febrile Disease” of Shao school again represents a period of further recognition to the exopathy disease.The unification of febrile and pestilence of Shao school may be unique,which has many differences from propositions of pestilence school,and being continually perfected in successive academic contention. Key words:febrile disease of Shao school;unification of febrile and pestilence;Treatise of Febrile Disease;Pestilence Doctrine;Common Febrile Disease 绍派伤寒,始于明代,盛于清、民国时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医学流派之一。这一学派阐扬补充了张机六经辨证体系,又吸收了叶、薛、吴、王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体系,独张异帜于浙江绍兴,其原因及其复杂。学术上的医圣六经辨证地位、温热类传染病的多次流行、吴又可《温疫论》的出版、叶薛吴王温病四大家的相继崛起、经方与时方的争论、伤寒与温病的争鸣、对四时外感病临证经验的不断结累、及绍派医家的勤践苦学与思考探索等等,这些均为绍派伤寒的形成、与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场景。可以说,《伤寒论》代表了前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温病学代表了后一时期的外感病总论,在伤寒与温病的论争中,绍派伤寒又代表了对外感病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时期。 1 伤寒论时期 伤寒概温病 《内经》、《伤寒论》有温病之名,晋宋以降,代有补充发挥,但终不越《伤寒论》樊篱。观念上宗“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论;上则以六经证治体系为实施准绳,温病附于伤寒之中。晋·王叔和《脉经》例五种伤寒,除伤寒、重暍外,其中就有热病、风温、湿温。《难经》也言伤寒有五,归温病、热病、湿温于伤寒麾下。晋·陈延之稍有发挥,别天行、温疫于伤寒,《小品方·热病门》指出:“古今相传……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惜不为时人所重。以后《巢氏病源》于温病又间有发挥,在《时气令不相染易候》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多相染易”。明确指出“乖戾之气”这一外界有害物质为传染病发病及流行的原因,但囿于议论简略,缺乏论证。《千金》仍以温病附伤寒,《外台》叙天行温疫证候,也几与伤寒同,直至北宋官修《太平圣惠方》时,干脆不为温病另立门户,而散于热病诸门。这种情况,诚如《世补斋医书》所说:“《伤寒论》是五种伤寒之总论”。
温病没有大的发展,然温病的发生及流行却有增无减。据笔者统计,北宋疫病流行13次,明公元1408~1643年间,大疫流行19次,清267年中,疫病流行竟达64次。正由于此,六经证治体系,面临着温病的挑战。六朝时《深师方》指出:“伤寒已八九日,三焦生热,其脉滑数,昏愦身热,沉重拘急,或时呻吟,欲攻内,则沉重拘急,由表未解;直用汗药,则毒因加剧”;呈现对热病表里同病治疗上的困惑。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也对温病治用伤寒法颇多感概:“四种温病(即王叔和归入伤寒的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炯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律)作伤寒行汗下”,“四种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六经证治体系难以解释温病,难以指导临证。以后的韩祗和、朱肱、刘完素等人虽着意探索温病,然与现实仍有相当大的距离。明初王履《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曾评说:仲景所叙伤寒三阴寒证,祗和“求对于春夏温、暑之病”,须“知温暑本无寒证矣”。“朱奉仪(名肱)作《活人书》,累数万言,于仲景《伤寒论》多有发明”,但惜其“每每以伤寒温暑混杂议论,竟无所别……自奉仪此说行,而天下后世蒙害者不无矣”。“至于刘守真出,亦以温暑作伤寒立论……也不无桂枝、麻黄难用之惑也……故其《原病式》有曰‘夏热用麻黄、桂枝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斑出矣。”王氏最后感慨道:近代先觉,竟“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王氏虽创伤寒温病异治之说,但却有伤寒温病混称之嫌,他以伤于寒即病与不即病二种情况分伤寒与温暑其类,又据“由其原(病因)不殊,故一以伤寒而为称”统温病,事实上也不清楚温病的病因也别于伤寒,因此直至明末,温病的治疗尚无多少的改善。明末吴又可《温疫论·序》说:“崇祯辛已,疫气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不死于病,乃死于医”的现实,孕育着温病学的新发展。
2 温病学时期 温病成学说
明末·吴又可著《温疫论》,率先发明“戾气”为温(疫)病的病因,推出“戾气学说”。后通过周扬俊、刘奎、舒诏等人的研究,刷新了人们对温病的认识。温病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在吴又可及王履以前,温病伤寒已开始分道。北宋庞安时首开温病门户,将温病分为二类,一是由伤寒复感异气而变成的温病,二是具有传染性自受乖气而成的天行温病,如青筋牵、赤脉攒、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等。继庞氏《伤寒总病论》后,朱肱《活人书》也提出了“温、热”不同于伤寒的论证。温热之别,是由二者风热之多少为义。温病还有新感、伏气之异。南宋以后,温病学又增加了新内容。郭壅《伤寒补亡论》提出新感温病之说:“春时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头疼身痛,既非伤寒,又非疫气,故称春温或春感。”还一再辨明冬感与春感之异,云春感“不传经”、“皆以温气治之”等。宋金时北方,因传染病流行,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等人虽都未放弃伤寒名号,但其论病之因,已有主寒、主热、主虚、主实之异,尤其是刘河间主火说,主用寒凉药,以治所谓“伤寒”,实际上已启温病治疗之端。明·王履推崇刘完素表里双解的方子,倡温病邪气“自内而外说”,而更重视温病攻里法:“治温热病,虽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温病……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把温病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
自从王履提出温病伤寒不论在病候上或治疗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后,人们逐渐改变了伤寒的概念,《温疫论·序》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即如伤寒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喻昌,亦在《尚论春三月温证·自序》中说:“况于触冒寒邪之病少,感发温气之病多,寒邪伤人十之三,温病伤人十之七”。伤寒的范围日趋缩小。另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是,伤寒学派内部此时还在就《伤寒论》原文是否错简、脱简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鸣,因而此时有关伤寒的著述虽多于前朝,但多不出方有执、喻昌、徐大椿、柯琴之途。与伤寒情况相反,温病学却在与伤寒学派的论争中迅速发展。通过寒温之辨,罗各种传染病于温病之中,有关温病的各种研究著作日益增多。18世纪30年代温病学又进入了新境界。叶桂著《温热论》,发明了温邪为病的发生发展,建立了“卫气营血”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及温病的特殊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叶桂之学风行50年以后,又有淮阴人吴瑭根据叶氏之学和自己经验,于公元1799年著成《温病条辨》,把温病学的研究推向高潮。他以上中下三焦为纲分别系统叙述了温病初、中、末期的症候、诊断及治疗,又根据各种温病的传变特点,将其依次分布于三焦之中,如风温系上焦,湿温布中焦等。吴氏的三焦证治体系和叶桂卫生营血证治体系相互羽翼,支起了温病学的大厦。除此以外,温病学尚有许多发明,如薛雪著《湿热病篇》,阐明“湿热病”的证治规律等,使温病学内容更趋丰富。
3 绍派伤寒出 寒温宜一统
自吴又可、叶桂、吴瑭等人把温病学推至全盛以后,清嘉道以降,温病学创新已不复往昔之盛。此时虽著述如林,但大多承袭陈言,间有发挥,如雷丰《时病论》、王士雄《温热经纬》等;或叙述一、二新病,如王士雄《霍乱论》;有些目为温病总论一类的书籍,实已偏重于一类或一种温病,如柳宝诒《温热逢源》等。然而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温病学已相当完备。实际上,至清朝,许多传染病如鼠疫、真性霍乱、猩红热、白喉等相继在我国流行,这些温病都异常地凶恶,诚如扬栗山《伤寒温病条辨》言:“且夫世之凶恶大病,死生在反掌间者,尽属温病。”对这些病,若仅用卫气营血、三焦之说以包容之,其势必有所不能。这种情况,遂又导致了医家对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证治体系的重新审视,其中还不乏伤寒与温病的论争。如柯琴宗陶华,既提出六经也有温病之说,又斥叶、吴诸人弃六经专三焦。即如在治疗上趋奉叶氏的柳宝诒,也以吴瑭言三焦而弃六经为一失。至于在治疗上的经方、时方之争则更为激烈。根据这些争论。及对新病防治的研究,乾隆41年(公元1777年),绍兴俞根初作《通俗伤寒论》三卷,试图将伤寒温病的辨证论治体系予以统一。他说:“以六经矜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经”,融三焦于六经的这一学术思想,为以后的绍兴籍医家任沨波、章虚谷、邵兰荪、陶晓兰、傅再扬,尤其是何秀山、何炳元、曹炳章等人的研究发扬而亨誉医林,名之曰:绍派伤寒。考寒温一统的思想,见于《素问·热论》及《小品方》,即热病皆伤寒之类,与伤寒、天行、温疫只是名谓上的雅俗不同,而“不说病之异同”。然而这二次主张,由于受时代局限,不但不可能提出寒温统一的具体方案,而且还只是在对温病不甚了解的前提下产生的模糊认识。以俞氏为代表的绍派伤寒则不同,浅识以为是六经与三焦之争的,以六经为主体的调和折衷,但深析后,就会发现其既不同于张机伤寒六经,也不同于叶派温病三焦的学术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1)六经非专为伤寒而设,乃百病之六经,包容了伤寒温病在内的所有外感病,即“六经钤百病”、“三焦赅疫证”。(2)拓展了六经的形层与机理,如言太阳主皮毛、主胸中;阳明主肌肉、主脘中等;密切了六经病理与脏腑病说的联系,又如言“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六经病理机转,实发仲景所未发。(3)补充和更新了六经分证,如太阳病分“本证”、“标证”、“中风证”、“兼肺经证”等;少阳兼证有“兼肺经证”、“兼胃经证”、“兼心经证”等。同时还把“大头瘟”、“春温”、“暑温”、“秋燥”等外感温病,皆类于伤寒之中,呼之为大头伤寒,春温伤寒、暑温伤寒、秋燥伤寒等。(4)发展了察目、切腹、验六经主脉、主舌(苔)及兼脉、杂舌(苔)等诊断外感热病的方法。(5)施治务求实效,不拘经方、时方,立法用药多重芳淡宣化。由此观之,伤寒温病也成一统。[1]
4 针叶派之弊 张绍派之帜
绍派伤寒的寒温一统说可谓异帜独张,它与温病学派的主张存在多方面的不同,是在不断的学术争鸣中成长完善的。
4.1 寒温之争 叶派(指叶、薛、吴、王温病学派)认为,伤寒是受寒邪引起;温病是受温邪引起,这是病因上的不同。寒邪伤人足经,循六经传变;温邪伤人手经,循卫气营血传变。这是病理上的不同,伤寒法在救阳;温病法在救阴,这是上的不同。伤寒当从六经分证;温病当从卫气营血、三焦分证。这是辨证上的不同。伤寒初起脉浮紧或浮缓;温病初起不缓不紧而动数,这是脉象上的不同。此外,在症状表现、具体用药等方面,还有许多原则性的区别。总之,叶派认为:伤寒与温病,在脉、因、证、治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且这些不同,不是大同中的小异,而是有着根本性区别。
但绍派医家认为,外感热病,因于伏气者多,由于新感者少,伏气温病,病因可以是寒邪,也可以是温邪,但不论寒邪温邪,既然伏久而发,则都属于伏火。而伏气温病之发,亦可复因新感引动,新感之邪,可以是寒邪,也可以是温邪。而新感也可以不兼伏气而为病,伏气也可不兼新感而自发。故外感热病,既有外寒内热者,又有内外皆热者,亦有外寒而无内热者及外热而无伏气者。凡此等等,足见外感病因,错综复杂。如认为伤寒后一定发为寒病,或温病一定不是伤寒引发,这也不符合临床实际。而手足经络互相联系,寒邪伤足也伤手,而且犯肺者也不一定都是温邪。对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绍派也有异议,何廉臣说:“叶案云温邪吸自口鼻,此亦未确,仲景明云六气之发,李明之、王安道俱言冬伤于寒,伏邪自口内而发,奈何吴又可《温疫论》混牵耶!”病发之后,应该救阴,还是应该护阳,要辨证为主,不可先将寒字或温字横亘胸中。总之,绍派认为:伤寒与温病只有小异,并无大异。广义的伤寒与广义的温病,往往是同一个对象。同一个对象并不会因给予它不同的称呼,便会在脉、因、证、治上即表现出大异。故绍派主张寒温统一。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中干脆对四时外感热病,称为风温伤寒、春温伤寒、湿温伤寒、热证伤寒、伏暑伤寒、秋燥伤寒、冬温伤寒等等。这样,既是温,又是寒,从命名上就标明了寒温一统之主张。
4.2 六经存废之争 对仲景的六经辨证之法,绍派与叶派,认识亦有区别,叶派认为《伤寒论》六经分证的理论体系,只适宜于辨伤寒,不适宜于辨温病,叶氏言“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且在六经分证之外另辟卫气营血辨证之蹊径。叶派还认为:外感之中,温病多,伤寒少,救温病当从四层三焦为辨,若拘守伤寒之法,疗六气之疴,是御风以絺,指鹿为马。吴瑭也云:“若真知确见其为伤寒,无论何时,自当仍宗仲景,若真知六气中何气,非伤寒者,则于本论(按:指《温病条辨》)中求之”,总之,按叶派所云,六经辨证之法,只适宜于辨狭义伤寒。又说南方无真伤寒。这样,叶派温病其废六经之主张,实不言而喻。
经长期的临床观察,绍派医家认为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不能全面适用于外感热病,因此,对叶派之不讲六经,深表不满。绍派认为:百病不出六经之外,何妨外感热病之类!俞根初认为:伤寒为外感百病之总名,六经为百病辨证之总纲。何秀山也说:“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何廉臣秉笔直言,针对叶派废六经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温热病只究三焦,不讲六经,故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范围,岂以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何氏将六经、四层、三焦作了仔细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认为:“细参吴(鞠通)氏《条辨》峙立三焦,不及俞(根初)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无一遗憾。”但绍派认为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是可以统一的,而并不是分道扬镳,各自对立的。所以,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何秀山说:“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廉臣则认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所以,绍派认为应将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与六经辨证有机统一。
4.3 经方时方之辨 至清,医家对仲景之学,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后世之治外感热病,不能出仲景之范畴,善用伤寒方,即经方,后形成“经方派”。经方立法严谨,结构简洁,尽可宗法,而后世处方用药杂乱,不堪择用。二是认为仲景书专论伤寒,只有伤寒才可宗法仲景,如果温病也用仲景法,麻桂误投,害不可言。又南方无真伤寒,尽是温热,所以治外感病必须跳出《伤寒论》圈子之外,另辟辨证用药之蹊径,自创新方,也称“时方”,后形成“时方派”。如《温病条辨·朱序》说:“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遍及于六淫也。奈后之医者,以治伤寒之法,应无穷之变,势必至如凿枘之不相入。”同书汪叙也说“仲景之书,专论伤寒,此六气中一气耳……其余五气,概未之及,是以后世无传耳。”上述二种意见,后演变成经方时方之争。持第三种观点的即是绍派医家。绍派主张崇实黜华,讲究实用,认为经方派推崇经方,时方派推崇时方,造成经方派与时方派的争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何廉臣说:“方求其验,岂判古今,药贵乎灵,何分中外。”换言之,只要辨证正确药到病除就行,无谓争论不必。绍派厚古不薄今,既认真继承仲景之学,亦重视吸收叶桂等后世医家的长处,并能因时因地制宜,融古今医家经验于一炉,然后,加以化裁创新。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绍派医家吸收叶派的用药经验,又反对其狭义伤寒之论。《通俗伤寒论》开宗明义说:“伤寒,外感百病之总名也”这与维护旧论崇经守旧的流派有不同,也与仲景学说分庭抗礼,而刻意罗织的流派,有明显的区别。[2]
俞氏《通俗伤寒论》首刊于公元1777年,与叶桂生活年代公元1667~1746年,约晚30余年,二种学说几成平行,绍派伤寒以《通俗伤寒论》的整、校、补为主线发展,叶派则后有薛生白、吴瑭、王孟英的崛起。其间又与维护仲景旧论者一起,不断争鸣,不断发展,使绍派伤寒的理论学说,制方用药不断完善,更加贴近绍兴及至浙江的外感病的临床实际。
5 著作登月刊,新方上教材
《通俗伤寒论》成书以后,先后有何秀山、何廉臣祖孙为之选加按语与校勘。初稿在《绍兴医学月报》上发表,随编随印,然刊行未及三分之二,因何廉臣先生逝世而停刊,时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党建三年(公元1932年)上海六也堂书局有鉴《绍兴医药月报》曾为该书出过大增刊,“版出而书即售罄,风行遐尔”(曹序),于是协议继续编印,再次出书,遗稿由何廉臣之子何幼廉,门人曹炳章共同编校,由曹氏执笔补苴续成,“以应读者渴望”(曹序)。然因时间仓促书中前后章节有所重复,学说有不相衔接,还有若干文字讹误,曹炳章欲再加整理,“奈衰年事冗,因循不果”。此时有徐荣斋老对《通俗语伤寒论》研究有加,在曹氏指导下同意其“去芫存菁”。徐氏《重订通俗语伤寒论》本对原著“点缀者删削之,繁杂者合并之,罅漏者补正之,每节之后并加按语以发明之”。[3]
仲景地处北方,著《伤寒论》而用药多为香燥。后世把《伤寒论》方奉为经方,不敢修制后为我所用,终使药不对症。留下诟病。而绍派伤寒则汇通了寒温二大派的学理,虽反对叶派的卫气营血之论,但吸收了叶派的用药特色,结合地域特点,治病经方、时方并重。用药芳香淡渗为主。并认为“治病当以药医,而药靠胃气之力,输布全身,直达病所,协调阴阳”。主张“用药不宜过量,否则易伤胃气;用药贵在清淡,否则易伤胃气”。而胃气的存亡,决定了疾病的转归与预后。
所创制的新方102方(实际74方),有“方方有法,法法不同,真可谓门门透彻,息息通灵”之誉。其中的不少方剂被收载于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方剂学》教材之中,最常见的如治热极生风的代表方剂羚角钩藤汤,治少阳湿热痰浊证的代表方蒿芩清胆汤,治阴虚表证的加减葳蕤汤,治少阳轻证的柴胡枳桂汤等。其它诸如阿胶鸡子黄汤、柴胡达原饮、枳实导滞汤、葱豉桔梗汤、柴胡陷胸汤等也书上有名。通过方剂教学,绍派的学理,绍派的制方用药经验,得以广泛传播。
【】
1] 叶新苗.温病学的辨证发展[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2,16(5):3?4.
[2] 陆晓东.绍派伤寒学术研究[M].绍兴:绍兴中医学会编,1987:23?27.
[3] 徐荣斋.重订通俗伤寒论[M].杭州:杭州新医书局,19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