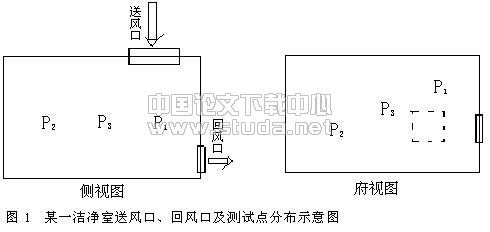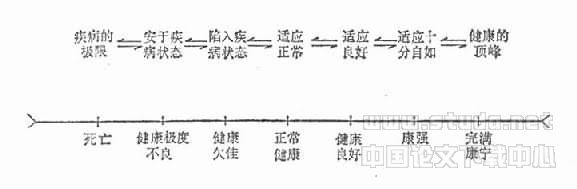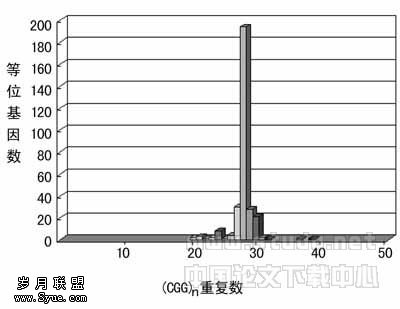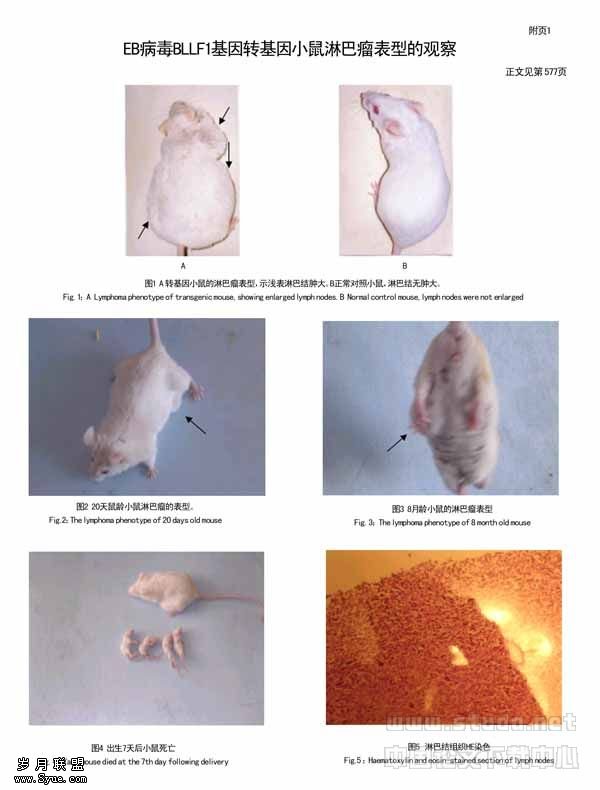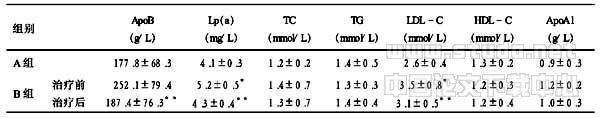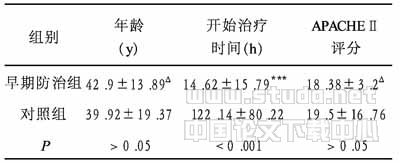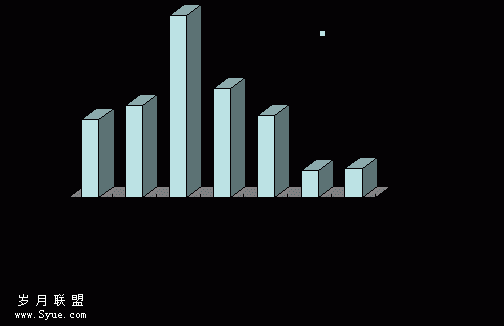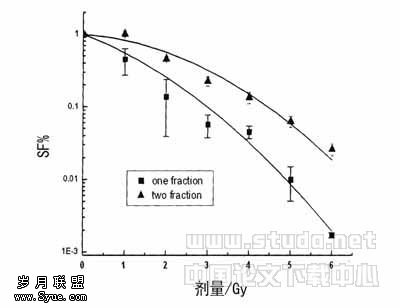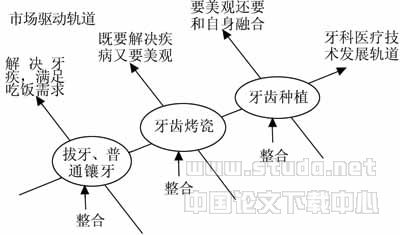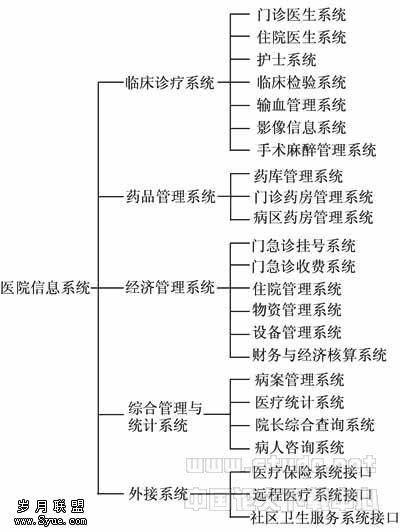从象思维的“迷失”看历史中对三焦无形说的“误读”
【摘要】 三焦是先哲运用象思维创生藏象之名的典型,“有名无形”并非“无状空有名”;宋儒的思想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是中医史上产生各种有形三焦说的根源;回归“象观”的认识路线才能真正体悟经典中的三焦原奥。
【关键词】 三焦学说 藏象学说 象思维 三焦 无形说 有形说 思维转型
Abstract:Chinese medicine,as “Xiang science” representatives,is that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natural person.”It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cang xiang” concept “ and viscera” concept;the two are not in one?to?one relationship.Re?understanding of the sanjiao in the classic original meaning,and the whole Chinese academic roots,sanjiao is one of the typical.
Key words:Sanjiao doctrine;viscera?picture doctrine;xiang thinking;Sanjiao;invisible;visible;thinking in transition
三焦“无形”和“有形”的问题,是中医学在过程中产生的。考察“三焦争议”的开端和扩大的历史,可以发现认识主体具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转型特征。本文认为历史时期中“象思维”的失传,是造成对三焦无形说误解和批判的根源,而回归“象思维”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医的藏象经络学说。三焦是藏象中的一个典型,《难经》明确提出三焦有名无形,现在看来正是唯恐后人误读。
1 三焦是《内经》、《难经》时代原发创生的式(象)科学之“名”
刘长林先生《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1]一书指明:“中国传统思维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意象思维。”“中国有自己的科学源流,有系统发达的科学思想,这就是象科学观。中国象科学的基础,即中国传统的认识论,集中在《周易》和老庄孔孟的思想中‘天下随时’;‘道法’;‘立象尽意’,这三句话是中国认识论的三项基本原则。”《黄帝内经》正是在这样的哲学理论影响下创生的,至今是中医理论的渊薮。藏象经络学说是其中的精华,也是中医学至今不被西医学所替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先生认为:“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藏象”概念正是先哲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的研究而形成的,也即“以象测藏”。《内经》中确实有解剖学的方法,但这并非该书的认识论主流,“藏府概念主要不是由与其对应的解剖器官决定,而是由人身整体功能的结构划分来确认。”“三焦作为一府并没有单独与与之对应的解剖器官”。
《素问》开篇即表明继承老子“道生万物”的认识。老子指称“道”为宇宙万物的本根,同时又是宇宙运化的总则。《六节藏象论》是整部《内经》中唯一出现“藏象”概念的一篇,篇中黄帝说:“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上半句表示认同老庄和《周易》“无形生有形”的宇宙创生论,也就是“朴散为器”的过程;下半句“因变以正名”十分重要,先看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即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据刘长林先生书中剖析,这表明老子肯定了抽象思维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认识还应进一步深化,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刘先生说:“从认识论上说,执道御有即以道领器,就是要求在研察具体事物时,主体要与客体相容,要把事物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中,放在宇宙整体之中,要探究事物的自然生化和与宇宙整体的联系,要从整体决定部分的角度说明事物的性质和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要认识事物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的现象层面的。因此,在认识和实践中,既不能离开抽象思维,必须借助和利用抽象思维的方法与成果,但是决不停留在抽象思维之上,一定要以主客兼容,天人合一的意象思维对其加以统摄,使其所获知识“转型”,纳入到意象思维的总体框架中来,与意象思维的方法和认识成果相融合,服从原本整体、因物自然的要求,这样才能实现‘为道’的认识路线。”因此黄帝后一句接着问:“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这正是“执道御有、以道领器”认识观的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帝提出了“藏象何如?”可见,这个“藏象”已经超越了单从抽象思维而来的解剖“脏腑”概念。
《周易》认为“言不尽意”,故“立象尽意”。刘先生说:“《易传》所谓‘尽意’是为了‘尽神’,尽神即知‘变化之道’,而知‘变化之道’系对妙化万物、阴阳不测的把握。‘尽意’—‘尽神’意谓既要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又要把握事物的丰富性、无穷变易性和不确定性。”“意象思维所追寻的正是事物在自然的时间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体状态和整体性规律”。《内经》作者也十分清楚语言的局限性,所以《灵兰秘典论》“中止”了抽象思维,而采用“象思维”进行取象比类来给十二脏下定义。该篇提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这正是由于人之生命整体的气化和水化过程具有独立意义。“意象思维并不排斥抽象思维,而且需要与抽象思维合作,将其统摄在自己的框架内。”如《灵枢·营卫生会》篇对于三焦有很多的描述,这些语言的作用在于“言以筑象”,在岐伯描述了三焦的“境域之象”以后,“黄帝曰:善。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之谓也。”可见黄帝认为“尽意”的目的达到了。仅仅懂得抽象思维是绝不能领悟:“三焦之所出”是对人身大化流行中所呈现的本真状态,所做出的“主客相融”性认识。其目的正是要超越“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因为“面对事物的自然过程,即自然的时间变化,抽象思维显得苍白无力”。
三焦是对人之生命自然整体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气化过程的“象思维”表达。“三”为人身上、中、下三个“境域”,焦为“火”字底,表明其不在“有形”的层次。对于“水道”,应当作“象思维”的体悟,此水为“生命本源”的象征。如《天一生水》之“水”;《老子》“上善若水”之“水”;《管子·水地篇》也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水道”当为人身之“水利枢纽系统”的譬喻,兴修水利正是国家大事,所以《灵兰秘典论》将人与国家相比类的时候,将“三焦”单独列为一府,称“决渎之官”。关于决渎的“渎”字,在断定为西汉初期的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脉书》中有一篇《六痛》:“夫骨者拄也。筋者束也。血者濡也。脉者讀(沟渠,水道)也。肉者附也。气者煦也。” [2]可见,将“脉”、“渎”、“水道”、“气道”相等同是有道理的,正如黄帝在《灵枢·决气》中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这些充分体现了《内经》的整体观是“道的整体观”,而非“实体总和的整体观”。《内经》对于道家、易学的继承是十分主动、高度自觉的。可见“三焦”是一个强为之“名”的“象”概念。否则以《难经》对脏腑详细的解剖学考察,何以反而明确提出了三焦无形说呢?依愚之见,“三焦”一府当在《内经》作者们充分自觉运用“象思维”后才形成。
黄拓:从象思维的“迷失”看历史中对三焦无形说的“误读”黄拓: 从象思维的“迷失”看历史中对三焦无形说的“误读”严健民 [3]认为,三焦概念产生的时限当在战国末年,并认为“秦统一六国前医学上已有‘五脏’、‘五腑’的概念。”考察比《内经》成书较早的《淮南子》等著作,也未见“三焦”之名。因此我认为《史记》中提到“三焦”,这是三焦之名产生的下限。战国末年到西汉中期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化,早已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的洗礼,是中国哲学高度成熟的时期,也是“象思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时期。正如严先生说的三焦建构是医家出于对古代“六府”取象比类,和符合“十一常数”的要求,可见“三焦”概念是在自觉运用“象思维”的方法下产生的。当时医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藏象”和“脏腑”的区别,否则《内经》何必多此一举提出“藏象”概念呢?假如三焦如严先生说的“小网膜”、“大网膜”、“肠系膜”如此肉眼可见的组织,何以“三焦”一名如此晚出呢?他说:“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肯定,就是先秦学者们对于科学知识的认定是十分严肃的,……难道创‘三焦’说明消化生理时反不要解剖知识作基础了?”这种观点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没有意识到中医学在本质上是象科学的代表,尊重人身的自然整体,采取主客相融的立场来认识生命过程,主要关注人的现象层面。这里并非要否定解剖学的重要性,只是应当承认“藏象”具有的独立意义。正因三焦是自觉运用“意象思维”而创生的概念,所以相对于其他有对应解剖脏器的“藏象”,三焦表现为“无形”。《难经》离《内经》成书年代较近,对这一问题看得十分清楚,因此特别警示后人。
刘长林先生说:“《周易》之道就是要指导人们自觉地去认识具体事物的终与始,死与生,通过这种时间性联系,去把握它们自然演进的生命过程。”《难经》引入汉代发展成熟的“元气说”,来认识人的生命过程。这是继《内经》后,对“命门”、“三焦”学说的发展,三焦被尊号为“原”,是“原气之别使”、“主通行三气”、“主持诸气”、“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难经》的“命门元气三焦”理论,正是对人之生命的“原始要终”。《难经》中说三焦“有名无形”的“无形”,并非如高阳生说的“无状空有名”,而是有实指,切莫忘记“道”、“气”、“元气”也是一种实际存在。这是中医学乃至中国学术的根本所在。“气”和“道”可以等同,都是“至大无外,至细无内”、“无不通透”的实际存在,可以创生“有形”,但是在“无形”的层次,也即《周易》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说“物物者非物”也是这个意思。因此,愚以为《难经》三焦无形说是指“三焦”不在“器”的层面,即不是有形脏腑。
杨仕哲[4]说:“中国中古时期的医学大家,都持三焦是无形气府的看法。”确实,张仲景、王叔和、华佗、巢元方、孙思邈、王焘等大批唐代以前第一流学者,均承继三焦无形说,处于认识统一期。但如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所言:“宋以后,新说代兴,《四库提要》云:儒家之门户分于宋,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此以其显著者言也,实者其机亦肇自北宋。”“宋儒起而以意推求”,“不能尽得古人立说之意。”由于宋代儒、医结合紧密,可以发现正是儒医的思维转型表现得尤为明显。宋代对三焦的认识差异,由对“无形说”的误读,进而产生“有形说”。
2 宋代儒家思想转型与医家“有形三焦说”的产生关系密切
和严健民先生一样,南宋后许多人认为“三焦脂膜说”是陈无择等人,在经过一番“科学而严肃的腹腔解剖”基础上形成的。其实不然,陈无择不过是道听途说。其真正的出处在于苏辙(1039—1112)写于北宋哲宗元符2年(1099年)前后的《龙川略志·医术论三焦》,篇中首先提到对古代三焦无形说产生怀疑的是单骧,此人曾为当时御医,宋英宗治平中(1064~1068)他告诉辙曰:“古人论五脏六腑,其说有谬者。”“王叔和言三焦有脏无形,不亦大谬乎! 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何以藏系哉?”苏轼《东坡志林》“单骧孙兆”篇中说:“蜀人单骧者,举进士不第,顾以医闻。其术虽本于《难经》、《素问》,而别出新意,往往巧发奇中,然未能十全也。”可见单骧为儒医,敢于“别出新意”,怀疑古人甚至经典著作。当苏辙为齐州从事期间(1073年夏~1076年),他将骧的“新意”告诉业医的举子徐遁,遁喜而把他过去从“群丐相脔割而食”剩下的残骸中,“悟出右肾下脂膜如手大者为三焦”一事相告,并说:“单君之言,与所见悬合,可以正古人之谬矣!”真可谓遇见“知己”了。
陈无择(1131~1189)撰成于1174年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焦精腑辨正”篇,以及张杲(1149~1227)刊行于1189年的《医说》“五脏六腑其说有谬”篇,不过是因循《龙川志》所言。而陈无择承接单骧说:“扁鹊乃云∶三焦有位无形,其意以为上中二焦,如沤如雾,下焦如渎,不可遍见,故曰有位无形。而王叔和辈,失其旨意,遽云,俾后辈承缪不已。且名以名实,无实奚名,果其无形,尚何以藏精系胞为哉。”考叔和《脉经》,并无三焦“无状空有名”之说。而是出自于高阳生伪托叔和之《脉诀》,据方春阳先生 [5]考证:“《脉诀》之成书,当在熙宁元年(1068)至元祐五年(1090)之间,则高阳生为宋朝人已无疑问”。元泰定四年(1327)医学教授谢晋翁撰《脉经序》,序中引宋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福州人陈孔硕曰:“《脉诀》出而《脉经》隐。”
杨仕哲认为:“陈氏所处时代离中医建构期的下限年代(晋代) 已有一段距离,约七八个世纪之久,难免与古代的中医气化思想脱钩。”本人认为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从北宋单骧、徐遁、高阳生到南宋陈无择、张杲等人,对于三焦无形说的原义已不可识。其根源在于宋代儒家思想的转型,特别是和的密切相关。首先这些医家大多数为儒医,可以说这是宋代的学风,如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其次,他们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苏辙《龙川略志》中说:“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也就是北宋著名的儒学家石介(1005-1045),他出于范仲淹门下,与欧阳修同年进士,他对汉唐注疏不满,被认为是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其撰写《怪说》、《论》等文章,称佛、老为“妖妄怪诞之教”,还把老子硬说成是一个“自胡而来”、欲“以其道易中国之道”、名曰“聃”的“庞眉”。由于石介当时身居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官之职,所以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谈佛老”(《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引《吕氏家塾记》)。欧阳修的《石徂徕先生墓志》对于徐遁“发现三焦形体”这件事也有记载。苏轼、苏辙都是欧阳修的弟子,可见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
明·李濂《医史》中认为:“晦庵朱子则谓《脉诀》辞虽鄙浅,而直指高骨为关之说,合于《难经》本旨,盖亦取之。”可见朱熹仍误以为《脉诀》为叔和之作,因为这一认识在《脉经》中已经存在。蔡元定为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另著一部《脉经》时已见过《三因方》,认识到《脉诀》是伪书,在他书中有“论三焦”一篇,估计应当也是反对“三焦无状空有名”之论。当时医家往往将“三焦有名无形”等同于高阳生“三焦无状空有名”。由于该书全本目前尚未发现,关于他是否承认“脂膜说”还不得而知,据明·刘浴德《脉学三书》后附的《医林续传》中“蔡西山传”[6],以及明·俞弁《续医说》中均提到蔡氏“论三焦”后引《白虎通》中《礼运记》曰∶“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俞氏客观地说:“然未曾发明其义。”但是二人均认为蔡西山“以三焦为有形”。其实“若窍”、“若编”、“若渎”亦是象思维的“筑象之言”,这样的语言不过如禅宗标月之“指”。考察《白虎通·情性》篇中的原文是:“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故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很显然这是在引用《难经》的观点,如果《礼运记》真的认为三焦为有形之“实体脏腑”,何以不直接反对《难经》十分明显的“三焦有名无形说”?可见孙景思辈据此“推解”三焦为有形观点看来并不符合原意。
刘长林先生对于宋儒思想转型有很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有”和“无”是中国认识世界所形成的特有的范畴,是最具中国智慧同时又最易引起歧义的范畴。“有”和“无”是意象思维的产物,抽象思维是不可能产生“有”和“无”的。从本质上说,“有”和“无”是时间性的哲学范畴,沿着抽象思维的思路则难于理解它们,就像用西医解剖生理学的眼光难于理解中医藏象经络一样。宋代张载(1020-1077)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此言有点失之轻率,既不符合实际,更是对‘言有无’的错误评判。有无理论为老子所创,其精神却贯穿《易经》六十四卦。《易传》作者则自觉将有无思想向前推进。他说:“二程、朱熹公开反对老子,高举《周易》,推崇《系辞》,却不知《系辞》所论‘易之道’与老子之道相通。”经过二程的一番改造,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实质上已不再是无形与有形的区别,而是抽象概念与实际存在的区别。形而上者为非实在,形而下者为实在。朱熹完全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并演绎成庞大的“理”学体系。这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无论对于易学传统,道家传统,还是先秦儒家传统,都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变化。它不是沿着原来的方向向前发展,而是对传统的破坏。这种破坏有其产生的合理原因,但是消极的方面远大于积极的方面。
3 宋以后医家对于三焦无形说的捍卫,并重视发展三焦辨证
应当肯定的是信奉道教的宋徽宗,在政和年间(1111—1118)主编《圣济总录》力主三焦无形说,也使得三焦辨证向前发展。该书《三焦统论》中说:“论曰三焦有名无形,主持诸气,以象三才之用,故呼吸升降,水谷往来,皆待此以通达”。后世或误此语为李东垣或是吴勉学之言,其实出处正在于此。惜乎此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南宋反未见此书。此后王重阳(1112—1170)创立的全真道教在北方开始兴盛,这些思想对北方的河间及易水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金元时期刘河间(约1120~1200)、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都是河北人,他们师承相授继承三焦无形说,高度重视三焦辨证的运用,为三焦学说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李梴、孙一奎、赵献可均继承了三焦无形说。到了清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反复提醒后人应当续接河间关于三焦的认识,如他说:“故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暑伤气分,上焦先受,河间法至精至妙。后医未读其书,焉能治病臻效?”如此可见一斑。吴鞠通《温病条辨》“治病法论”中说:“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这正是将《内经》所筑三焦境域之“象”为“境域式象”,成为温病的大法,可见从象思维继而形成象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典型。
4 从西学东渐到西方中心主义,比附西医学的方法,使三焦无形说原奥进一步“迷失”
上第二次大的医家思想转型由西学东渐引起,至清末西医学的大量传入,形成了中西汇通派,直至中西结合派。从唐容川的“三焦膜油说”,到章太炎的“三焦淋巴腺说”、再到……,这些五花八门的三焦新说,究其实质都是运用以西医解剖学(包括微观)为代表的抽象思维,来“探明”《内经》、《难经》基于意象思维下创生的“三焦”。深深陷入了主客对立的实体思维之中,而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象思维在西方中心主义中逐渐“迷失”,三焦正如庄子寓言中的“混沌”,在被凿开了七窍之后,死了。
5 藏象研究应当回归“象思维”,为三焦“正名”,成当务之急
所幸,当前中国“象思维”传统正在复兴,其中,以刘长林先生《中国象科学观》一书最具有代表性。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三焦、藏象学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武器。千年前的宋代,由于部分儒医对传统的背离导致了“三焦有形说”的兴起。学术争鸣是件好事,可是作为学术理论基石之一的“三焦”长期争议不休,绝非好事。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拾“象思维”的认识论路线,挖掘三焦“无形”的真实内涵,而“无形”也绝非空洞无物。刘先生在《中医药走出困境的关键和建议》[6]一文中提出应当“对传统中医部的学生,要做好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训练。”等见解十分深刻,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有必要在学界开展一场中医科学范式大讨论。
【】
[1]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8.
[2]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315?317.
[3]严健民.战国消化生理三焦(集)配六腑新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13(6):408?410.
[4]杨仕哲.从历史的分期重新检视三焦的实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11):24?25.
[5]郑金生.蔡西山《脉经》考[J].中华医史杂志,2002,32(2):82?84.
[6]刘长林.中医药走出困境的关键和建议[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1(6):7?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