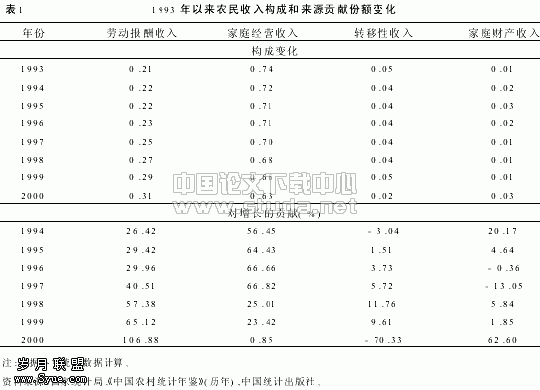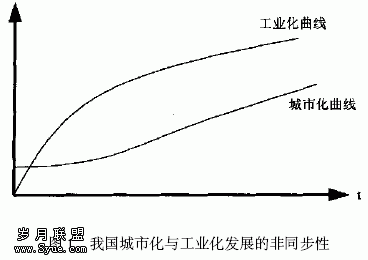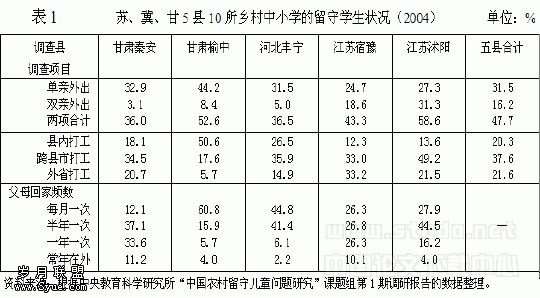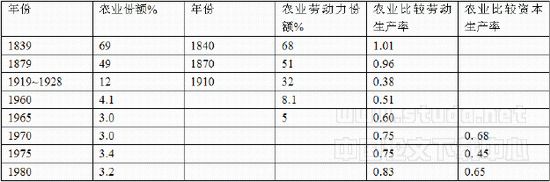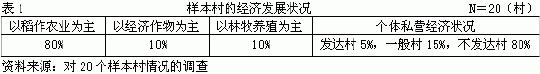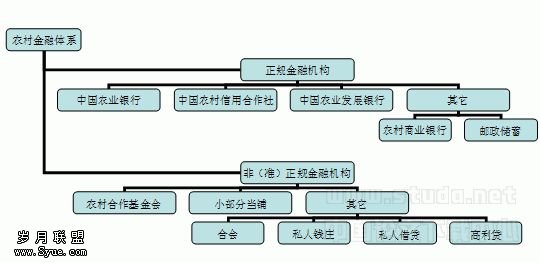近代山东农村的土地经营方式:惯行述描与制度分析
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划分,近代土地经营可分为租佃、雇工与自耕三种形式。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是发生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自耕较多地反映了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乃至近代时人的社会调查、方志写作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小自耕农、佃农的家内劳动关系及户际劳动协作关系(即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帮工搭套”)重视不够,甚或将其完全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小自耕农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但在耕地、播种、收获等农忙季节,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力、畜力、农具投入都较平时为多,这时就需要小农户间人力、畜力、农具的劳动组合。这种劳动协作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小农户的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户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习惯法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契约关系。由此说来,租地农户会面临两种契约关系,即租佃关系和户际劳动协作关系。
一、租佃经营的民间惯行
清末至民国时期,因地权渐趋分散,山东农村的土地租佃比例较小,佃户占总农户的11.1%,半佃农占18.5%(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第65页。),但租佃关系的分布却较为广泛,几乎80%的村落存有租佃关系。据抗战后期的调查,鲁南2528村,有租佃关系者1981村,占78%;鲁中区沂蒙县1000个村庄中,有租佃关系者867村;鲁南区600个村,501村存在租佃关系;泰山区五个县1012村有租佃关系者909村,莒南县513村有租佃关系者430村;就连一向认为租佃关系很少的淄川山区,据减租减息时调查,129村有租佃关系者89村,亦占69%(注:《山东租佃关系分布概况》,载《山东群众》第7期,转引自朱玉湘《近代山东的租佃制度》,见《山东史志资料》1984年第1辑。)。因大地主较少,在存有租佃关系的村落中,仅有少数几户出租户,且情况较复杂,有些是鳏寡孤独没有劳力,或是土地太少,又缺少耕牛、农具和种子,只好到外地谋生,被迫将土地出租。在村地主一般是不出租土地的,多采行雇工经营方式,只有不在村地主(包括城居地主和外村地主)在多数情况下才出租土地。
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永佃制,在山东极为罕见,在全省比较普遍的租佃制度是分成租佃制与定契制两种。依分成租佃制,“人工牲畜农具概归佃户担任。肥料种子则多由主佃双方均摊。至收获物则按一定之比率分配,有平均分配者,有四六分者,亦有三七分者。分租制大概无期限,可以继续耕种多年,亦有一年一易者,无押款,亦不另立契约。此种制度,于丰年时佃户固可以多得利益,若遇荒歉,则佃户所分得之一部分,常不足以补偿其资本与劳力。”而定额租制,则“耕作费用,统归佃户担任。地主坐享固定之地租,地租或以物纳或以钱纳。包租制有一定之期限,或三年或五年,须凭中书立契约,写明地租定额及包种期限等。……无论包租或分租,所有应纳田赋及各种捐税,均由地主负担。”(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第28~29页。)分租制与定租制只是出租户与佃户之间收益分配的不同方式,如分析地租形态,则可以进一步划分实物分成租、实物定额租、货币定额租与劳役地租。
分成租制的收益分配形式,一般以交纳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为主,故称实物分成租,这类租佃形态占全省各类地租的39.1%。以分成租制为主的,有博山、峄县、济宁、郯城、莒县、沂水、曹县、城武、定陶、茌平、安邱等县。分成租佃制在各县乡间又有不同的惯例,有的叫外分子牛,即一切农具、牲畜、种子、肥料全由佃户出,收获后佃户与地主平分,这在土地肥沃的地方较为通行;有的叫里分子牛,地主养牛,佃户使用,牛草归地主,佃户负责铡草垫栏,肥料归佃户使用;有的叫赔牛客,地主买一头牛,借给佃户用,作价要佃户逐年偿还,而佃户有好多年还不清者,实际上带有高利贷性质。还有叫估租,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是由地主估计产量,向佃户多要粮或要好粮;有的叫抽陇子,地主看好哪几拢就割哪几陇,剩下的归佃户。
这种分租制,名义上是平分,但享有土地占有权的出租地主一般在收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在鲁西南曹县的高韦庄,租佃制度以分成租为主,又分两种,“(一)停种——佃主只出地,所有种地的家具及牲口、人力都出到佃农身上,种出来的庄稼两边平分。(二)三七分——佃农只管出力的事,所有牲口及家具都是佃主的,分法是佃主分十分之七,而佃农则十分之三;凡是杆草、麦秸之类,佃农都没分的权利,理由是这些须给牲口吃。然而在停种地,佃主虽是并不养一个牲口,杆草麦秸却是一斤也不能少分,理由是得‘均分’。在停种地中,种子照例是佃主先拿,等到粮食上场,再行收回;各家的办法则是以官堆(指主佃未分之前的粮堆)上一升种子收回三升。……至于佃主要从一升取三升的理由是这样:官堆即还没分,三升里头应有他自己的一升半;余下的那一升半,则是一升本,半升利。(注:韦昌骢:《山东单曹县农民的痛苦》,《村治》第1卷第7期,1930年9月。)。
与此相类似,鲁中有些县盛行伙种制(又名“干提鞭),一切农本(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供给,佃户仅出劳力,因此租额较高,地主分得六成或七成(注:薛暮桥:《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土地组报告(草案)》,《山东革命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211页。)。莒南县的“双除种”法与曹县高韦庄一升种子收回三升也较相近,即“如种地时用地主的种子,收下来归还,借一还二,如种一亩麦须种子八斤,收下来就得扣十六斤给地主,一般每亩可收八十斤麦,扣去种子十六斤,后再平分,佃户就只能分到三十二斤。往往在歉收年成,把收下的粮全给地主充作种子还不够,欠下的第二年仍须补交。”(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莒南县三个区十一个村的调查》,载《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3页。)一般说来,凡是征收实物分成租者,多是土质瘠薄或容易受灾,由于农作物的产量没有保障,从而采用分成制;在村地主给佃农提供生产资料,监督佃户生产过程,利用分成制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甚或佃农的必要劳动。
实物定额租又称谷租,即佃户要交给地主定额之农产物,无论丰歉,不得短少。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调查,山东省至少有47县实行实物定额租制。如历城县,每亩收租一至两斗,该县冷水沟村,旱地二年三作,上等田头一年种小麦及谷子,每年交租二斗五升;第二年种大豆,收一斗五升租。泰安县,每亩收租80到150斤,该县第一区西隅乡涝洼庄有40%的土地征收定租地租,租额甚至高达每亩350斤,超过了该县的一般水平。像冷水沟、涝洼庄这样靠近大中城市的郊区村落,一般土地较肥沃,水源较为充足,粮食产量常有保证,故多征收定额地租;又在定额地租制,地主只管收租,比分成租减去许多手续,因此不在村地主多喜欢用此种租制。
货币地租又称钱租,一般有一定额数。货币地租制因所纳地租为货币,故多在商业性农作物种植较为广泛的地区如胶济铁路沿线各县流行。临朐县有桑田6万余亩,种烟的农户也很多,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原来的分租制逐渐为货币地租所取代,原“一夫授田七亩(大亩——引者注),牛力、子种、肥料悉由地主出,佃夫担任耕作之劳,登场后,获粮食地除亩留除二斗外(俗称地粮食),余者两方均分之。但佃期无常,地主有不时之责,佃户多过望之怨,因而发生龃龉者往往有之,此佃种制度所不能行于今日之临朐也。近数年来盖藏日竭,谋生汲汲,一般农民多有租地耕种,藉牟赢余以糊口者。例如每地一亩租金若干,与地主约定年限内不欠租价,不准退租,如此办法,在多地之主可以不劳耕耘而得适中之代价,在勤奋农夫亦可以藉此奋力,每亩有所弋获。”(注:《临朐县志》卷十五,1935年,第30页。)但在1937年以后,因通货膨胀,货币地租也有转为实物地租的趋向。
劳役地租是作为租佃制尤其是实物分成租制所派生的地租形态,体现了主佃间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原始形态的劳役地租很少,多数是以副租形式出现的。自清初至民国时期,山东省劳役地租在各地仍有存在。曲阜孔府贵族地主庄园,在租佃关系方面,仍然保留着劳役地租的形式,甚至有庙户、林户、喇叭户和哭丧户等农奴制的残余形式(注:参阅齐武《孔氏地主庄园》,中国社会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2页。)。在清季乾隆年间,出租地主与佃地农户之间虽然没有严格的封建等级隶属关系(所谓“主仆名分”),但劳役地租在各县仍普遍存在。如高密县单阜常役使佃户张杰推送煤炭,甚至菏泽县谷王氏因系佃主谷正道之族侄媳而役使佃户王三(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2、729页。)。
至民国时期,山东各地仍存在劳役地租。据1934年调查,全省30.2%的出租土地有劳役地租。何思源先生曾描述了家乡鲁西南一带的劳役地租情形,他写道:“我在青年时代(1912年左右)就亲自看见一个例子,……曹县有个地主朱凯臣,他家朱庄是个寨子。他住在中间一个砖围子里,周围都是他的佃户,此外还有几个‘下庄子’。佃户耕他的地,住他的房子。佃户不只交纳地租,并且需要‘出差’。有一次佃户被派出差到曹州府城送西瓜。因为数目不对而质量不好,他回去后被打了40棍并拆房赶出庄去。……这样的封建剥削制度,据我所知,在单县、曹县、滕县、邹县等处是普遍的,不是特殊的。”(注:何思源:《梁漱溟先生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光明日报》1952年1月10日。)劳役地租不是独立的租佃形态,多作为实物分成租制的次生形态,除个别情况需要写进租约,一般均是口头约定,或据乡俗乡例而临时派差。
地主为了招揽佃户,常口头散布乡里,或托人介绍。农民想租种土地,也注意这种信息,得到信息后,即设法了解该田的土质,然后托人与田主联系。田主了解佃户情况后,经中人及双方协商,最后订立佃约。租佃关系的成立,有的仅凭口头约定。一般在村的中小地主多采用口头约,或是佃户与地主有亲戚关系,不需要中间人说合,也大多采用这种契约形式,分成租制多与口头契约相对应。凡收钱租、谷租,多用书面契约。书面契约的名称不一,较通行的叫“租单”、“租帖”、“揽约”或“揽票”等。书面租约的内容包括租地面积、租额、租期、交租方式、交租时间、地主提供的耕作条件及主佃、中人姓名、签约日期。
租佃契约仅仅是在书面上反映了出租地主与佃地农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租佃契约中尚看不出租佃关系的实际发生过程。一般占地超过百亩的在村地主对所在村落周围的土地多采取雇工经营形式,对远离本村的土地才采取出租经营方式。而本村的缺劳力小农户也有可能出租土地,如前述后夏寨村马吴氏。在广饶县北隋村的24个出租户中,没有一家地主,除贫农一部分因乏力耕种而全部出租外,其余则都有自耕田,与出租地主不同,甚至有的出租户本身就是被剥削者。
租佃与雇工经营方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上,近代山东的雇工与租佃经营形式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在村地主对所在村落附近的土地多实行雇工经营方式,雇工又分长工和短工。短工多在农忙如收割时雇用,以劳动日,或给粮,或给钱,雇主与短工间表现的是较为单纯的雇佣关系。雇长工,情况则复杂些。如“东阿县之长工雇主只管食住,不给工资,而抽田地出产十分之一给长工,以为工资,邱县亦有如此者。”(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53页。)这种雇工经营方式颇类似于流行山东各县的“二八种地”的租佃经营方式。“‘二八种地’虽似租佃,却非完全之租佃形式,种子肥料概由地主担任,农工只负耕耘收获之责。田地之出产地主得八成,农工得二成。而郓城县之农工,仅负耘获之责者,则得二成,若兼负耕种之责,须得三成。此种制度亦盛行于河南,有称之为‘拉鞭地’者。”(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56页。)这种经营方式应看作是租佃经营与雇工经营的合一。
雇工与租佃结合程度更深的,是一种地主给长工土地使用权以代工资的经营方式,在临邑、郯城、长清、峄县、德县、金乡、平阴、恩县等地颇为流行。“此种长工,乃雇主给以田地若干亩,使其耕种收获,为其所有,以代工资。雇主有工作,雇工来服务,无工作则回家,亦有常住雇主家服务者。除给田地耕种外,尚须给房屋居住。然亦有不给房屋者。所给田地之亩数,大抵皆在壮农每年能耕亩数之百分之五十以下,间有超过百分之五十者,其在各省颇为稀少。”(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之调查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8月,第335页。)所给使用权的地亩数额在不同的长工之间,因其劳动熟练程度不同也有差别,如“德县之此种佣工,当领袖工人者给田地五亩,非领袖工人者则给四亩”;而在利津县,则“雇主给佣工些许田地耕种,减低工资。”(注:费耕石:《雇农工资统计及其分析》,《内政统计季刊》第1期,1936年10月,第74~75页。)
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给长工,是雇工经营与租佃经营相结合的表现形态,而流行于鲁西平原地区的“种地头”制,则是经营地主出让部分土地管理权的一种雇工经营制度。朝城县(现为莘县朝城镇)即流行这种雇佣制度。该县位于大运河、黄河交叉处,与河南省毗邻,地狭人稠,劳动力大量过剩,但地权集中程度尚不严重,县内大地主很少,小地主居多,一般有3顷地就算是大地主了。因此,地主土地极少出租,而是同时雇请长工和“种地头”耕种。长工由地主供给饭食住宿,按年支付货币工资。种地头在自己家里吃饭,也不拿工资,只在秋后分取二成或三成粮食,俗谓“二八(或三七)劈粮食”。种地头一般都是本村人,同经营地主关系比较密切。他每天到地主家里带领和指挥长工劳动,计划和安排生产。但他只干地里和场院的农活,不管地主的家务杂活,而长工既干农活,也要承担家务杂活。通常一百亩左右雇一名长工和一名种地头。县城西北15里的王庄,有地主王之政占地3顷,全部采取雇工经营。本世纪30年代初,他雇了两个种地头和四个长工。种地头和长工内部分别有“大头”、“二头”、“三头”和“大鞭”、“二鞭”、“三鞭”的称谓。大头指挥一切,种地头的名称盖源于此。如果农忙时雇用短工,则由地主和种地头分别雇请和管饭付酬,但数量须对等。种地头和长工的雇期通常为一年。每到中秋节,地里收割完毕,地主请种地头和长工一起吃饭,同时决定明年是否续雇。如果地主、种地头、长工三方都满意,雇佣关系继续;否则,只要一方不满意雇佣关系即行终止。据当地农民讲,这种经营方式的好处是,可由种地头筹划生产,地主比单独雇工经营省心。因为种地头是按成分粮,收成好坏直接决定他的收入,又有指挥长工生产的权力,就会自觉地督促长工搞好生产,而不会联合长工以怠工方式来对付地主。这种雇工经营方式也带有租佃制的某些特征,一如前述较为流行的“二八种地”。诚如有学者归结的,这是一种地主供给全部生产资料、准佃农只出劳力的分益雇役制(或称帮工佃种制)。种地头与地主是一种以租佃关系为主兼具雇佣关系的契约关系,长工与地主间则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
地权形态的表现形式是极其复杂的。在山东各县,有相当一部分小自耕农,除耕种自家土地外,尚有余力,即设法佃种或为地主佣工,以补原有土地生产之不足。自耕农兼佃农如土地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则尚须雇工经营。如在鲁南平原区、鲁东南山区的峄县、滕县和临沂县,有一种大佃,“佃地在百亩以上三百亩以下,耕牛至少有二、三具(硕牛二头为一具,羸的不等),大车一辆,耕具完备,并雇有‘大领’(农作时之领工者)。也有些大佃自充‘大领’,但须深通农事,农作娴熟,方够资格,否则只有年出工资雇‘大领’代疱(大领工资每年至多不过三十五元)。肥料完全自备,种籽与地主分出,不为地主服役,但遇婚丧除外。”象这样的“大佃”雇用农工,甚或即具备了经营地主的身份特征。佃种土地10亩以上20亩以下的佃农,称为“小佃”,因耕牛、农具之缺乏,需要向“大佃”或地主借使耕牛、耕具,但须以劳动力作为交换条件,俗称“以人力换牛力”。“一般一户大佃名下有四户小佃(俗称小佃为‘打场拢的’),这四户佃农,听从大佃或大佃的‘大领’指使,耕耘收获,都要完了大佃的事,方才可以来做自己的工作。……也有些小佃在自耕的地主名下充当‘打场拢的’。至于肥料、种籽,与大佃同,但地主无论何事,小佃均可任其驱使,名为‘出差’。”(注:黄鲁珍:《鲁南临峄滕三县的租佃制度》,《东方杂志》32卷4号,1935年2月,第88页。)这种“小佃”兼充“打场拢的”角色,在身份上即具有佃农与雇农合二为一的特征,不管其为“大佃”或为出租地主佣工均如此。
在山东各县还普通存在小自耕农兼雇农的现象,即俗称“带地佣工”。“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佣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佣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佣工为‘打裹’。”(注:陈正谟前揭文,载《中山文化馆季刊》创刊号,第355页。)带地佣工的小自耕农,为地主佣工也是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交换条件,以使用雇主家的耕畜、耕具,在雇佣关系上与前述峄县一带小佃农兼做“打场拢的”颇为相近。
长工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其雇佣契约关系的建立程序,在各县有不同的乡俗乡例,大约各县相同之处,在于雇用长工一般须有“中人”介绍,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仅需口头约定。在莱芜县,“长工、月工之雇佣,概为口头契约,每年于十月一日左右(时农事皆毕)劳动者凭‘中人’向地主说妥,愿担任那项脚差,‘作伙计’或‘二伙计’……,并言明工钱,而劳动者的行为由‘中人’担保,便算了事。契约一经成立,‘长工’便终年(一般的说)住在地主家里或园里,如有小疾病,地主可代付药费,且不扣工资,如遇大病时,‘长’工必须找代理人,或由地主代觅,但工资悉由有病的‘长工’担负。这时地主也不再代付药费。当主人对某工人不满意,或工人与主人间发生龃龉时,双方都能提出解雇,工资则按时间扣算。”(注:王毓铨:《山东莱芜状况》,(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第29期,1934年9月15日。)在招远县,经营地主雇佣农工也是口头约定,并经中人介绍,但约定工资后,“长工即到雇主家试工三日(如熟知者即无须试工了),试工期间无工资。试工满意,约即成立,如雇主认为不合,或长工以为活重或饮食不好,原约即可宣告无效。若约定而中途发生意见,亦可解约,视两方曲直,而断定应予长工之工资。”(注:晓梦:《山东招远农村概况》,同上,第48期,1935年1月26日。)长工与雇主的契约关系,由中人说合方得成立,这说明此种雇佣关系受民间惯行(乡俗乡例)调节。在馆陶县(今属河北),“雇工有戚谊者,论戚谊,无戚谊者,家长对雇工称名,雇工对家长或叔或伯或兄之,视年岁为定,衡无贫富阶级,亦无主仆名分,故相交以诚。”(注:刘清如主纂《馆陶县志》卷之六,礼俗志·风俗,1936年铅印本。)抛开方志作者的价值判断,可以看到该县的雇佣关系,呈现了利益与情感原则并重的运行特征。
而一般的经营地主甚或小自耕农、经营规模稍大的佃户,在农忙季节均需雇用短工,故各县一般均有若干劳动力市场,即“短工市”。在莱芜县,“全县各重要乡镇,都有‘短工市’,清晨四时至五时间,日工劳动者麇集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待雇主购买,愿从事某项工作者,则随带某项工作所需要的农具。购买者皆为地主或中农的‘作伙计’,工资之高低亦随时而异,但总较平时贵二三倍。在交易的那一刹那间,供求律显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交易成立后,大批短工便随着‘领短工的’人,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人不等,齐集地主的农场上去工作。”(注:王毓铨前揭文。)劳动力供求比率是影响短工雇佣关系成立及短工工资的主要因素,因之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市场取向是其主要原则。
一般的经营地主和较大的自耕农(相当于土改时划定的富裕中农或富农成分),均拥有可以独立耕作的耕畜和大农具(如犁、耙、大车、水车等),不需要与其他农户进行劳动协作。而一般的小自耕农和佃农大都缺乏耕畜和大农具,在每年的农忙季节尤其是春耕、秋耕时候,必须数家小农户形成一定的劳动组合,如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组成二牛或三牛犋。这有着技术与生态的双重原因。由于气候因素,播种和收获一定要不误农时,如邹平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宜时”(注:《邹平县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73页。),历城农谚“秋不让犋,麦不让场”(注:《历城县志》,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页。),正说明适时耕播、收获的重要性。又因财力限制,小农户常把购买和饲养一头耕畜的费用数家分摊,所以有时一户会拥有耕畜的一部分,俗谓“半头牛”、“一条腿”,即是所谓的帮工搭套。
莒南县官地村的小农户间即实行这种劳动组合。官地村是一个200余户人家的村落,“本村土地多为黑土,宜种高粱而不宜种穇子(稻田杂草,稗的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秆粗壮,穗直立,无芒,子粒可作饲料——据《新华词典》,引者),因此牛草困难,过去富农喂养耕畜也全靠换穷人牛草。十五六亩地的中农是很少养牲口的,只有少数兼营磨坊的农户养头小驴。往日的互助关系,也是建筑在这种客观基础上。有三种互助形式最普遍,一种是普通的搭犋,一种是用牛草换牛工,一种是帮工带地。后两种形式对于缺乏畜力的贫苦农民含有相当剥削性质,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注: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地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1944年11月,载《山东革命档案资料选编》,13辑,第190页。)官地村的三种劳动互助形式中,后两种类似于峄、滕、临沂三县“打场垅的“佃户”以人力换牛力”方式。对于占地较多的经营地主和富裕自耕农来说,这两种劳动互助形式带有雇工经营性质。由上亦可见,普通的“帮工搭套”劳动协作关系只是存在于官地村一部分农户之间。
帮工搭套的劳动协作关系的形成,有其赖以产生的生态条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山东生产力的水平。这种劳动协作关系在长期的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已逐步稳定化,表现在农民的行为方式上,就形成一定的习惯作法,亦即成为乡间惯行。从习惯法的角度看,小农户间的这种劳动组合方式,不象租佃、雇工契约关系那样正规,但协作农户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过,在这种协作关系开展过程中,农户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是完全对等的。在协作关系的发生机制中,经济利益驱动和家族伦理取向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胶东半岛区广饶县的辛集村,“劳动的组合,完全是感情的,他们各户之间谁多作少作都满不在乎。”如人和堂张大全和张复汉的合伙耕种,人和堂有地43.2亩,牲口少壮些,又有工具;张复汉有地34.2亩,只有一个牲口,每年他们只要耕过就算完。有同一家族的5户小自耕农,张景孔(地14.4亩,壮劳力一,驴一头)、景续(地13.57亩,壮劳力一)、景荣(地11.52亩、壮劳力一)、景彦(地11.52亩、壮劳力一)、景孟(地14.4亩,壮劳力二)共有一套农具,只有张景孔有一头驴,每年五家均合伙耕种。张兆林、武宪章、张凤桐、张兆元在一起合资开弓坊,在耕种方面也合伙,四家共有驴两头、土地58.32亩,除牲口拉弓外,也能把所有土地都耕种过来。在劳动合作方面,有张明敬与张健全合伙锄割的事例。类似的帮工搭套在该村还有许多。抗战期间,因耕畜大量减少,这种合伙耕种的劳动协作又较前有更大的发展(注:《辛集村土地经营的调查》,1944年2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卷宗字号26-214-3)。辛集村“帮工搭套”中劳动协作关系的成立,家庭伦理的价值选择起了基本的导向作用。在张景孔等五户小自耕农的劳动组合中,景孔与景孟、景荣与景彦的占地数额完全相等,这决不是统计数字上的偶然巧合,极有可能是两对兄弟刚经过分家析产。又据笔者在山东农村的生活体察,这两对兄弟再加张景续可能是五服之内的从堂兄弟关系。象辛集村的这种劳动协作方式,在近代山东农村当是十分普遍的。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的制度表现,不能仅仅在传统经济史的狭隘视野中,进行简单化、形式化的分析。
以上在民间惯行述描与制度变迁分析两层面,对近代山东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可知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已不是以往那种形式主义的研究所能完全涵盖的,也不由不使我们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教条,产生更深的怀疑。土地经营方式,既有一定的制度表现(如租佃制度、雇佣制度),又成为一定的民间惯行,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当是相对稳定的,而生产力特别是农业收益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起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