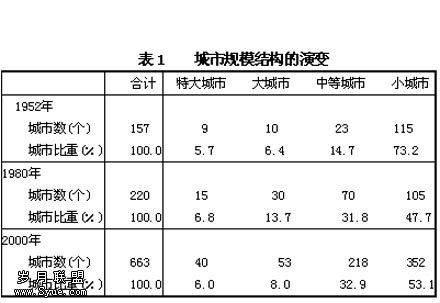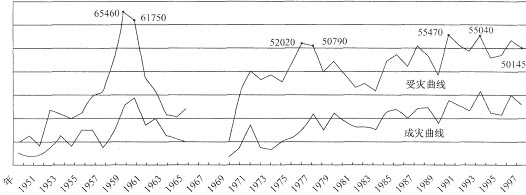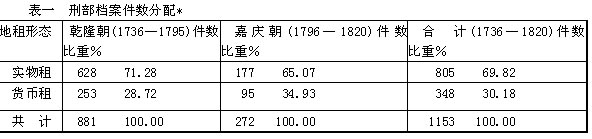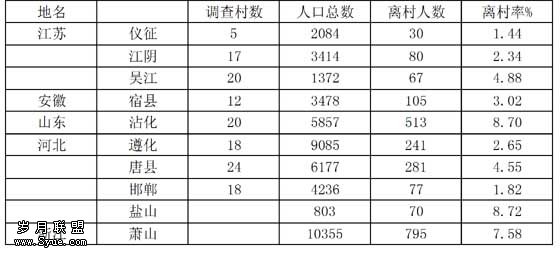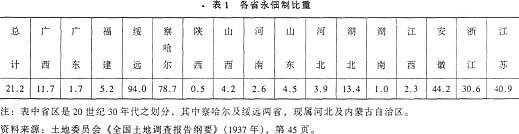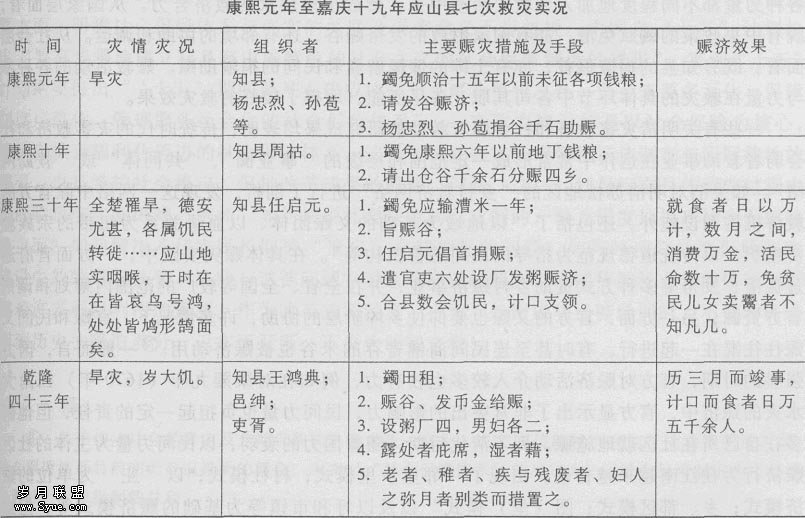明清时期土地市场化趋势的加速
[摘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的,农业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强,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地权转移的高频率与零细化,使得土地买卖愈加频繁。因此,土地市场的发育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地权市场范围继续扩大;二是地权与资本的相互转化;三是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结果是土地市场化趋势得以加快。
[关键词]明清时期;土地市场;土地经营权;土地市场化
唐均田制遭到破坏以后,由于封建国家对土地买卖限制与干预的废除,较为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正惟如此,唐中期至明中叶这一时期土地市场发展较为迅猛,土地买卖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土地买卖形式亦始见多样化发展之势,土地市场迈人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权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处,土地市场的发育还出现了新的迹象:一是地权与资本的相互转化。资本流向土地,在明清之前,史不绝书。但是,通过出卖土地,获得资本后用于商业经营,至明清时才见于史端;二是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明代以来,定额租制得以长足发展,至清代前期,已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土地经营权呈市场化发展趋势。正因如此形成大规模的土地交易,土地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快。
一、土地市场化趋势加快的主要表现
(一)地权市场范围的继续扩大
宋以降,封建国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私有土地的买卖日益广泛和频繁,国有土地如官田、学田亦渐次卷入交易。明清以
来,明代的官庄、屯田,清代的旗地,都突破了买卖禁令,或典或卖,以各种名目进入地权市场。宋代开始出现的族田,明清时期也卷入买卖之中。
明人国有土地有官庄、屯田、没官田、无主荒地等,上禁止买卖,但明中叶以后逐渐向私有和民田转化,并进入土地市场。官田多招人承佃,承佃既久,遂“各自以为已业,实与民田无异”。⑴虽然官田禁止买卖,但在佃权的转让过程中,形式上的承佃契约变成买卖契约,实际上也就实现了地权的转移,所谓“其更田实同鬻田,系契券则书承而已。”⑵屯田尤甚,明人马文升说:“屯地多为势家侵占,或被军士盗卖。”⑶满清庄田旗地,本来是严禁买卖的,后来也卷入了土地市场之中。针对旗地典卖的现象,康熙时曾规定:“官兵地亩,不准越旗交易;兵丁本身种地,不许全卖”。⑷实际上默认了旗地在旗内的交易,缺口一开,旗地交易势头日渐难遏,至乾隆间不得不继续放宽,“准其不计旗分,能融买卖”。⑸由于旗人家庭人口繁衍及其腐化骄奢,不事生产,开始多以保留地权,出典旗地的方式进入市场。尽管清王朝多次大规模为旗人赎回典田,但旗地之卷入土地市场,并由典而卖的趋势是难以阻遏的。乾隆四年,民典旗地就达数百万亩,典地民人至数十万户。乾隆十年,民典旗地就达数百万亩,典地民人至数十户。乾隆十年,舒泰反映“旗地之典卖者已十之五六”。⑹早在雍正年间,皇帝就指出,旗地买卖“相沿以久”。至道咸年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余顷地,除王庄田而外,沿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⑺
迅速增加的族田也成为土地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族田的形式起源于北宋范仲淹设立的苏州范氏义庄,此后向全国各地推广,至清代时进人高峰。清代族田的迅速增多,主要是通过多种形式从土地市场产生的。⑻宗族通过多种途径典买田地,不遗余力,不得典卖族内成员田房的规定,也被突破。宗族尤强调绝买地权常有专人负责,力求手续齐全。族田的出卖相对较少,朱熹《家礼》族田“不得典卖”的原则,为各地族训所恪守不渝。广东南海黄氏族田,自宋朝以来,皆为宗族永远世守管业,“不得卖与外人,亦不得招引外人居住。历来无异,例禁甚严,如敢违,即将此人永远出族”。⑼尽管如此,族田进入市场之势不可遏止,据考察,在清代广东土地买卖中,宗族是最大的买家,又是最大的卖家,而且往往是在宗族之间进行的。多因“阖族急用”,经全族人商议而出售。⑽
非族田土地交易亦受到宗族的干预,不过这种束缚渐趋松弛。地权交易的亲邻优先权,是地权市场的特殊传统习俗,唐宋官府法律与家训中就有明确规定,明清地权市场仍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刻影响和严重约束。宗族势力对地权市场的正常运转存在很强的干扰,这种非正常干扰受到交易者的抵制,官府也力图排除。随着明清土地市场的发育,这一传统习俗走向式微,至清代开始提出废除“优先购买权”。雍正三年河南巡抚田文镜针对“豫省有先尽业主邻亲之说,他姓概不敢买,任其乘机揩勒,以至穷民不得不减价相
就”,规定:“田园房产,为小民性命之依,敬非万不得已,岂肯轻弃。既有急需,应听其觅主典卖,以济燃眉。”不论何人许买,有出价者即系售主。如地主之邻,亲告争,按律治罪。雍正八年清廷规定,已经成交的田地买卖,若有人“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掯勒,希图短价者,俱照不应重律治罪。”⑾
杨国桢在(闽北土地文书选编)所收77件文书中有14件载明已先尽亲房伯叔等无力承买外,绝大部分文书声称:“共田系是自置物业”,或“其田系承父遗授物业”,或“其田系是分定之业”,因而“与亲房伯叔等各无干涉”。⑿这无异于宣告。我的田地属于自己,有自由买卖支配的权力,宗族不要横加干涉。宗族势力较强的福建尚且如此,其它地区更甚,田地买卖,都不顾这种优先权,而以买价为最高原则,谁出价最高,谁就能购得土地,无论是亲族还是外人。因此,有的宗谱谆谆告诫族人,田宅“族人互相典买,其价比外姓稍厚,不得用强轻夺。违者具告宗子,合众处分。”⒀宗族优先权的削弱,一方面说明干扰地权市场发育的非经济因素减轻,另一方面,地权交易向宗族外发展,说明地权交易的覆盖面在扩大。综上所述,明清以来,随着国有土地与族田大量涌人土地市场,以及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日益削弱,地权市场范围随之亦日趋扩大。
(二)地权与资本的相互转化
通常所见,都是资本投入到土地的单向流动,逆向运动者绝少,历代皆然,宋至明清仍未脱其窠臼。所谓“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⒁事例不胜枚举,正如陶熙《租核·推原》所说:“上至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赢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
明清时期出现了前代少有的现象,即客籍商人在外地大量购买土地。跨省际异地购买田产,在宋代仅见于大官僚,他们因履职客寓异地而购买田产。明清商人则纷纷在客居地置产,这是商业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政府曾查禁“越境买产图利占据者”,尤其是在商贩聚集、盐贾富户颇多的扬州、汉口、徽州等地,但令行不止。徽商在家乡置地数量有限,而在外乡置地则不少。晋商在外地置地也越来越多,乾隆五十年,河南连年饥馑,有田地之家纷纷变卖糊口。有的甚至把即将成熟的麦地贱价出售,以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山西等处商人“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大肆收购土地。⒂灾荒最严重的河南郑县,两年后,土著“在籍置产者,尚不及十之一二,西商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⒃嘉庆间,直隶灾荒频仍,地价狂跌,“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⒄陕南山区,流民垦荒进入一定时期后,继续涌至的客民,“有资本者买地典地,广辟山场;无资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谋生。”⒅许多商人进而定居于客籍地。
更为重要的是,相反的情形也出现,即出卖田地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商业经营。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这在宋以前就是普遍的现象,但出卖田产转化为商业资本,则直到明清才见诸史端。今存明清时期的徽州契约,此类事例就不少。刘绍泉汇集了明代天顺至嘉靖年间徽州因经商出卖田地的9份契约,⒆内有几份是因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经商,妻小在家无以度日而出卖田地者。也就是说,其中有的是因商业资本周转无着,无法寄钱回来赡家,出卖田地实际上是间接用之于商业,例如成化十五年程道容卖出1.5亩地计6两银,原因是“父程社和借银买卖无还”。另有几份契约则明确记载,出卖田地是因为“买卖无本,或买卖少本”,或“各商在外,无措”等,这显然就是将田地财产转化为商业资本。章有义所辑清代事例也是如此。⒇如乾隆七年休宁人胡景文,道光六年黟县胡氏出买田产,都是由于“店业亏空”、“客帐未清”
而将祖产变卖,偿还商业经营所欠债务。康熙二十六年休宁胡率之将自己亲手所置田业出卖与堂弟名下为业,也是“因开店缺少财本”。道光九年黟县所有析产阄书,语称“已弃己产而充店本”。
全国各地都可见此类事例,社会上有一种人,“典卖现在之产,稀图未然之益,合什伯小分为一大股”[21]这种典卖地产投资工商业,虽然被人轻蔑地称之为无赖之徒,但他们破釜沉舟,敢于走出农耕,勇冒风险去追求商业利润的行为,也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荡家破产者是其中多数人难以避免的命运。据明人张英《恒产琐言》观察:“尝见人家子弟,厌田产之生息微而缓,羡贸易之生息速而绕,至鬻产以从事,断未有不全年尽没者。余身试如此,见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张英此言明显有所夸大。既然有人出卖田地换取资金投资于工商业,正说明社会经济中出现了社会资金从土地转向商业的客观需要与可能。虽然残酷的商业竞争使许多人的梦想破灭,但商业利润以其不同于土地收益的一些特征,的确使人暴富起来。如山东濮州人刘滋世卖田20余亩还债,以所余10两白银经商,结果起家致富,20年后,“田连阡陌,家累数万金。”[22]总之,明至清前期,土地市场出现了地权与资本的相互转化,特别是地权向资本的转化,这一新情形构成了土地市场发育到高级阶段一个重要的特征。
(三)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
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宋元时期以分成制为主,明清时期则普行定额租制,到清代前期其已在全国范围内占居主导地位。在定额租制下,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经营权趋于商品化,其主要具体化为以下两种形式进入土地市场。
第一,土地经营权以押租形式进入市场。所谓押租制,就是一种佃农交纳押金才能佃种地主土地的制度,也就是地主以收取押金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制度。它标志着土地经营权的商品化、货币化。明代在个别地区开始出现了押租制,清以降,押租制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获得一定发展,其他各省亦有出现。江西押租俗称“批礼银”,有十年一换租约,重批礼银的习俗。福建称“粪土银”,广东一些地区谓之“粪质银”,镇平县自乾嘉以来,“佃户凭耕,立承耕字,以银为质,如有欠租即另招别佃,将此银抵扣所欠之租,名曰粪质银,亦曰粪尾银”。[23]在押租制下,经营权独立性增强,从而可以单独买卖。湖南有人说,“楚南俗例,凡招佃耕种,必须进庄银两,少则十余金,多则四五十金,虽宗族戚友未有佃银而能承耕者”。[24]正如江西民谚所说,“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25]浙江临海县,租田时将佃价交于田主。佃户缺乏银钱时,可把佃田出让他人承佃,不拘年月,原佃者可以赎回佃权。同时,如果田主将田地出卖与人,原佃户耕种还租仍旧,这叫做“卖田不卖佃”。[26]
祭田一类的土地,自宋代以来,或由政府规定,或由宗族规定,一般是“永禁买卖”。到了清代押租制流行后,这类不能买卖的土地,其经营权也以收取押租形式进入市场。乾隆间,浙江常山县江姓祀田是佃农“须先拿出顶钱有祠,方许佃种”。有些地方祭田是由族人轮流值年耕作。轮值的人也可将田地经营权出佃,收取押租。乾隆间,江西上绕县王姓祀田即由轮值人出佃,“收取脱肩钱”。有的祭田甚至是可由佃户自由顶批,乾隆间,广东潮阳县林姓族内祭田三易佃户均系自行转抵,“并未经由田主批佃”。
第二,田面(皮)权进入土地市场。清代时,永佃制已流行于江南等地。所谓永佃权,实际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并彼此完全独立。在这种租佃制度下,地主的土地所有仅发生分解,分割为田底(骨)和田面
(皮)。佃农购买所得经营权与田主保留的所有权,各地有专门的对应语,如:田底一田面;田骨一田皮、根田一面田;大苗一小苗;大租一小租;无论何种称谓,其内含均大同小异,都是说,经营权的进一步发展,分解为占有权与使用权,并各自以独立的姿态进入市场。
由于佃农投入工本垦辟、改良土地、或出资购买,地主遂用田面(皮)权形式,将土地的经营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授予或转让与佃农。佃农完全取得对土地经营权的独立支配,而且田主对土地经营没有干涉与支配权力,土地所有者出卖土地时,亦无权出卖经营权。而佃农对于经营权的独立支配,表现于可以单独出卖经营权,也可以将经营权出租,并获取收益。在江西宁都,“佃农承凭主田,不自耕,借与他人耕种者,谓之借耕。借耕之人,既交田主骨租,又交佃人皮租。”如50亩之田,获谷200石,以50石为骨租,以70石为皮租,借耕之人自得80石。[27]福建汀州一带,“田主收租而纳粮者,谓之田骨,田主之外又有收租而无纳粮者,谓之田皮。是以民、官田亩,类皆一田二主。如系近水腴田,则皮田价反贵于田骨,争相让渡佃种,可享无赋之租”。[28]由于存在高额的级差地租,田面的价格往往高于田底的让渡价格。[29]江西建昌府,乾隆时,“男皆主佃两业,佃人转卖承耕,田主无能过问”。永佃田,“此主只管收佃,凭耕转项,权由佃忘户,地主不得过问”。[30]同省宁都县,乾隆《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载:“佃户之出银买耕,犹夫田主之出银买田,上流下接,不便禁革。”在苏州,陶熙:《租核.重租论》说:“俗有田底、田面之称。田面者,佃家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丰。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已不与”。福建省建阳县,陈盛韶《问俗录》谓:“有一田而卖与两户,一田骨、一田皮者;有骨、皮俱卖者,田皮买卖并不与问骨主。骨系管业,皮亦系管业;骨有祖遗,皮亦有祖遗。”甚至族田轮值权也可以交易。族田所有权归宗族,而宗族成员拥有轮值年的经营权。也就是,在轮值年份里,成员拥有族田经营权及其收益。此时,有的成员将自己的轮值年经营权抵财富。轮值年一过,则无权经营,也无权抵押。[31]这种轮值年经营权出当的形成,成为地权市场组成部分。总之,土地产权进入市场,土地经营权一经商品化,必然会使土地市场的土地交易量成倍的增长,正惟如此,其构成了土地市场发育到高级阶段的又一重要特征。
(一)商品的与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部门中商业性农业得以长足发展,即农业商品化程度呈增强之势。
当时几乎全国各地都种植棉花,而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因有大量外输而成为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迟的奉天,也已变成棉花的外输地区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棉花生产的增长,造成棉花市场的活跃。河北保定一带当棉花“秋获,场圃毕登,野则京坻盈望,户则苇箔分罗,擘孥如云,堆光若雪”。[32]‘每当新棉人市,远商翁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市以敛之,懋迁者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孥纷如”,[33]勾画出乡村棉花市场活跃的情况。除此季节性的乡村市场外,上海等地不仅出现了经常性的“花行”、“花市”,还出现了专门的广东、福建商人收买“花市”的“洋行”。[34]
烟的吸食和种植的传人,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末清初种植和吸食才日益普遍。烟草的种植在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占着巨大的比重。烟叶的吸食与种植最早的福建,清初即已是“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35]陕南汉中、城固一带,“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
夏曰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36]另外以烟著名的地方如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都有同样的情况。济宁六家烟场的烟叶贸易,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37]汉中也为此而“岁靡数千万金”。[38]这均可见种植数量的巨大。
茶叶不仅为我国广大人民长期以来的重要饮料之一,而且也是一种主要的输出品。尤其是十八世纪茶叶外输数量的迅速增加,更刺激了茶的种植推广。茶的产地遍及秦岭淮水以南,尤以皖、浙、闽、湘产量最多,种植最盛。人民多以茶为生。如安徽霍山“近县百里皆种花,民惟赖茶以生”。福建武夷山下居民“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产数十万斤”;浙江于潜则“乡人大半赖以(茶)以资生”;“湖南攸县人以茶花为业”;巴陵亦有经营茶园以谋利者。
在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在地主和富商集中的和商业城市附近,就已出现了专门城市人口服务的蔬菜种植业,果树栽培业和花卉栽培业的经营。随着手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这种经营也日益发展和专业化。这些生产事业的经营者,有的随城市季节消费的不同,而有地变更自己的营业。如苏州,“虎邱人……三四月早卖时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后时者价二三倍。五月五日卖花胜,二伏卖冰,七夕卖巧果。皆按节而出,喧于城市。大抵吴人东利好便,多无宿藏,悉资于市也”。[39]有的形成为主要供给某城市的郊区菜园、果园和花园,有的则成为以较广大区域或以全国为市场的专业性的蔬菜、花卉和果树种植业。总之,经济作物的种植,标志着种植业内涵已发生变化。棉农、烟农、茶农、菜农和果农等专门名称的出现,表明已出现了获利率较高的农业专门化商品性生产领域。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生产粮食的基地,土地周转、买卖的频率相对较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土地日益成为人们追逐求利的对象,因而土地的周转和土地买卖亦日益加快。在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之下,农桑、衣食的简单再生产对土地的要求较为单一,土地价格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土壤的自然丰度;相反地,在农业商品化生产条件下,除了考虑土壤的自然丰度外,方位、、农产品价格成为决定地价的重要因素。如附郭之田受到重视;烟田一亩产值“敌田十亩”;棉田产值“五谷不及其半”;种兰制靛“利倍于种谷”等。在许多地区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还有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农、林、牧、副、渔各业不同的生产环境、条件要求,把更多的、各有其适应性的土地带人土地市场,肥硗与否已不成为决定性因素。[40]正惟如此,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强,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加速了土地市场化发展趋势。
(二)地权转移的高频率与零细化
地权转让的主体,就社会经济单元而言,不外乎个体小农家庭,以及包括商人在内的地主大户,他们的经济特征与土地买卖行为,决定了地权交易的主旋律和土地市场发育的状况。
宋代以来,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渐趋成熟,小农对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与占有能力增强。两宋主户在总户数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主户中占绝大数的小农家庭数量增加,无地而佃耕的客户中,也有少数能够通过购买土地上升为主户。明清时期小农对自有土地仍多能世世相守。如乾隆年间,安徽霍山县,“中人以下威自食其力,薄田数十亩,往往子孙世守之,佃田耕种者仅二三。”陕西三原县的农家,对不足十亩的田地,“世世守之,可资俯仰”。[41]
应该强调的是,小农对小块土地的占有,正是在地权不断典当、买卖之中实现的。宋代以来,小农家庭经营与市场已形成密切的
内在关联,这种特征使其田地不能不经常出入市场。农民出卖田地,并不是像他出售剩余粮食一样作为商品来出售,而是在其农业再生产或人口再生产出现中断与危机时,只有通过出卖田地换取其他需求的满足,或者说,通过地权的转让来换取购买能力,才能恢复和延续其再生产。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揭示道:“盖人之卖产,或以阙食,或以负债,或以疾病,死亡,婚嫁,争讼。”司马光也说:“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于婚姻丧葬之急”。[42]清同治《新宁县志》载:“民间不尚积蓄,秋成后,计食若干石,余皆陆续粜去。次年将及收,则旧谷颗粒不存,名曰扫以待新。所得俗价即以市田。富室亦然,鲜有盖藏”。地主将自己的积蓄寓于田地之中,而农民也将自己的小块田地作为自己潜在的积蓄形态,当再生产出现危机或生活无着时,就只好变卖田地以资补救。章有义统计明清徽州休宁朱姓置产薄中74宗土地买卖原因中,为了维持平时情况下必要生活消费需要,正常的收入来源无以为继,只能出卖土地来补偿,即所谓“缺用”、“正用”、“需用”者,其中家有意外变故或遇婚嫁庆典,“费用无措”,因“急用”而卖田者,共占总数的78%;应付赋之征,国课无措,“钱粮紧急,无处措办”者,占总数的12%。[43]
地主所有的土地,则在诸子均分与土地买卖之下,由集中而分割,地权集中的势头受到遏制,地权的分散与转移因此而加强。地主大家庭特别忌讳田产分割,袁采在《袁氏世范》告诫子孙说:“若均给田产,彼此为己分所有,必邀求尊长,立契典卖。典卖既尽,窥觑他房,从中婪取,必至兴讼。使贤子贤孙,被其扰害,同于破荡,以至败家。”但子孙分家自立,对于多数大家庭而言难以避免,从而田地分割也在必然之中。清人李调元《卖田说》述四川一个地主家庭诸子均分的情形:某家曾有田地不下千亩,生子五人,均分后每人各有田二百亩,田之所人,不敌所出,于是出卖田地,佃耕为生。阚昌言《崇俭记》也说:“不少家庭,因为祖宗勤俭积累,遗有产业,但传至子孙,常转瞬立尽”。可见,地主阶级固然是土地兼并者,但同是又是土地的出卖者。所谓“有田者或自有而之无,无田者或自无而之有”。[44]
小农家庭地主家庭纷纷卷入田地买卖,说明地权市场广泛而普通,他们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造成了地权交易的零细化。明代安徽休西胡玄应家的地契抄件载明,从隆庆元年到崇祯十年(公元1567—1637年)70年间,胡家共买进土地110笔,其中绝大多数是几分地以至几厘地,1亩以上的只有9笔,最大的l笔不过11.9亩,这110笔合计纳税亩数仅有44.875亩,平均每次交易O.4亩,[45]足见交易是零星进行的。清代章邱县太和堂李家,从乾隆二十六年到咸丰十年整100间共买进土地57笔,计260.38亩,平均每笔4.5亩,最大的1笔不过11.6亩。[46]族田也是如此,据《肖山朱家坛朱氏宗谱》的记载,萧山米氏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咸丰九年增置的32处田地,每次增置绝大部分都是几分或一两亩地,最少的仅半分,最多的只有3.8亩。《练西黄氏宗谱》卷13记载,江苏黄氏宗族在喜定、宝山、昆山拥有616亩多处田地,各县80%一90%以上都是三四亩以下的小块的田地,族田的零星分布,表明是通过零碎购买而得。大面积的地权转让也不时可见,一次交易就达几十亩、几百亩乃至成千上万亩,大笔土地的购买者主要是一些权势豪门,往往是运用经济外强制干扰田地市场的正常运转才达致交易的。[47]就土地市场整体情形而言,多零细化实际上又是地权交易频繁的表现形式。地权高频率转换,在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流动与更替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宋人《袁氏世范》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清人所谓“人之
贫富不定,则田之去来无常。”[48]宋人谢逸所见四十年间的变化:“乡间之间,曩之富者贫,今之富者,曩之贫者也。”[49]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今不须广论久远,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势?”小农决不只是被兼并的对象,他们有可能通过艰难积蓄购买田产上升为富农地主。甚至出现“再传而后,主佃易势”的转化。宋代地权转移的速度,辛稼轩词《最高楼》谓之“千年田换八百主”。明清时期地权转移的速度有增无减。以最突出的江南地区为例,苏州俗有“百年田地转三家”之谚,到清嘉道之际,更出现地权“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的情形。”[50]
地权转移的高频率,意味着农业的自然经济色彩的渐褪,商品经济色彩的渐浓;土地买卖愈频繁,土地畸零现象就愈突出。相反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占有在空间上就易于连片。地权转移的零细化,是经济规律作用于地权市场的表现,特权、法权等非经济因素在地权转移过程中的干涉,强制作用逐渐降低,土地市场发育日臻成熟,故此,我们认为,地权转移的高频率与零细化为土地市场化趋势加快的又一重要原因。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
[2]万历《应天府志》卷19。
[3]《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 。
[4]《八旗通地初集》卷18。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8。
[6]舒泰:《复原产筹新垦疏》,载《清朝经世文编》卷35
[7]光绪《畿辅通志》卷95。
[8]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光绪《南海学正黄氏家谱》卷11,引乾隆十一年《禁约碑》。
[10]赵令扬、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的与土地问题》,载叶显思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向,1992年版。
[1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12]《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2期。
[13]《桐城赵氏宗谱》光绪九年四修书,卷着,家约。
[14]《清代户部档钞》,乾隆五年四月胡定奏疏。
[15]《清高宗实录》卷1255。
L16]孙王行:《归田稿文》卷6。
[17]《清仁宗实录》卷310。
[18]道光《宁陕厅志》卷1。
[19]刘绍泉:《试论明代徽州土了买卖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4期。
[20]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21]《清高宗实录》卷213。
[22]康熙《濮州志》卷4。
[23]黄钊《石窟一征》卷5。
[24]《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9。
[25]《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宁都仁义乡横塘塍茶亭内碑记》。
[26]《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5页。
[27]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11。
[28]《福建省例》卷15。
[29]方行:《清代前期封建地租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2期。
[30]陈道:《江西新城田租税》,载《切问斋文钞》卷15。又载《皇朝经世文编》卷32。
[31]彭文字:《清代福建田产典当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3期。
[32]《棉花图》《拣晒》。
[33]《棉花图》《收贩》。
[34]《褚花木棉谱》。
[35]《皇朝经世文编补》卷36《郭起无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36]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安康府食贷志论三》。
[37]《安吴四种》卷6。
[38]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安康府食贷志论三》。
[39]道光《苏州府志》卷2《风俗》。
[40]樊志民:《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研究》。
[41]光绪《霍山县志》卷2;乾隆《三原县志》卷8。
[42]《宋会要·食货)。
[43]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
[44]康熙《孝感县志》卷12。
[4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46]景苏、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1959年版,第51~52页。
[47]李文治:《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载《经济生活》,1956,1期。
[48]李光坡:《答曾邑候丁米均派书》,载《清朝经世文编》卷30。
[49]谢逸:《溪堂集》卷9《黄君墓志铭》。
[50]钱泳:《履园丛话》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