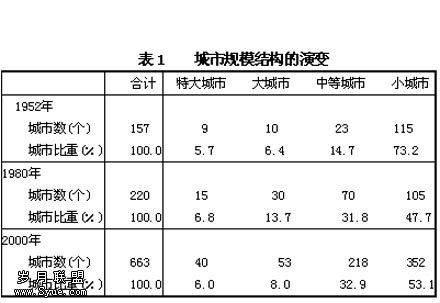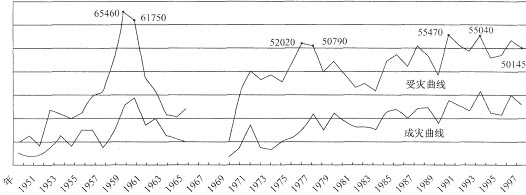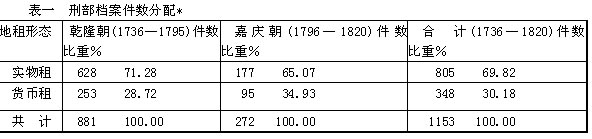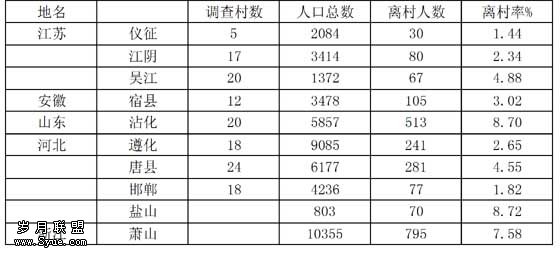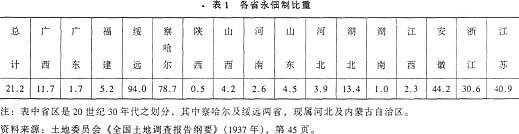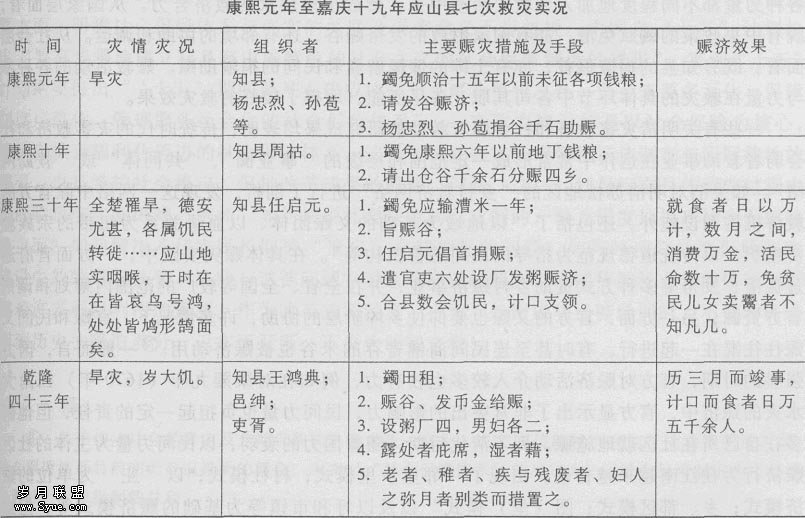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变迁
[关键词]生活方式;近代观念;上海;社会风尚
[摘 要]晚清时期,上海的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出现了如洋货流行、从商之风、尊卑失序、女子走上社会、追求享乐等新社会风尚,导致传统伦理衰坏,同时也孕育产生了近代市场意识、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功利主义及肯定人欲、自由的近代伦理观念.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变动是引起近代生活伦理观念变迁的中介和启动力量。
Changes in Life Style and Ideas in Late Qing in Shanghai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China) Key Words: life style; modern ideas; Shanghai; social customs Abstract: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Shanghai in late Qing caused changes in people's life style and ideas. Foreing commodities were popular, people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old order of high and low was broken, women began to enter social life, people longed for ease and pleasure. These resulted in the breakdown of tradition- al eth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arket consciousness, the sense of equality, the pursuit of freedom and satisfaction of desires.
引 论
鸦片战争后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积聚,到了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兴起,形成了近代以来思想观念变革的一个高峰,维新人士提出的民主、近代工商、社会平等、肯定人的自由权利和本性欲求等一系列新思想,标志着近代观念的初步形成。关于这些近代观念形成的源流,以往史家曾作过不少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危机和日本仿效西方而崛起的刺激下,由原来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确实都是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但这只是从思想层面就维新精英人物思想的发展流脉和谱系来说明其源流。实则,维新思想不仅从思想层面具有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一些内容还与社会普遍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一般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比如在生活方面,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社会价值方面,从崇尚纲常礼仪到崇尚富强;社会关系方面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到社会平等观念;人性价值方面从崇理节欲到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等等。这些关涉社会一般观念转变的内容,仅靠对精英言本的解读,仅从思想层面来说明其源流是不够的,由于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方式,因而还需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层面来探索其缘由,还需考察一般社会观念赖以存在的社会民众生活状况。
人们的社会观念,来源于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决定人们观念的基本元素。在化最早发源的西方,近代化首先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动为启动力的,科技革命引起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又带动人们生活方式变化,进而引起社会观念的转变,形成适应工业化、市场化的社会观念系统。而中国的情形则与此不同,中国是由被迫通商而被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市场,进而引起经济近代化变革的,因而不是首先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是由中外贸易引起商业化、城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启动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因而生活方式的变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回顾鸦片战争后至维新运动前这五十多年间,由通商贸易及与西方文明的交汇而产生商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变动最为明显的地区,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南沿海最早开口通商的城市,在这些地区也首先出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变迁,同时近代报刊和市民舆论等也初步形成了人们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公共舆论空间,反映了民间观念的变化。因而本文拟就晚清上海为个案,考察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方面曾有研究者作过一些探讨,指出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社会心态变化及民主观念、开放性、近代消费观念的关系等等。[1][2]但这些还只是社会观念的一些元素,还未构成近代社会观念系统,而且对于这种观念如何转变的机制尚未有充分的解释。
本文就是基于上述问题,拟通过对晚清上海出现的一些新社会风尚,以及《申报》上汇聚各地士商人士对于这些现象的议论进行分析,以求对上海所代表的通商城市人们生活方式变动与社会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一番考察,从而对于近代观念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内在源流及转换机制提出一种解释。
一 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生活方式变动
上海自1843年开口通商后,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商业繁盛、华洋混居、五方杂处、商贾云集、人口流动等变动,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人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环境已大不一样。
首先,人们的经济生活环境变化了。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商业繁荣,西货输入,百货流通,商贾云集,商业贸易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中心,使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和生活都日益与市场相联系,日益商业化,与以往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家庭经济方式已有很大不同。
其次,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人口的涌人及人口流动频繁,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已不同于传统伦理所依托的聚族而居的村社结构,单身人口及小家庭比例上升,社会阶层的构成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如商人地位上升,而以往居于特权地位的土宦乡绅的势力减弱,传统伦理所依赖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
再次,政治及社会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西人势力的介入,成为中国官府之外的又一权势力量,对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制约性,使以往中国官府一统天下的控制力减弱。特别是华洋混居、由西人管理的租界地区,不再直接受中国官府控制,使以往传统伦理最有力的支撑势力——官府的权力控制和社会制度性控制力减弱,人们的自由空间扩大,并趋于形成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最后,人们的文化交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在聚族而居的村社生活环境下,人们的言论行动、行为规范及价值观念等要受到族长、乡绅等家族村社权威的控制,受到村社亲族群体的舆论监督。而在上海,这种文化控制机制也伴随着宗族村社结构的松弛而日渐丧失,以单身人口和小家庭为主的市民结构,市场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独立、平等、自由。同时,近代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也形成了不受官方和上层直接控制的民间公共舆论空间,使人们能够更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并具有比以往更强的民间传播、呼应等效应。
在通商后的上海,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生活环境所发生的上述这些变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近代商业化、城市化、社会化趋向。人们在这样的新生活环境下,要维持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就必须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求适应,因而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新生活方式一旦出现,并使人们从中得到益处,便吸引其他人争相仿效,以致流行成风,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这在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表现。
例如,在物质生活方面,随着洋器洋货大量输入,人们生活的市场化,洋货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类制造精巧、五光十色的洋货如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洋布、洋油、洋皂、洋针、火柴等,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或为了新奇,或为了炫耀,或为了方便利用,或作为馈赠礼品而购买使用,特别是一些物美价廉的生活日用洋货,更引起人们的争相购用,成为人们的日用品,人们也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流行的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祗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3]长期在上海生活的文人买办郑观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一口气列举了西国输入的食物、用物、玩好等日用洋货计57种,指出这些洋货“皆畅行各口,销人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4][P586—589]可见在上海开埠后二三十年间,洋货流行已日渐成风。
在社会生活方面,商业的繁盛并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使商业成为最能赚钱致富因而最适宜生存的行业,商人发财致富,地位上升,成为人们所羡慕的对象,因而形成人争趋商之风。西人人居、人口聚集、商旅往来、五方杂处等城市化和流动性的居住形式,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往的一些社会关系规则和行为规范效力减弱,因而以往所重视的血缘亲族关系、诚信、友谊等成分趋于淡化,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更看重人是否有钱,是否有赚钱的能力及赚钱的机会与资源,而不再看重以往所重的社会身分、出身门弟、官衔名分,以及血缘亲情、师友故旧等关系,而出现了贵贱颠倒、尊卑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在此风气之下,人们交友不问出身,不念故旧,全以衣冠取人:“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遂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5]同时,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变化。由于大量乡村妇女流人城市,为了生存而走出家庭,出外作女佣、女工、娼妓、艺人、跑堂等以谋生,因而出现妇女走上社会做工之风。离开家庭流人城市的单身男女增多及生活方式的市场化,使家庭关系松弛,社会交往空间增大,造成男女自由交际之风及姘居之风。
在消费消闲和文化生活方面,随着人们商业化的生活方式,闲暇时间增多,社会交往需求增多;收入的货币化方便了人们的消费,人们的娱乐休闲需求增多,各种消闲娱乐业如茶楼、酒馆、戏馆、说书馆、烟馆、妓馆、赌馆等日益兴盛,形成了发达的大众化公共消闲娱乐空间。于是,人们无论男女,不拘贫富,都乐于上这些消闲娱乐场所去消遣,而形成冶游之风。而商人的富有,特别是一些暴富起来的新富,为了显示自己的成功和财富,在消费生活中往往逞奢摆富、一掷千金,形成炫耀式消费,在其影响下,人们相互仿效,出现了消费上的崇奢之风和逞富之风。当时报刊诗文中便多有对这种时风的描述:如在酒楼里常可看到“万钱不惜宴嘉宾”[6]、“一筵破费中人产”[7]的豪宴,在妓馆常有“不惜千金付阿娇”[7]的嫖客。人们的衣着装饰也是争趋华丽、追逐时尚,“斗丽争华者层见叠出”[8]。90年代初《申报》有文记述这种奢靡之风的源起道:“风俗之靡不自今日始矣,服色之奢亦不自今日始矣。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近今风俗之侈靡日甚一日,较之三十年前已有霄壤之别。”[9]在上海率先兴起这种奢靡夸富之风,随后便浸染至内地,遂形成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城市商业化生活形成市民文化氛围,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生活规则的变化,也使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松弛,传统伦理意识淡化,出现了社会心理上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要求,形成社会风气上的逐利之风、逞欲之风及追求享乐之风。
这些与以往传统礼俗大为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被人们相互仿效,流行成风,表明人们认为这些新生活方式更适合于变化了的新生活环境中求生存的需要,因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仿效,遂成风尚。由此可见,伴随商业的发展,上海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商业化、城市化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生活需要,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出现了上述这些与商业化、城市化相应的新社会风尚。[10]
三 生活方式变动催生新社会观念
新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流行成风,形成人争趋之的社会风尚,反映了人们选择这种新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人们适应生活需要的一种选择,有其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一些站在现实立场、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人们,也开始面对和正视这种合理性,不再拘泥于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而试图寻找新的伦理依据,来说明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新伦理就这样萌生了。
如在生活方面,对于洋货流行,有人提出人们喜新厌故、喜欢奇巧之物,这是人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洋货流行也是不可能扼止的。他们不再拘泥于道德上的评判,而是从商业化的市场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由于人的喜新好异的本性,洋货流行就是不可能扼止的,这表明洋货具有广大的市场,这是一种利源。人们由“利源”的认识,进而得出了从利源中获取利润的“利权”观念,西人就是靠掌握这种利权而赚钱致富的。在人们的意识里,本来的“利源”,自然应当由中国人获取利益,即“利权”本应属于中国人,而洋货流行,使洋人大获利润,“利权”落人洋人之手,这是不应该的,也是造成中国钱财外流的重要原因。由此人们得出结论,提出中国人应当起而仿行西法,自造洋货,自己的工商业,以自己的优势去与西人争夺市场,争夺“利源”,“分西人之利”,以夺回“利权”。如有人所说:“欲禁民人不用洋货,势所不能,则莫如中国自行筹赀,逐一仿造,庶几将中国之货易中国之钱,富者可便于购求,贫者更开无数谋生之路。按之和约亦所准行。而来华之洋货日稀,即银钱流出日少矣。”[3]到七八十年代,上海社会舆论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仿造洋货,去占领洋货市场,与洋人“分利”,与洋人展开“商战”,直至夺回“利权”,这才是挽救国家贫弱的富强之道,从而形成了中国以求富强为中心的近代工商业观念,即重商主义。
在社会生活方面,对于从商之风及商人地位的上升,以及贵贱尊卑失序现象,也有人开始不再拘于传统身份等级观念,而以务实的态度,更多地从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对各阶层的评价应当从其社会实际作用的角度来看待,提出以实际作用为基准的评判标准,显示了一种与传统身分主义取向不同的能力及功利主义取向。例如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有人便抛开以往基于道德主义和农本主义的轻商、贱商观念,开始以现实的态度来重新审视。特别是70年代以后,振兴工商以求富强已成为社会上越来越多人认同的口号,在这种尚富强的新社会价值观念确立之后,一些面对现实的人们也开始从兴商强国的角度,以富强的功利价值标准,来看待商人对社会的作用,对于商人予以重新定位。例如,在1872年《申报》上一次关于士商地位的争论中,有人就针对尊士贱商的传统观念,提出现在的买办、商人发财之后,“多有发达,体恤时艰,捐助军饷者,不知凡几”。论者认为,商人发了财以后,拿出钱助饷赈灾,对于社会有实际的用处,远胜于那些只知道舞文弄墨空言无补的文入学士。“其家虽不能致君泽民,而胜乎舞文弄墨、颠倒是非者相去几何?”[13]有人更进而提出,对于社会各业之人的社会地位,不应当只是以传统的身分贵贱作评判的标准,而应当以其对于社会的实际作用来衡量,“夫人类各有分,如士、农、工、贾是也。欲较量其上下,则以其所行所为之大小,子(仔)细而求之”。论者认为,依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商人的社会作用则“更为大矣”。这是因为商人对于现实国家和社会需要来说功用最大,“夫西人通商之事,于国计为大事”,买办商人们对于通商发挥的作用最大,“奏效于此役也,功力莫大焉”,所以,“即或嘉之过分不亦可乎?”这位论者甚至还进而说,如天下之人,都能像广东人那样乐于作买办商人,对于通商这一国计大事“大奏功效,实中国之大幸矣!”这种看法已经完全抛弃了贱商观念,而是明确地以“国计”、通商、“富强”为评判标准,因而对商人的作用给予这样高的评价。以这种新价值标准来衡量,与商人对国计的“大奏功效”相比,以往一贯推崇的士人的作用就黯然失色了,况且当时士人阶层已经充满了腐朽之气,盛行逐利之风,所以这位论者说:相对于商人于国计大事“功莫大焉”,士人的作用反而不如,“士人有高有低,以其所行所为,尚有不如商人者”[14]。这种观点反映了人们对于商人的评价,与以往的重道德相比,而更加注重实用功利性,开始从国家富强的角度来看待商人的作用,对商人的社会作用给予积极的肯定。这种尚富强、重功利的新社会价值观,使商人赚钱求利这种以往被传统道德否定的东西,在新价值观下有了新的道德基础。以这种新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从商赚钱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与洋人争利有益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士人的作用显然比不上商人。这种“商人有功”说,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在对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已开始萌生重功利、重能力的新价值观念。
对于女性社会角色和男女地位关系的认识,也随着妇女走上社会独立谋生的风气而有所变化。一些站在同情下层人民和妇女生活立场的人,认为由于贫穷、灾荒和战乱,下层小民生计困难,贫穷妇女离乡人城,为佣、为妓、做工以谋食自养或养家,这是小民的生计之路,如禁止之,又无他业安置,则是断其活路,因而妇女出外做工是理所不应禁,也是势所不能禁的。如对于舆论一直呼吁禁娼,有人就指出,欲禁娼必须考虑这些人的生计出路,有他业以安置之,否则势在难行:“欲禁一业必须筹及位置此业诸人之处,令其有业可改,而后方能望此业之不复兴,吾禁令方能久行也。……即如娼妓一业,令其改业,何业可改?……兹禁其女为娼,必至驱其男为盗矣。此业之人又属不少,在上者纵能博施济众,谅亦无法以位置之也。”所以认为若无他业以安置,只是一味下令禁娼,是不顾小民生计、不切实际的迂腐道学之论:“道学居官禁娼,将置娼于何所?何以为生?”[15]“妓馆一禁,因之失业者不少矣。”[16]对于取缔烟馆女跑堂一事,有人指出,此业已成为许多贫家女子赖以为生的一个职业,一旦取缔,将使这些女子失业而陷于饥寒,“千百辈之衣食此若藉,一禁止忍其饥以死乎?”[17]对于茶栈、丝厂等处招用女工一事,也有人指出,这是使贫穷人家妇女“得一项出息”[18]“女工而亦藉通商之故,而得以自求口实”,认为这是“利于中国人民者”[19],不应当禁止。也就是说,妇女走上社会作工谋生,“自求口实”,是有益于小民家庭生计的,因此是应当允许其存在的。
妇女离乡人城以后,离开了土地,也脱却了依附家庭、依附男人的经济纽带,她们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做工谋生,自求口实,表明女子可以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自食其力,独立生存。这是妇女生产生活方式的一种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使得一些人开始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妇女的社会作用和家庭角色,反省传统伦理男外女内的规范对于妇女的束缚作用,从而提出了男女平等,女子与男子应并立并用的观念。如有论者根据《易经》的阴阳说,批评以往人们由“扶阳抑阴”之说论证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这一传统观念,而根据阴阳“两象并蓄”、“两德互用”理论,提出男女应当“并重、并用、并生、并育”。[20]有论者就传统贱女及女德观念对于妇女的歧视,以及男外女内模式对于妇女的束缚压迫发出不平之鸣:“今日为女子者,且自叹人生之不幸,事事退让,不敢与男子并立,以为男子治外,女子治内,酒食是议,阃限不出,暇则治女红,勤洒扫,如是不愧为妇人,若留心世务,娱志诗书,即为越分。”论者认为,正是由于女子被男外女内的传统伦理所歧视和束缚,不能与男子并立,使得她们的才智能力受到压抑,“坐使聪明伶俐之才屈于巾栉箕帚间,终其身以死,不可惜哉!”论者为中国女子发出悲呼道:“呜呼!人禀气质而生,为男为女因乎自然之化,而二千余年间之女子有此奇冤无人昭雪,试为一言其理,不几令普天下女子一齐痛哭哉!”[20]由妇女走上社会独立谋生的生活现实,以及男女并重观念,有人进而开始思考妇女走上社会与男子并立并用的可能性,以及对于妇女家庭角色的意义。如有论者从天地生人、男女本性相同的朴素观念出发,认为“妇女之灵性与男子同”,只是由于无教无学,才使其聪明才智被湮没,被弃之于无用之地,而这不符合天地生人、皆有所用的本意,应当使女子与男子并学并用。[21]这一时期人们提倡兴女学的议论增多,主张应当使女子和男子一样读书为学,学成后可以发挥与男子同样的社会作用。所以有人批评传统对于妇女家庭角色的规范是不合理的,“若徒以工刺绣、司酒食为能,则失之远矣”[21]。这种主张男女并立并用,支持妇女走上社会就业,发挥聪明才智的观念,是在妇女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就业这种生活方式变动的现实基础上产生的男女乎等观念,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条件。
在消闲消费和文化生活方面,伴随着崇奢享乐之风,冶游纵欲之风,人们对于宋明以来家所提倡的“崇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礼法越来越疏离,在社会舆论中虽然仍充斥着一些迂腐文人的理学道德说教,对于上述不合礼教的新风一片谴责之声,而且往往一呼百应,表明传统伦理仍占社会舆论的主流地位,但是这些新风的流行,已表明现实生活中这些新生活方式已是众所趋之、不可扼止。因而,在民间舆论中也开始出现肯定人欲、自由,主张适应人性人情的新伦理要求。例如这一时期上海报刊上就屡屡有人公开提出“劝人行乐”,肯定人对于享乐的追求。他们认为如今上海娱乐业发达,有钱人多,挣钱的机会多,是古往今来天下最享乐的地方,生活在上海的人们不应当只为赚钱辛苦,而应当享受这些乐趣。如有人说:“今天下最乐之境莫如上海矣,天下最乐之人亦莫如居上海者矣。”[22]虽然享乐观念在中国自古即有,源于中国“乐生”的传统人生观,但这一时期人们的享乐观念,因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环境而其内涵已有所不同。如这时期人们重提古已有之的“适度享乐”观念,以往这种“适度”的内涵,一是指适合自己的身分,一是指适合自己的财力,并且把这种“适度享乐”主要看作是一种道德修养。而这一时期的适度享乐观念中,以往多被重视的道德和身分观念趋于淡化,人们提出适度享乐,更多强调的是过度享乐会使人破财败家、陷于贫困,体现了人们在享乐问题上,更看重享乐对于人们的实际利害,即重功利的务实态度,这无疑是商业化濡染的结果.在关于享乐的议论中,人们对于人的嗜欲享乐大多比较宽容,给予一定的肯定。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如何享乐,特别是主张中下层人也应当适度地享乐,而强调只有那些超过自己的财力,会致人破财败家的享乐才是“过度”的、有害的,予以明确的批评。这种肯定享乐和量财享乐的观念,反映了商业化生活变动下,商人和市民阶层的享乐观及功利观。
由上可见,人们适应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而采纳新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在传统伦理不再能规范人们新的生活需求之时,一些最早面对现实生活的人们,便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基于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而寻求建构新的价值观念,由此孕育形成了发展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以及生活的世俗化,这些都是与近代工商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近代化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的时代伦理观念。
四 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的内在资源
上海新社会风尚所反映的生活方式的变动,导致旧伦理的衰败,新社会观念的萌生。然而,这种新旧观念的更替却并不是一种断裂和完全相背,其间虽有价值取向的转变,但就其内在涵义来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这是因为,人们生活方式虽然依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支配这种生活方式变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却有一定的连续性。晚清上海出现的这些新生活方式及其内含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以往社会推崇的主流伦理中几乎看不到,但却在非主流的民间世俗生活中大多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在民间实际生活和由此形成的民间生活伦理中一直有延续。
例如,对于洋货流行所反映的人们的“好异喜新”及物欲本性,以往虽然在提倡节俭、务实的正统伦理中是被贬斥的,但是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也一直有随分适度、量人为出,即符合自己身分、财力的物质消费观念及生活方式。[23](p203)一方面这是对人的物欲本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对物质生活水平标志一定的身分这种附加社会值的肯定。只是在上海商业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条件下,购用洋货标志身分和财力的附加社会值更高,人们这种观念更为膨胀,因而争相购用,相习成风。而一些既物美且价廉的日用洋货如洋布、火柴、洋油、洋钉等广受人们欢迎,更是人们历来沿袭的“利用取廉”实用消费观的延续,是市场价值交换法则的扩展,因而,洋货流行的风尚,是随分适度、利用取廉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洋货涌人、市场化环境下的延续和扩展,正是这些构成了洋货的需求市场,使人们产生了“利源”即洋货市场观念,进而形成了仿造洋货、与洋人争利的近代工商观念。
从商之风及由商人地位的上升而引起的贵贱失序之风、以钱衡人之风,也有民间传统生活方式的渊源。虽然历来正统伦理提倡贱商、轻商,但自汉唐以迄明清,在民间实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趋商、慕商的传统,因而,凡是经过了一段安定升平时期,就会出现人争趋商、商人大增的现象,这在历代史籍中多有记载。[24](p180—184)晚清上海商业化的发展,为人们从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条件,因而吸引人们纷纷从商。商人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地位上升,自然引起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互关系的调整,因而出现与士阶层地位关系的升降更替,并使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规则——即以钱衡量人的价值,取代以往身分价值而上升为社会普遍性的交往规则,从而形成了能力功利主义的近代社会平等观念。
女子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就业,虽然是上海商业化引起的新生活方式,但也有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源流。传统小农下男女社会角色是一种“男耕女织”、“男外女内”的模式,由此形成了一套束缚妇女的伦理。但是在一般中下之家,女主内并非不事劳作,而是需要从事纺织、副业、助农活等生产活动。实则妇女与男子一样承担家庭生产者角色,只是由于男子垄断土地,使妇女被迫对男子及其家庭处于人身依附性地位。而通商后妇女人城,因为失去了土地而只能到市场上去靠出卖劳动或色艺来换取衣食。她们的生产者角色并没有变化,只是劳动场所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市场,从这一点来说,她们这种出外就业的生活方式,也是传统“主内”——即在家庭内劳动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但是,正是脱离了土地、出外就业这种新方式,割断了妇女依附于男子的绳索,使她们像这里的男子一样,成了在市场上交换劳动的自由身,因而她们便产生了要与男子平等的要求,她们不仅要像男子一样到社会上去闯荡挣钱,也要像男子一样享受消闲生活,一些同情她们并代表她们愿望的人士更公开提出了男女应当平等,女子与男子并立、并用的新观念。[25]
至于肯定人的本性欲求,追求人的自由、利益、权利的享乐之风、趋利之风及功利主义,这些因素都是人自来就有的本性欲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生存规则,只是以往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人们因物质资源有限而普遍贫困,为了社会和谐及群体生存,统治者要提倡崇理节欲冀以避免纷争,因而这些人的本性欲求受到正统伦理的压抑,相应的生活方式受到限制和压制。而在这时期的上海,由于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使这些人性因素得到了释放的空间,人们以往只是作为想像或受到社会排斥的一些享乐随欲的生活方式,如今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公然而行,并引起群相仿效而流行成风,由此引起人们对于人性欲求及人的自由、利益等赋予新的价值含义,予以正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生活方式不仅是传统伦理向近代观念转变的中介,而且也是连接新旧观念的内在资源。这种资源主要存在于民间生活方式及由此形成的民间生活伦理之中,正是这种内在资源,在适应近代化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调整和变异,由此构成了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内核,其中蕴含着中国近代新价值观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
结 语
通过以上对于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观念的近代转变,首先起自上海等通商城市由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变化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生活方式变动是这种观念变迁的启动和中介,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由化生产方式变动而引起观念变迁有所不同。
第二,人们由适应新环境而采纳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社会风尚,对传统伦理造成冲击,传统伦理由于日渐丧失有益于人们的效能及对于人们的规范效应,日渐被人们所抛弃,由此造成传统伦理的衰败,但对于社会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第三,由生活方式变动而孕育形成的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功利主义,以及生活的世俗化等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都是与近代工商业化和城市化这一近代化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社会观念。它们来自于人们由实际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变动,来自于中国民间世俗生活方式和生活伦理的内在流脉,虽然人们在思考这些观念时,也往往将西方国家作为富强榜样而作为参照,但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孕育形成过程来看,主要是来自于内在的生活变动和民间观念的源流,而不是受西方观念的直接影响。
第四,这些新的社会观念,从其基本价值取向来看,是以求富求强的功利主义为核心,从这一点来说,与西方的理性化是一致的,但中国近代观念仍有其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具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和伦理内涵。探明这一独特性,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上述考察虽然仅限于晚清上海,但反映的一些基本趋向,对于中国近代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首先,这些现象具有时代趋向性。因为这一时期由上海等通商城市开始的商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是一个此后不断向其他地区扩展的时代趋向,在同时期的天津、武汉等通商城市,以及后来的城市化中,都会观察到一些相似现象,只是上海出现的更早、更集中。其次,上海对于其他地方除了的幅射力之外,其文化影响也具有更强更远的幅射力。如《申报》在七八十年代就发行各地,在内地多处地方有销售点,传阅、谈论《申报》已成为各地关心时势的文士官绅们的日常活动。[10](p363—367)因而上述这些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动虽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如上海这样的通商城市里,但其影响却大大超越了这些地域,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少后来参与维新活动的人士,就或是曾亲临上海等通商城市,或是阅读过那里出版的报刊书籍等,因而他们的思想也多少曾经受到过这些地区的影响。可以说,上海等通商城市发生的社会生活变迁与社会观念变化,与后来维新思潮具有某种联系,是孕育形成近代思想观念的一条内在流脉和内在资源。
:
[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熊月之.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A].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C].上海: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89.
[3]中国宜造洋货议[N].申报,1892-01-18.
[4]郑观应.商战上[A].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N].申报,1873-04-07.
[6]洋场咏物诗[N].申报,1872-08-12.
[7]龙湫旧隐稿.前洋泾竹枝词[N].申报,1872-06-13.
[8]岁除论[N].申报,1880-02-08(十二月二十八日).
[9]论服色宜正[N].申报,1894-03-16.
[10]刘志琴主编,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1]论中国洋务之效[N].申报,1890-03-04.
[12]服色辨[N].申报,1890-10-18.
[13]香山荣阳甫致本馆书[N].申报,1872-12-29.
[14]本馆劝慰香山人论[N].申报,1873-01-03。
[15]江苏华亭县人持平叟.禁娼辨[N].申报,1872-06-10.
[16]中外新闻.录华友来稿[N].上海新报,1869-11-13.
[17]拟请禁女堂倌议[N].申报,1872-05-25.[
[18]机器缫丝说[N].申报,1882-02-05.
[19]中外之交以利合论[N].申报,1883-12-11.
[20]扶阳抑阴辨[N].申报,1878-07-15.
[21]棣华书屋.论女学[N].申报,1876-03-30.
[22]及时行乐说[N].申报,1877-09-29.
[23](清)石成金.知世事:二集[A].传家宝:上海[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4]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25]李长莉.家庭夫妇伦理近代变迁的民间基础[J].福建,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