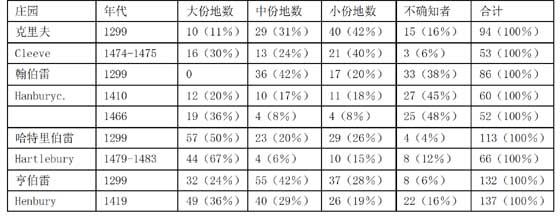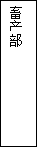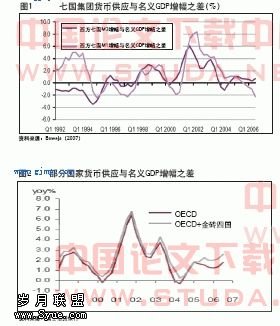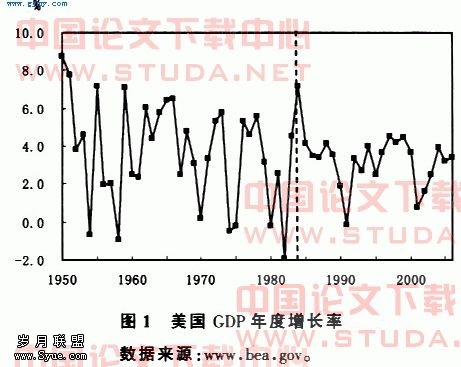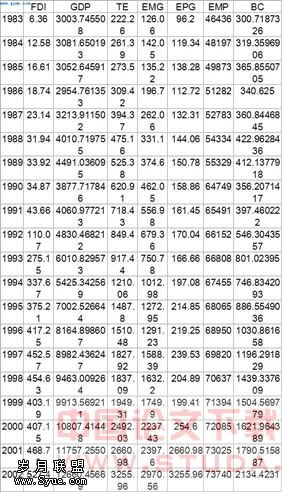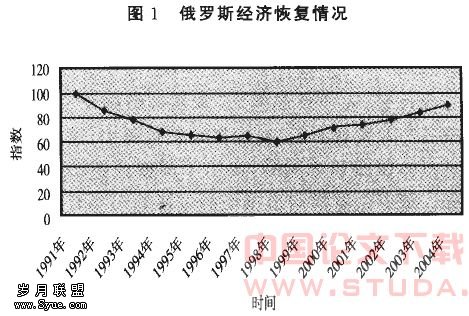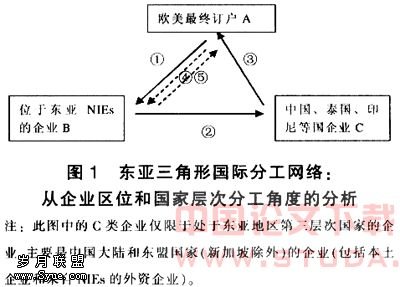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从“长时段”的角度宏观审视中日两国化的启动进程,就会发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前,亦即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这告诉我们:在宏观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事件比较”,而应注意“过程式”的长时段比较,进行探源式研究。
关键词 现代化起点 中日 非西方国家 文明 现代世界观
十八、十九世纪,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从上看,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率先勃兴并“骎骎东来”的形势下,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生,往往都是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认和大力摄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但在确定起点的标准和具体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做一比较研究,以揭示中日现代化启动运行的特殊,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中日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往往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叶前后,并很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民国以来,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是“西洋列强冲击论”。即以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重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如1937年王芸生提出:“我们若以江宁条约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神奈川条约则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①
其二是改革运动说。此种观点又可分为“同步说”和“非同步说”两种。“同步说”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从洋务运动开始时起算,比较近乎事实。而日本的近代化一般都是以明治维新作为契机的。因此,近百年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开始的。②所谓“非同步说”,则是将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分为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改革”两个不同的阶段。所谓低层次改革,就是在知识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改革则是国家制度的变革。在日本,这种“低层次改革”主要表现为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南诸藩改革运动,在中国则为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发起的自强运动。相比之下,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就晚了二十多年。③
其三是“前现代化说”。即以中日两国步人近代社会前(19世纪中叶前)其社会内部发生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如日本学者大石慎三郎等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应以此作为现代化的起点。④中国学界也有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内生性的早期现代化萌动,并认为:“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⑤
上述观点分别以中日两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改革运动或传统社会内部萌生的现代性因素为标志,来揭示两国现代化启动运行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我们理解认识两国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是颇有裨益的。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未真正体现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现代化启动运行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特点,以确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的独特标志。
首先,关于“西洋列强冲击论”。应该承认,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等手段,强迫非西方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是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它标志着非西方社会从此步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发展阶段。但由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实际上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所做出的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究其实质,乃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只是标志着西方列强对其所施加的“外压”更加强大,“挑战”更加严峻,作为一种“外力”作用,这种“外压”和“挑战”只能通过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主动“回应”,才能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或外交讹诈,强迫非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事件,只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可以作为非西方国家被动地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如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1853年的“黑船事件”作为日本步人近代社会的标志等,但我们却不能将其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说明现代化的起点和近代社会的开端不是一个问题,二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应该加以认真区别。
其次,关于“前现代化说”。以中日两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中出现的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局部性变化作为两国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其价值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强调非西方国家传统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生的“现代性”资源,借以发现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来样态。这些研究对于探索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衡量评估非西方国家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要注意对问题进行复杂性分析:一方面,要注意人类文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评估非西方社会这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时,一定要注意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率先启动并迅速向东方扩张的形势下,历史已不允许这些国家在传统的文明秩序框架内自生现代工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移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通过“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以非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产生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作为其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另一方面,虽然非西方国家的上述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不能作为其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现代性”变化没有价值。因为在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摄取西方文化的整个行程中,其社会自身“现代性”因素变化的作用绝非消极被动,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性的因素始终参与影响着现代化的全过程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代化,只有在其社会内部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性”因素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化作一种发展的潜力时,其现代化进程才具有可能性。因此,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标志选择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非西方国家中世纪晚期社会内部某些带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为标志,也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强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或以其现代化改革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而应以将上述两种“趋向”结合起来的“双线交汇点”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这一“交汇点”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其社会精英人物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束缚,确立实证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调动社会内部有利于现代化启动的因素,大力摄取西方文化,以直面西方挑战的重大事件为标志。这正如法国学者阿兰·图雷纳所云:一切成功的发展过程“无不把内部和外部因素统统作为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而结合起来”。⑥而能将这种“内生的”现代性因素和“外来的”现代性挑战结合起来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恰恰是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在体认世界文明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世界秩序观”的变化。
再次,关于现代化“改革运动说”。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陆续发动的带有资本主义现代化色彩的改革运动,是其走向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这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改革运动同样不能作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因为非西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发轫不是其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积累、发展的产物,而是其面对外部现代性“挑战”所作出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在回应、学习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抛弃传统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形成新的科学实证的世界秩序观。只有这样,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才能顺利地启动运行。
二、中日两国现代化起点之标志
根据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启动过程中的上述特殊规律,结合中日两国走向现代化的具体史实,我们可以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过程概括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以及几乎同步兴起的从“形器”层面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指在传统世界秩序观解体和新的世界文明秩序观形成的基础上兴起的包括“制度性变革”在内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上述两个阶段前后相续,构成了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的全过程。很显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变化构成了中日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原初起点,而第二阶段则属于现代化的具体推进阶段。比较观之,日本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起点是18世纪70年代的兰学运动中《解体新书》的出版。而中国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束缚则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主要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为代表的世界史地研究著作的刊行为标志。据此,我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化发轫于18世纪70年代,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起点的,相比之下,两国间存在着一个长达80多年的巨大的“时间差”。
1.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在漫长的古代农业社会中形成的传统世界秩序观都非常狭隘,表现在: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⑦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在宋人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周边国家和海洋都被绘得很小,而中国区域则画得很大。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相比之下,岛国日本则因远离亚洲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其视野更加狭隘。“飞鸟时代”前,古代日本人的地理观念带有“神道空间”论的色彩。所谓“神道空间”,是指依山川地势而构成的封闭的空间单元,其空间为不同的神、部族、神话、礼仪所充填。这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众多的“神话空间”如同蜂房一样排列于日本列岛之上。“飞鸟时代”后,以佛教传入为契机,日本人的地理世界观进入了一个“神道空间”和“佛教空间”二重构造的时代。在接受佛教世界观的同时,日本人的地理视野开始扩大到印度,得知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另一个高级的文明存在,从而形成了“三国世界观”,即认为世界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国)、天竺(印度)三国构成的。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⑧
其次,在文化世界观方面,中国历代朝野人士大都持带有浓厚文化优越感的“华尊夷卑”说,即认为中国周边的诸族诸国皆为落后的夷狄,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夷狄的义务,使中国士大夫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与中国相比,日本文化世界观的结构则极为复杂,在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的框架内,日本是桀骜不驯的一员,它虽被中国视为夷狄,但始终没有放弃力争中华地位的努力。对日本民族来说,最高文化崇拜与一个民族所必有的我族最高崇拜未能合二为一,而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正如佐藤诚三郎所指出的那样:室町时代出现的“和魂汉才”一语,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归属独自的日本文化的归属感和自卑于中华帝国文化的劣等感的某种复合。⑨在这里,“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和神国的自尊意识矛盾地并存为一体”。⑩日本文化世界观的这种独特结构,决定了其对外意识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极是对中国大陆文明的狂热崇拜;另一极是对大陆文化的离心力和疏离感。受中国历代王朝“华夷观念”的影响刺激,日本统治阶级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册封体制”产生了一种逆反离心倾向,他们称日本是“神国”,位于“天下之中”,是真正的“中国”。在文化道德上也是“圣贤之国”,形成了“日本型”的华夷观念,自圣德太子以降,取消了对中国的贡纳、臣礼关系,谋求国际自立,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小型的华夷秩序世界。⑾
可见,在16世纪西人东来以前,中日两国在地理世界观方面都显得狭隘无知,亟需开阔视野,摄取近代地理新知。而在文化世界观上,日本人所持的是以“慕夏”为核心的“崇外主义”,而中国所持的是“天朝意识”下的自恋自大,两国对外来文明分别采取“狂热摄取”和“傲然排拒”的不同态度,这对于两国改变传统世界秩序观,形成新的世界秩序观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2.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与科学实证新世界秩序观的确立
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地理观念开始传人中日两国,立即对两国的传统世界秩序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以此为契机,两国的“世界像”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化:
首先,从比较角度研究分析世界史地知识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具体进程,会发现许多重要的不同:
(1)从世界史地著述成书及传播的过程看,在中国,耶稣会士扮演了绝对的主角,而在日本则以兰学家、洋学家为主力。19世纪中叶前,在中国颇具影响的世界史地著作几乎都出自耶稣会士之手。而且,在西学著作的具体翻译过程中,明清士大夫虽然也曾参与其事,但其作用不大。可见,上述西学著作的产生,并非中国士大夫倾心学习摄取的产物,而是耶稣会士“灌输”的结果。而同期的日本,其世界史地著作则多出自洋学家之手,或为翻译洋书而得,或为自汉籍训读而来,或为综合洋汉各种著作独立撰著而成。如被称为锁国时代日本最大的“海外通”的新井白石因编写《和兰纪事》、《采览夷言》等书籍,使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遍及五大洲,“(白石)的世界观在广博精密这一点上,整个十七八世纪的亚洲无与其比肩者。”⑿1810年,德川幕府又命高桥景保绘制刊行《新订万国地图》(东西两半球图),成为江户时代最为精确的世界地图。此外,与康熙年间的测绘活动由西士直接主持不同,1800年,日本人伊能忠敬在北海道测量了子午线1的长度。此后又经过了18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全国的大地测量,绘成《大日本沿海实测地图》。1821年,洋学家高桥景保曾将忠敬地图与清康熙年间的大地测绘相比较,评价道:“汉土五千年,至清假手与西人,而后地图始定,则忠敬之功岂浅小乎哉。”⒀应该说,这是对此时期中日两国世界史地成果恰如其分的评价。
(2)从长时段角度审视世界史地知识在两国传播的动态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中国明清时期呈现出“中断性”特色,而江户时代的日本则带有“连续性”特点,不断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
就世界史地著作本身而言,在日本,十七八世纪由南蛮学家和兰学家撰写的西学著作到19世纪初大多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如兰学家山村才助昌永在1802年国内外史料增订白石的《采览异言》,为撰写此书,才助“参考西籍32种、汉籍41种、和书53种、汉籍中包括了《坤舆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图说》、《坤舆外纪》等”。⒁兰学家大规玄泽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书中“精详明确,尽白石先生所未尽之地海、坤舆、方域之至大,四方万国之广袤,国俗之情态,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周悉至其极”。⒂才助将白石的著作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创造了江户时代世界地的最高峰。再如1799年人大规玄泽芝兰堂的大坂富商山片重芳,酷爱荷兰“风物”搜集,在他数百件的“兰癖收集品”中,仅地理学门类的图书就有40多种。⒃可见,对外“锁国”并未使日本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发生中断,反而有了更高的“连续性”的发展。
而在中国,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则发生了严重的中断。明代西方世界地理知识初人中国时,对于这些闻所未闻的新知,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为自己和国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广阔的世界而感到惭愧,惊呼:“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慨叹:“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洲吾乡又一粟之毫末,吾更藐然中处。”⒄这说明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已经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知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范围很小,有些西洋舆图的收藏者,其动机也只是好奇。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甚至抵制的态度。翻检明清时期的典籍,怀疑、排斥西方世界地理知识的言论俯拾皆是。他们将世界地理知识斥之为“邪说惑众”,“直欺人以目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⒅并视之为“邹衍谈天,目笑存已”,⒆根本不予接受。致使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等一代灌输西学的伟人辞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人所忘记、失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识反而不如明朝末年。降至清代,这些经由耶稣会士之手传入的西方世界地理新知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在很多官方权威经典中却对此表示怀疑和批判。《四库提要》的作者们虽然将耶稣会士所著之《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世界史地著作列于“总目”之中,但对书中所描述的真实的外部世界图景却采取了轻率的否定态度,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⒇将耶稣会士描绘的真实世界图景视为虚幻的传闻之辞,采取了“姑且录之”的态度,根本不承认其学术价值。
(3)在初步接受世界史地知识的基础上,日本的兰学家和幕府中较为开明的统治者摒弃了传统狭隘的“三国世界观”,确立了科学实证的现代世界观。而明清朝野人士则未完成这一关键性的转化。明清时期,由耶稣会士主持翻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实际上已经向闭锁状态的国人介绍了五大洲、地圆说、五带划分、测量经纬度等全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他们强调“地既圆体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之名,初无定准”。[21]但这些观念传播不广,并未被时人所接受。可见,从16世纪上半叶的西人东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前夕300余年间,在人类文明由“分散”到“整体”,走向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朝野人士没有对剧变的世界作出迅捷的反馈和回应,没有完成由古代世界秩序观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变。
与中国不同,日本的近代世界地理知识传播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的研究者,他们常看着世界地图,与近臣畅谈世界形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1708年,新井白石通过审讯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传教士西笃梯,与荷兰商馆长等途径,成为锁国时代日本最大的“海外通”。“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邻”[22],这是兰学家杉田玄白所赋的诗句,从中可以窥出以新的地理空间知识的广泛传播为前提,日本知识精英全新的、开阔的世界文明视野。可见,19世纪中叶前,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拓宽了视野,打破了狭隘的“三国世界观”,确立了科学实证的世界地理观念。
其次,在文化世界观方面,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日两国传统的“文化世界观”发生了不同路向的变化。明清时期,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少数开明士大夫开始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那里也有“声教”、“礼仪”,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风俗。并坦言:“独笑儒者未出门庭,而一谈绝国,动辄言夷夏夷夏。若谓中土而外,尽为侏离左衽之域,而王化之所弗宾。”[23]对传统夷夏观进行深刻的反思。但上述卓见只限于明中后期和清初极少数士大夫之中。随着清政府对外采取闭关政策,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仍固守传统的地理观念,对五大洲、地圆说深拒固纳,仍陶醉于浓烈的“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面对剧变的世界,其华夷观念非但没有走向消解,却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从历史上看,这种转变是在以下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一方面,明清王朝是这个历代封建政权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王朝。这是因为明政权是驱逐元朝,恢复“中华”的产物,而清朝则是以“东夷”的身份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在对内统治中非常忌讳自己的“夷狄”身份,故在对外关系上大力提倡华夷之辨,企图借此把汉族视满族为夷狄的看法转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早期西洋各国贸易商人为牟取贸易之利,对中国封建王朝一切惟命是听,甚至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强化了国人的华夷观念。其直接后果是严重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处于文明剧变前夜的近代中国根本无法直面世界,产生开放意识,其现代化也自然无法启动。
而在日本,新的地理世界观的确立,直接导致日本传统世界观的根本变化。笔者认为,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秩序观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其具体标志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亲自解剖处刑犯人的尸体,并据此证明了荷兰版医书的正确性,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错误,由此对中国文化产生怀疑。1774年,日文版的《解体新书》出版,立即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划时代意义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其一,打破了对中国的传统崇拜观,确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观。早在飞鸟时代,随着佛教的传人,日本人已意识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像印度那样与中国文明并立的文明,对中国的绝对崇拜开始走向“相对化”。但日本人对中国相对化的认识,还主要是建立在想像和情绪化的基础之上。而以《解体新书》中所传输的新世界秩序观则是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的,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1775年,杉田玄白继译刊《解体新书》后,又著《狂医之言》,初步否定了古来流行的“中国中心论”,形成了“西洋文明中心观”。他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24]渡边华山也提出:西洋各国“之精博,教正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指中国)所不及”。[25]在他们的文化世界观念里,中国已经不再是文明的中心,崇拜中国的天平已逐渐向西方倾斜,这标志着日本知识精英中国文明崇拜观的崩溃和西洋文明崇拜观的确立,也揭开了日本摄取西方文明的序幕。
其二,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化。早在17世纪初,新井白石即承认西方文明在“形器”方面是先进性的,但日本在“形而上”的哲理和人伦方面还是远远优越于西方的。[26]随着兰学的日益传播,日本知识精英开始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形而上”之道也是颇值得师法的。如兰学家前野良泽在《管蠡秘言》中即指出欧洲的比中国和日本优越,批判了封建的身份制度,从而暗中赞美了基督教。本多利明也认为“国土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与教示”。[27]透过上述对西方文明“形而上”层面的倾羡赞叹之辞,可知日本知识精英的西洋观已经超越了“形器”层面,进入到社会制度层面。这是日本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进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它开辟了日本人直接依据原著研究和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道路。这标志着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开始移人日本,标志着日本现代化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其三,在民间形成了一支“自下而上”的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与“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转变的同时,先后兴起了兰学运动和洋学运动,出现了一大批通晓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据1852年出版的《西洋学家译述目录》统计,自1774年至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欧洲的医学、天文、历学等书籍多达470余种,从事翻译西洋书籍的学者有117人。[28]而且,其中还有像杉田玄白、志筑忠雄等兰学家构成了日本摄取西方文化的核心力量。可见,日本与中国不同,其“执政者虽亦关心西欧科学,但其输入及研究却以民间为主”。[29]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起自民间的摄取西方文化的浪潮,逐渐向幕府权力深层渗透,出现了与政治结合的趋向。有些幕府的老中、一般官吏和地方诸侯大名醉心于以兰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被称为“兰癖老中”和“兰癖大名”,形成了由兰学家、诸侯大名、幕吏藩臣三者构成的摄取西学的主体力量。如1795兰学家大规玄泽成立以兰学家和兰学爱好者为核心的沙龙式组织“新元会”,定期集会,研讨西方学问。从1795年到1837年,共集会44次。据考证,计有104名兰学家和兰学爱好者参加了集会,“就其中经历大致清楚的67名来看,官藩医阶层26人,被推定为町医的有8人,医生占绝对多数。此外,藩主阶层7名”,[30]足见其成员构成的多元性。再如萨摩藩主岛津齐彬酷爱西方文化,常“与江户洋学者川元幸民、箕作阮甫、高野长英等共讲洋学,在当时的诸侯中率先研究泰西文明,通晓海外大势,见识远大。”[31]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放弃锁国,走向开放进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使日本现代化在启动的伊始阶段便呈现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特点。
而中国在同时期对西方文明的感应则比较迟钝,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诞生为标志,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强劲的认识西方的思潮。以此为契机,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新知才又重新传人。如魏源在《海国图志》的三种版本中,均按区分国,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及其他情况,成为当时中国最完备的世界知识总汇,构成了立体实证的世界文明全图。在传统地理世界观转变的基础上,国人初步摆脱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对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有了深刻的体认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已率先突破了华夷观念的束缚,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转变。正是在上述“无形”之变的基础上,中国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但相比之下,日本在现代化的启动发轫阶段已比中国早了80多年,这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时间差”,实际上是两国对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综合回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三、余论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海内外很多学者开始对传统的“西方冲击——回应”的外因取向分析模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反对单纯地从“西潮冲击”视角来解释非西方国家走向化的,主张改变研究视角,从“亚洲的角度”来分析观察亚洲国家近代剧烈的社会变迁。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对于学术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研究发现非西方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的特殊,尤其是揭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大有裨益的。但应该指出的是,人类文明由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十七八世纪的中日两国已经发生了种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由于此时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业已兴起,使得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而然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因此。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便成为此时期非西方国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课题。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挑战和中国的回应,仍然是这些国家现代化研究分析的一个基本视角。本文就是以此问题为基本线索对中日现代化起点进行比较分析的。
如前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大体上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同步启动的,相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一些。因此,很多学者把比较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30多年的时间里,认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明治维新超过了洋务运动,东亚文明实现了结构性的盛衰之变。但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角度宏观审视两国现代化的启动进程,就会发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前,亦即是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这告诉我们:在宏观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事件比较”,而应注意“过程式”的长时段比较,进行探源式研究。
同时,值得提及的是,19世纪中叶前百余年间,中日两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之所以有上述不同的反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看,两国不同的对外认识传统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初,梁启超就曾提出:“日本乃小国,且无其所固有之学。故有他界之文化传人,则趋之若鹜,其变如响,不转瞬而全国亦与之俱化矣,中国则不然,中国既是大国,又有数千年相传之固有之学,壁垒森严,故他界之思想人之不易。”黄仁宇也认为:“因日本重洋远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时发展为举国一致的运动。”[32]上述观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日两国现代化启动发轫过程中的异同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① 王芸生:《芸生文存》,大公报,1937年版,第249页。
② 汪向荣:《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页。
③ 丁日初、杜恂诚:《19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浅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大石慎三郎主编:《江户时代与现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版。
⑤ 高翔:《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中国社会》2000年4期。
⑥ 阿兰·图雷纳:《现代性与文化特殊性》,《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
⑦ (宋)石介:《徂徕集》卷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 朝尾直弘编:《日本的社会史——社会观和世界像》第七卷,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⑨ 佐藤诚三郎:《近代日本的对外态度》,东京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⑩ 朝尾直弘编:《日本的社会史——社会观和世界像》第七卷,岩波书店,1987年版,第303—304页。
⑾ 柴田纯:《思想史上的近世》,思文阁,1991年版,第274页。
⑿ 宫崎道生:《世界史与日本的进运》,刀水书房,第291页。
⒀ 伊达牛助:《伊能忠敬》,东京古今书院发行,1937年版,第116页。
⒁ 海老泽有道:《锁国史论》,东洋堂刊,1944年版,第143页。
⒂ 沼田次郎:《洋学传来的历史》,至文堂,1960年版,第97页。
⒃ 有坂隆道:《日本洋学史研究》,创元社,1985年版,第129页。
⒄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48页。
⒅ 徐昌治辑:《圣朝破邪集》,卷三,清咸丰五年刻本。
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23页。
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
[21]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页。
[22] 高桥磌一:《洋学论》,三笠书房,1939年版,第211页。
[23] 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24] 信夫清三郎:《日本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25] 《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69页。
[26] 《日本思想大系,35,新井白石》,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19页。
[27] 《日本思想大系,44,本多利明、海保清陵》,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132页。
[28] 辻善之助:《增订海外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年版,第757页。
[29] 薮内清:《西欧科学与明末》,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2页。
[30] 杉本勋著、郑彭年译:《日本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9页。
[31] 鹿儿岛市役所编:《岛津齐彬公传》,鹿儿岛市会,1925年版,第12页。
[32]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