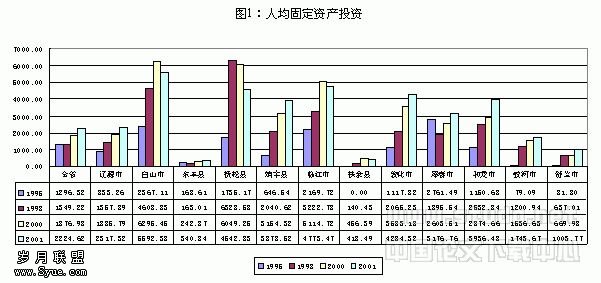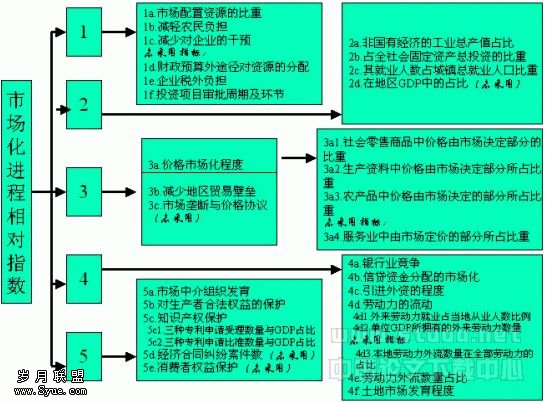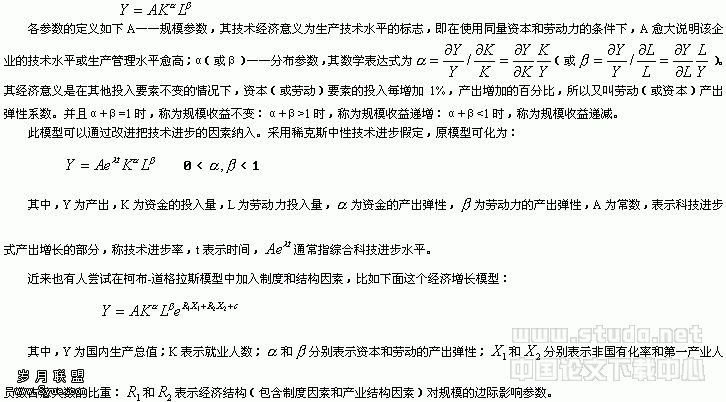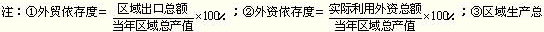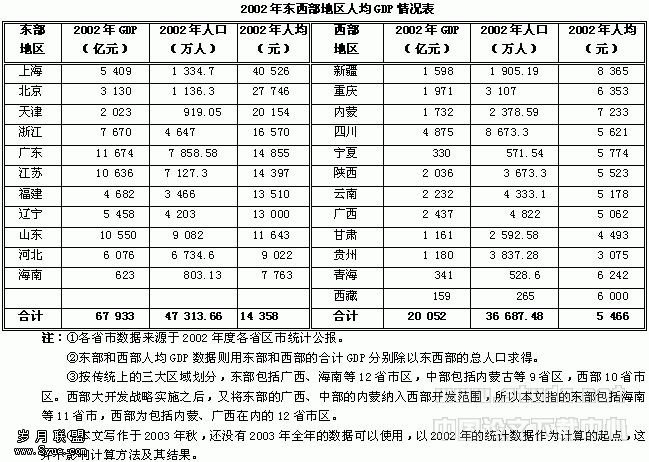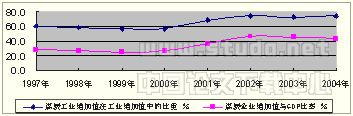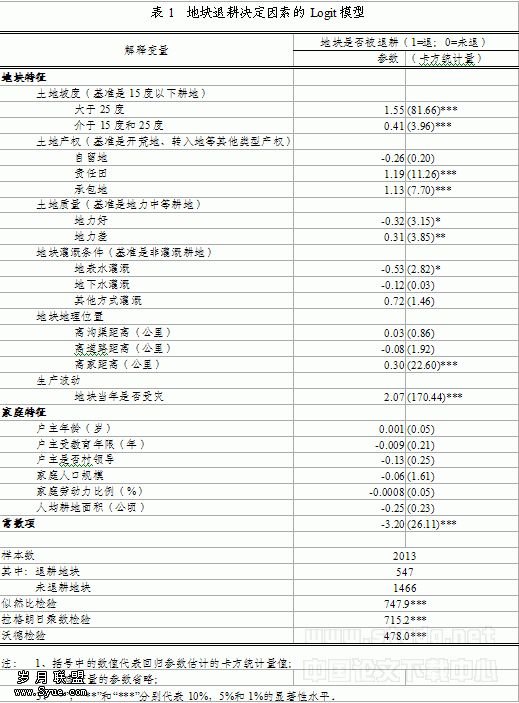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
方氏并非徽州土著,其先原居于黄河流域,“世望河南”[④a]。方氏南迁并演化为“新安名族”的过程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关于后二个方面,将分别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论述)。
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汉末的社会动乱。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b]。从明刻本《新安名族志》来看,方氏是其收录的78个名族中最早移民徽州的。纮二传为储,东汉和帝时方储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任博士迁议郎、洛阳令、太常卿,死后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葬淳安城内,立祠享祭。方储死后被逐渐神化,撰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的《开国公家世行实》称方储“博经文,辨图谶;讲孟氏易,善星文,占吉凶,知未来,察奸谋,预知灾异”[②b]。宋明帝加赠方储为龙骧将军、洛阳郡开国公。唐监察御史张文成撰文立碑云:方储“生平之日,羽驾乘空,仙游之时,蝉脱而去,咸以公为仙化,莫知所归,共建祠堂,以时祭享”[③b]。方储祠堂后被称为方仙翁庙。宋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赐以“真应庙”额。《敕赐黟侯真应庙额》载道:方储“号仙翁,遂立庙,系在祀典今千余岁,前后灵迹不少。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所勘青溪县初乃歙之东乡,因储父子避地始为州县,故其庙正当县郭冲要之处,远近祈祷必会集其下。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委是功德及民最为深远”[④b]。生前显赫,死后神化的方储虽然不是方氏始迁江南的第一人,但由于仙翁庙、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结集的场所,“每岁仲春(今用季春)三日诞辰,子孙陈祭行三奠礼,读祝升歌,罗拜其下,祭毕聚饮欢洽而散”[⑤b],因此方储成为宗族崇拜的偶像,方氏认同的标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撰修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将方氏世系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原始世系》,追溯方氏受姓的经过直至迁徙江南,封黟侯建庙祀,共113世。方氏以雷为鼻祖,据说雷是榆芒帝的长子,有“破蚩尤于阪泉,斩永曜于涿鹿”的功绩,被轩辕封于方山,“因封赐姓,所传伏羲后六姓方居其一”[⑥b]。《原始世系》失之邈远难征,方氏后人已指出:“自雷祖至回公历年未及四百而传世四十有五,窃有疑焉”[⑦b]。其二为《统宗世系》,自方储1世起至12派始迁祖汇而图之。由于原始世系以方储之子辈为113世,方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统宗世系第1世。其三则为《分派世系》。
方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这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关方氏宗族活动的记载甚少。除上述方仙翁的祭祀活动外,东晋咸和年间方氏8世藏曾撰修《方氏历代谱牒》,“考姓氏之源流,据年代帝号著世次,而衍真传,奕叶相承”[①c]。方氏《原始世系》当出藏之手。此外,根据宋明帝对方储的追封以及宋政和五年(1115年)《方氏续修谱序》的记载,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可以断定当时方氏在江南有相当大的势力。
方储定居的歙东乡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建置为始新县[②c],到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新安县(由始新改名)改隶睦州[③c],从此不再属徽州。汉唐间方氏的活动并不限于歙东乡,他们与徽州本土(不含东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例如方储炼丹处即在歙县柳亭山(今名霞坑)。但是,方氏向徽州本土大规模移民,建立宗族定居点,则是在唐代末期了。
最先向徽州本土迁徙的是方储季子洪的后代29世羽。羽的父亲肃于唐文宗七年(833年)登进士,任杭州仁和县令,三年后迁桐庐万户,始居白云村,为白云村始祖。肃有三子,长子huī翚无传;次子干唐僖宗时以诗名江之南,人称玄英先生;羽为季子,也善诗文。干和羽是方氏迁徙徽州本土10个大派的共祖,十分重要。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860年1月)裘甫率众起义于浙东,这场历时七个月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震动了整个浙江。咸通元年(860年)羽率家人退避到“居万山中”的歙县茆田。《联临分派世系》载羽小传云:“唐咸通元年与从孙甲之子景云避裘甫乱,挈家寓居歙西临河,筮者告以遇田则止,于是卜筑茆田,颜其庐曰师古,读书自适,因以家焉,是为联临派始祖”[④c]。羽五传琪迁联墅,珍居临河。联墅、临河隔丰乐水相望,与茆田相近,形成联临派的基本格局。
第二支迁入徽州的是33世杰兴。杰兴乃方储次子觌之一脉。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由歙东乡迁居歙县。《灵山方氏宗谱序》(1543年)记述其迁徙的原因是“避五季之乱”。杰兴是为灵山派始祖。第三支迁入的是33世景玘。景玘乃方储季子洪一脉,系29世干的后裔。《方村分派世系》载,“黟侯三十三世孙景玘公字公玉,仕唐为浙江廉使,致政归田,值世变乱,避地而居于歙南,以姓名其村”[⑤c]。第四支则为第34世承威,字可畏,又名彦成、三公。承威系干之后裔。关于承威迁徙瀹坑的原因,《方氏会宗统谱》卷七《瀹坑派始迁》的记载是:“宋景德甲辰(1004)自古睦州白云村避仇而迁歙南方巷井坞,即今瀹坑,是为瀹坑派始祖”。《方氏族谱序》(1525年)则认为:“三公,又曰彦成,值唐末藩镇割据自白云源徙歙之瀹坑。”该谱另一篇序言也说:“有三公者当唐末藩镇割据自桐庐迁歙之瀹坑”。上述两说,时间上互异,原因也不同,但不管是避仇还是避乱,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引起承威这一支迁徙的原因。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方氏第二次迁徙,他们由歙东乡、桐庐向徽州山区移民,从而促进了地域社会的开发。据《新安名族志》的不完全统计,汉晋南朝时迁入徽州的有13个大族,占78个名族的16.6%,而唐朝、五代迁入徽州的达37个大族,占总数的47.4%强。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合同的10个大派中的4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可见。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54世裔孙,属干的一脉。天泽原属苏村派。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交通要冲。《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元至正壬辰(1352)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方氏族谱》(磻溪成性堂抄本)对天泽迁徙的经过及原因作下述说明:“因红巾作乱,祖居地当孔道,避于磻溪之上。待洪武定鼎始偕昆季卜居,后裔奉为成性祠始祖,是为成性派”[②d]。磻溪在深山更深处,安全更有保障。
方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③d],方氏移入山川平衍处聚族而居,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人地矛盾必然会尖锐起来。于是有进一步的分支迁徙,从而使山区的开发向纵深。34世承威迁居瀹坑后,到第41世子华迁瀹潭,其间经过6代150年左右的时间。《瀹潭分派世系》指出子华是因“派衍繁盛,人稠地隘,乃于南宋绍兴间去井坞里许卜基,筑室而居焉”[④d]。人地矛盾也是桐庐白云村方氏继续向徽州迁徙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经商或宦游。例如,环岩派上路口支第43世千,“宋末时商游滁州,留家全椒县”。从千的小传还可知,千“尝游蜀中,倦还江南,因睹滁之全邑峰峦秀拔,遂寄籍焉”。可见千曾在四川经商,后又商游全椒,最后定居该地。
分析上述方氏迁徙的原因,可以看到歙淳方氏12派(康熙九年12派订立轮祀柳亭山真应庙合同,比之洪武四年10派宗支合同增加2派)中有6派是因社会动乱而迁入徽州的,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在唐末、五代。另有4派则是因人地矛盾而迁徙的,其中有3派是由瀹坑分支派生的。其时间则主要是南宋。此外,还有苏村、环岩2派始迁原因不明。以商业和宦游迁徙者均未直接构成大派,但16世纪后,因商业迁徙者在远地构成新的门、房支系则甚多。
从汉末方纮始居江南歙东乡,到唐末、五代向徽州山区的迁徙以及南宋时在徽州境内的进一步分支移徙,与中国古代北方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大致同步。三次南迁是传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表象,同时对江南的开发起着积极的作用。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方氏等“中原衣冠”不仅使徽州得到开发,而且也使其成为文化繁兴之区,以致有“朱之厥里”、“东南邹鲁”之称。汉唐五代中原各大姓向徽州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形式进行的,而徽州山区也以它的怀抱使宗族制度得以长久保存,从而形成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景观。
二
方氏以动态的迁徙来应对社会的动乱。当着方氏在新的生存空间定居下来时,便迅速地复制宗族组织,以“静”制“静”,恢复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生活。说相对静态是因为随人口的自然增殖,宗族还会有新的迁徙活动,各大派继续分支,不断地向人口更为稀少的地区拓展。方氏在迁徙的过程中,保持着清晰的统系,有严格的世代区分。方氏12派均出方储之后,其中方储次子觌之后有灵山、环岩2派;季子洪之后则以29世干、羽兄弟分支。干之后有方村、瀹坑、瀹潭、潜口、沙溪、苏磻、磻苏、佘坡、柘源9派;羽之后则有联临派。12派有着共同的始祖崇拜,有着固定的祭祖节日(9月初6)。凡统系、世次不明者不予认同。环岩《方氏族谱序》(1561年)指出:“希道公乃由淳安徙今歙县,又再传至念五公乃徙环山居焉。历宋至元,子孙蕃盛析居岩镇等处。故今新安诸方虽各有显官腴室而念五公之派终恃不肯轻与合。”《灵山方氏宗谱序》披露了这样的事实:成化年间灵山方士贵请兵部郎中方嵩为宗谱撰写序言,方嵩要求看谱,而士贵仅给他看了其它序言。根据这些序言,嵩只能“悟其大概耳,而索诸全谱则弗克也”。究其原因则是防止世系图外泄,以免同姓冒认宗亲。所以嵩在谱序中就此发表议论:“余虽愚,非欲援引以求通亲或稽考,而渥洽之两相资焉,而借重于世也。”潜口派富源支《方氏族谱序》(1525年)介绍了富源派与桐庐方氏认同的经过:“方氏族谱书成,携过桐庐访玄英之遗裔,会族长曰冕者出其谱相参订,上下数千年靡不符契,于是叙族讲好。”反之,如苏磻派分迁杞梓里支下方村头裔孙,虽也积极参与方氏统宗祭祖活动,但因世次不明而不准入统宗图系,“以俟续考订正”[①e]。这就造成极强的群体归属感,从而有利于方氏在新定居地以整体的力量与其他族姓争夺生存空间。在山多田少的徽州,这种争夺往往是十分激烈的。
笔者曾往徽州方氏聚居地考察,深深感受到宗族是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较为成熟的生存系统。例如磻溪,距苏村3里,旧时只有山间小道可出入。群山环合中,一线源于浙江的昌源水穿过这里,注入新安江。磻溪村便在昌源河谷。明初方氏宗族迁入后,即组织人力、财力,拦河筑起4道石堰,枯水期可储水,平时则抬高水位,保证生活和生产用水。这4道石堰现在已遭破坏。数十年前,村周山头还是树木参天,因有祖坟,不准砍伐,生态得以保持平衡,现在山木几乎已被砍伐一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生态平衡是徽州山区宗族的一大功能。这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宗族聚居,子孙繁衍,必然会有贫富的分野。《续方氏家乘序》(1464年)云:“凡同方姓者虽贫富不齐、贵残殊位,皆吾纮祖储仙之遗裔,其遇高年长者咸宜尊敬,于茕独孤弱变必加恩意焉,如此斯有以广念宗敦族之义,又有以致竭诚事天之孝,庶仁义之流演而吾族之益盛容漫没乎?!”因此,宗族以族产收入来泽惠族党、救济贫困。宗族抚孤恤贫的义举缓和了其内部小农的分化,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这些小恩小惠,族人之外的佃仆是得不到的。但歧视、迫害佃仆现象,在徽州很普遍。嘉靖《徽州府志·风俗》称:“其主仆名分尤严肃而分别之。臧获辈即盛赀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宗族与佃仆之间的对立状态,掩盖着宗族内部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在徽州我们可以看到佃仆的反抗斗争,却少见农民起义。瀹坑派55世方时翔的传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季无主荒馑,后不逞者乡纷起,群仆而叛,族哄而攘,君首创富室醵金饷贫,联络拳勇,名以御外侮而实杜内衅”;“本朝(清)既定鼎,山寇犹在在窃发,乡之悍仆杨继云恃勇为乱,肆害本乡,屡捕不得,一日忽至众怖甚。君乃帅乡之有力者密谋之,先藏器械诱之至,突起击之仆地,村众继至共杀之,余党皆骇散。巨害既歼,乡遂宁静。”[②e]方时翔是个“往来大江南北间,转移贸易,以时伸缩之”的客商,后归乡置产,成为族中大地主。在对待“族哄而攘”上,时翔“首创富室,醵金饷贫”;在对待“仆群而叛”,方氏则毫不手软“共杀之”。谱牒志乘中常见“族居数千人,相亲相爱,尚如一家”[③d]的记载,这并非全属虚饰溢美之词。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及南宋赋役的繁重,这个自34世承威迁瀹坑起,直至第40世的7世同居家庭才析居。第41世子华、贞献分别迁瀹潭、潜口。迨至明清,这类百口同居、同爨的大家庭已不多见,但在新的小家庭大宗族[①f]的格局下,佃仆阶层仍是转移、减缓宗族内部矛盾冲突的特有机制。作为一个生存系统,徽州宗族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富有张力。
方氏族人对宗族的归属感是建立在尊祖敬宗的基础上的。上述在祖宗面前不分贫富人人平等的观念便是由此派生的,其理论根源便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孝。方氏《成性祠宗谱叙》(1644年)云:“子与子言孝,父与父言慈,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推之与事君者言忠,与交友者言信,皆孝也。”孝派生忠,忠也是孝,“百行孝为先”。由此而推导的结果是,当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作出孝优于忠的选择也是合于儒家伦理的最高原则,也是理所当然的。《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太学广居方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启大以“祖父母在不敢以身从”为由,拒绝参加抗清斗争,不但未遭到人们非议,反而被作为孝的典范受到环岩方氏的推重,其墓志铭也上了方氏会宗统谱。儒家学说本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所以孝被推崇到至尊至高的地位。这套理论对维持农业时代农村宗族、家庭的稳定十分有利。只要能保持家的利益不受损害,在孝的理念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
宗族是封建国家的缩影,也是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此反封建国家的斗争其矛头所向往往首先对准宗法统治。据《桂林方氏统宗谱》卷四《忠义彦通方公传》载,北宋宣和年间“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人多出其门,竞为刻剥,深山穷谷之民,罔克奠居”。东南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在民间传播着食菜事魔教,该教教规之一是“不事神佛祖先”[②f]而主张“同党相亲相恤”[③f]。以“同党”取代同祖,直接与宗法观念相对抗。方氏族人方腊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谓“腊得妖书,藉以倡乱”。关于方腊,建国后尤其是“文革”后曾就其出身和籍贯发生过争议[④f],但是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方腊乃歙淳方氏的族人。方腊起义是由造宗族的反开始的,《方氏会宗统谱·佘坡分派世系》方有常小传载:“邑人方腊者向佣于家,宣和初腊得妖书,藉以倡乱,因令次子世熊首于县大尹,陈公光不察,反坐诬系世熊于狱,腊觉即杀其家人四十余口,惟第三子庚及孙文忠、文毅,并在狱之世熊得免。”方有常(44世)系自苏村始迁淳安帮源桂(41世)的曾孙。佘坡分派世系方桂小传载其“承父遗业,服贾青溪万年镇,即今威平,得膏腴产于帮源,曰姑婆宅,因挈家帮源居焉,时宋仁宗天圣癸亥岁也(1023年)”。桂因经商致富购地过居帮源,这是方氏12大派中唯一以经商始迁,又以战乱再迁定居的派系。三传至有常已是帮源的大地主了。宣和二年(1120年)秋,方腊杀有常一家后,“数日之间,啸众至数万人”[①g],不久便“众殆百万”[②g],席卷东南。三年(1121年)4月方腊被韩世忠部俘获,起义失败。《桂林方氏谱序》(1685年)有方庚助韩世忠破方腊的记载:有常季子“庚公乃奔命江淮,逆王师为韩忠武先导,诱擒腊并其党羽,东南以平。余读宋史尝观腊寇之变起于仓卒,聚群不逞之徒,伪据吴越,欲凭江为阻窥视中原,已而王师直指,忠武为王渊裨将,以素未经涉之地,独能卷甲疾趋攀崖度谷,不浃旬而捣其巢穴,意必有卓荦非常之士,奋忠义以为先者,今乃知皆庚公力也”。有象征意义的是,方腊起义是以打击宗族势力开始的,也是在宗族势力的打击下结束的。宗族在变乱中,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复制再造能力。
在方腊起义的过程中,受打击的另一支方氏是柘田派。《柘田分派世系》方愚(45世)小传载:“宣和之难,奉亲避于穷山,兄弟被戮,室庐灰烬,创兴于平复之后,葺墓修谱,追溯渊源,后世赖以传焉。”柘田方氏所受的打击是双重的。《续方氏家乘序》(1464年)云:“愚祖遭兵燹,后获抵升平。”[③g]遭“兵燹”而不称“寇”,是指柘田受方腊的株连而遭宋兵打击。这是明代天顺年间写的序,而当事人在宋代却未便称“兵燹”,只是强调自己“清白相承”,这是可以相印证的。同时,方腊对柘田本家的叛逆和打击,也可见于愚的谱序:“蒙又以族系日繁不可具载方册,略书世代名行纪于家谱之后,自元英先生干以来至我高祖承之,祖行共十一世,叙成一图,传宗人之家各图诸壁,庶几举目知敬,不幸贼炬一焚,悉为煨烬。”谱图付之一炬,这是方腊对宗族统治的宣战和讨伐。
柘田方氏在经历方腊和宋兵的双重打击之后,迅速地重建宗族统治,《方氏谱牒序》(1130年)云:“渐创屋业,会骨肉于离散之后,定宗盟于扰乱之余,亲族得以再聚。”愚小传所称“葺墓修谱”都是宗法统治重建的象征。
《方氏族谱序》(1700年)指出祠堂、谱牒可以“济宗法之穷也”:“吾乡聚族而居,居必有祠,而大宗祠必建于始迁之族,与庶子祭必于宗子之家义犹相近,而谱牒因此以系,凡昭穆继序、嫡庶相承、尊卑长幼、爵位名号与夫忠孝节义、幽贞阃范斑斑可考,虽数千年之族,松分叶散,而入其祠观其谱凛然有不可犯之色,则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在徽州宗族社会,一个个富有张力的生存系统,在祠堂、谱牒、祖坟的维系下,不断地延续、再生,“以静制静”,从而构成农村社会“静态”的景观。
三
传统社会的转型始于16世纪,其标志是资本主义萌牙的诞生。由于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直至19世纪中叶,新的因素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社会转型始终是沉重而难以启动。传统中国特有的结构之一便是宗族制度。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宗族自身又有什么变化呢?这一变化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如何?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的视角稍往前拉,从转型前最后一次王朝交替,即元明之间的动乱开始观察,以便作出比较,把握转型期的特征。
方氏宗族受族人方腊的“连累”,致受沉重打击。除了柘田、佘坡外,其他方氏派系也不同程度受“连累”。《联墅方氏源流序》(1308年)云:“独怅祖宗文集家传谱记毁于五季及宣和。”方村《锦庭方氏家谱序》(1242年)云:“干戈纷乱之后,版籍图书大都厄于兵燹。”方氏所遭打击是普遍而深刻的,以至家郑玉在为这个“东南为第一大族”的《方氏族谱》(1324年)撰写序言时,告诫方氏子弟:“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方氏子孙勉之。”可见直至元代,方氏“家声”仍未“复振”。元未明初,改朝换代的战争也给这个山区宗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临河方氏本宗源流考》(1484年)载:“元朝之乱抽点富民婴城固守。后归我太祖高皇帝遂籍于兵,调征不停,既成混一,分隶诸卫,无复得守乡土,纪于载册。吾宗富盛之族全徙于军者七去其五,加以贫乏不能自存,流散走死,不知其有几也。所得存于临河者是亦其幸欤。”《方氏会宗统谱》联临分派世系没有具体披露元末明初方氏被“乱抽点”和“籍于兵”的情况,但其他分派世系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柘田派居马源》载,第54世聚师(1342-1414年),“父以有司令拒红巾贼,死于饶州,时聚年甫十二,能哭奔贼寨,获父首归葬”。聚师第4子春童(1363-1401年)“建文三年辛巳充百长,部领赍粮赴德州,回至徐州卒”。这些资料可以印证元末“乱抽点”和明初“徙于军者七去其五”之说的真实,以及动乱对地域社会,哪怕是群山怀抱之中的地区,也是影响深刻的。撰于明永乐戊子(1406年)的方氏《家谱续通序》惊呼:“数十年间尊祖之义扫地矣!”元末明初战乱后,方氏宗族的重建其方向仍是农村到农村。到15世纪末的弘治年间,徽州农村社会又恢复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闾阎安堵”、“比邻敦睦”的情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再度突出。
16世纪初的正德、嘉靖年间,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给了徽州前所未有的震荡,其深度和力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乱和灾异。首先是宗族迁徙和重建的方向转为以农村到城镇为主,这与社会转型是合拍的。方氏因经商而迁徙的城镇几乎遍及全国,而以江、浙、赣、鄂、川以及闽、粤、鲁地为盛。我们知道,徽商的兴盛是与其对盐业的把持相关的。方氏经营盐业起于明初,柘田派等55世赵童(1362-1414年)“洪武间诏济边储,时甫弱冠,资装赴甘肃易粟输公”[①h]。这是方氏以边商身份开中纳粟经营盐业最早的一例。因边地遥远,方氏为边商者不多。弘治间开中折色,内商兴起,徽商得地理之便,在两淮盐场迅速崛起。迁徙于扬州、江都、泰州、仪真等城市的方氏都直接与盐业相关。而迁徙于汉口、荆襄、江西等两淮引盐销售口岸的方氏其经营往往也与盐业有关。这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点方向。以联临派为例,16世纪前,联临方氏的迁徙主要是在徽州境内及境外近地。联临派居联墅钟英门最早迁扬州的是44世祐孙,时在明初。其后从16世纪下半叶的万历年间到18世纪上半叶的乾隆初年,即从53世到59世,临联方氏不断地迁往扬州。
山东也是方氏迁徙的一个重要方向。联临派居联墅黑楼门55世嘉言、嘉训同迁济宁小闸口;承庆门50世雄才、僖、*[仁去二加郊],51世文@⑨嘉靖年间“俱迁临清”;新屋门45世九皋迁临清;慎业门居信行第50世符“迁居临清,符之次子元修由恩贡授北直深泽令”临清、济宁均为运河边上的重镇,商业素称繁兴,是徽商麇集之地。谢肇浙《五杂俎》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有一学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领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试者,尤可笑也。”方氏迁居山东,经商致富,延师教子,子弟科举入仕。这种局面说明方氏在临清已颇为得势。
方氏联临派从嘉万至乾隆初向远地的迁徙,除集中于扬州、临清处,还涉及四川、贵州、汉口、襄阳、海州、湖广、天津、镇江、常州、苏州、通州、常熟、湖州、孝丰等地,只是较扬州、临清人数为少。
方氏每一派别都有重点移徙的方向。如潜口派以赴荆襄经商为多,环岩则以扬州为主,瀹坑迁闽粤、两浙、济宁为盛。各派的迁徙也有相交叉的集中地。在《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七《科第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氏在移居地占籍或以商籍科举成功的记录。方氏联临派元焕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山东籍参加乡试中举,这是方氏在移居地科举成功的第一例。方氏以客籍参加科举,说明他们在移徙地已有相当根基。因此,这一变化反映了16世纪后宗族由农村向城市移徙的新走向,与社会转型是同步的。综合明清(自嘉靖十六年至乾隆九年213年间)方氏在远地占籍或商籍科举成功者的分布情况如下:山东籍2名,顺天籍2名,江都籍4名,仪征籍2名,湖广籍2名,江西籍1名,江苏丰县籍1名,浙江籍1名,安徽本省全椒籍2名,颍州籍3名,怀远1名,共计21名。可见江都、仪征是方氏最为集中地,沿江而上江西、湖广也多方氏,这9个科举成功者,其家族大多当与两淮盐业相关。将方氏在浙江科举的情况与两淮、山东比较,则可见方氏在该两地移居人数之多及势力之盛。
明代方氏科举成功者共54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仅占5.56%。清代则有很大变化,自清建国至乾隆九年(1749年)的百年里,方氏科举成功者共34人,其中占籍或商籍者竟达18人,占总数的53%。可见,从16世纪开始的向城镇迁徙的趋势,到清前期愈益发展。宗族顺应社会变迁所作的变通,证明即使到通常所谓的封建社会晚期宗族制度仍是充满活力的;同时,它也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力,给传统社会的转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其次是宗族自身的变化。社会转型一方面给宗族发展开拓了新天地,另一方面也给宗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因素。商品经济扩大了贫富分化,煽起了奢靡之风,打破了固有的等级顺序,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磻溪宗谱叙》称:“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面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若而人者即令萃集庙中,气谊不属,虽备言燕私不过轰然一堂,如韩公所云聚飞蚊焉。”《方氏会宗统谱》卷四载有一则由白云源迁问政的支派被革除的事例:“按祖庙旧籍载有问政一支而久不与祭,详考其故:吾乡巨族必置廨宅于郡城为因公至郡及岁科应试止宿之区。我方氏廨宅今独不存乃问政支丁私鬻致废,其久不入庙盖由于此。”上述变化与正德末、嘉靖初至万历年间徽州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情况是相对应的。
商品经济在破坏宗族传统秩序的同时,却又在加固着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清时代,徽商的财力居各大商帮之首,堪与其匹敌的只有山西商。徽商在其经济活动中借助于宗族势力,因而不惜斥巨资购族田、修谱建祠办族学,救助族之贫困者[①i]。郑玉曾在《方氏族谱序》中阐述宗族兴盛的三个条件:“非有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世以力田相遗而能保守不坏。”徽商为改变商为四民之末的地位,除捐纳为官外,还兴办族学培养子弟入仕。族中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徽商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入仕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经商。族中子弟为官,有利于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这在封建商业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利于宗族在徽州山区争夺生存空间。因此,宗族组织、达官大人之势,豪家巨室之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从而给宗族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方氏科举状况也证实了“资”与“势”的结合是宗族兴盛的前提。两宋300余年方氏科举成功者共25人,元代仅2人,明代54人,清代前叶百年间达34人,联临派在宋代占科举成功者的32%,有8人,明代占11%,有6人,清代占11.8%,有4人。占方氏四朝总数的15.65%,共18人。这一派在宋代科举最为发达,明清略有下降。而环岩派在宋代仅占8%,有2人;明代则上升至19人,占35.2%,清代再升至21人,占61.8%,占四朝总数之36.5%。柘田也是后来居上,宋元为0;明代占29.6%,有16人;清代占2.94%,有1人;占总数14.78%,共17人。潜口宋代占8%,有2人;明代占20%,有11人;清代0;占总数11.3%,共13人。这4个派科举成功者共90人,占总数的78.26%。而这4人派恰恰就是在12派中向远地城镇迁徙最为活跃的派别。潜口派“商游荆襄”者居多,其49世方勉“永乐辛卯(1411年)举人,乙未(1415年)进士,由庶常历官湖广布政司参议,进阶亚中大夫,尝篡家礼辑谱牒”[①j]。潜口派在荆襄的活跃与方勉在湖广的“势”有关联。柘田派南下福建,北上汴梁、山东;环岩派则以扬州为主,遍及各地。正因为“势”与“资”的结合,这4派宗族是方氏在徽州12大派中最为兴盛的。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宗族自身结构也相应作了调整。笔者在《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一文中曾对方氏4个支派的家庭人口作了统计,指出“明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次。家庭宗族结构概括地说,就是大宗族小家庭结构”。家庭规模的缩小可以避免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也利于商业经营。宗族圈的扩大,则有利于方氏各支派在远离本土的异乡经商时互通信息、互为奥援。扩大的标志则是修统宗祠、统宗谱、始祖墓。方氏统宗祠在歙县柳亭山,称真应庙。方氏在万历年间为真应庙产纠纷曾多次与异姓发生诉讼,三十八年(1608年)“庙业始复”,并形成十派“轮司祀事”的制度。康熙九年(1607年)12派“复立合同”,改由12派轮祀。方氏各派共同拟定《条议十则》,这是前所未有的统宗组织法。《方氏会宗统谱》是由方善祖(环岩派,59世)发起撰修的。这是个徽商世家,上溯到54世文辉即开始经商,至58世良孺“远服贾于江淮三楚间”。善祖本人也是“鬻财江淮间,延缘楚之西南靡不遍”[②j]。这个盐商家族对撰修统宗谱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乾隆十二年善祖向徽州本土及迁徙异地的方氏各支派发出《会宗小启》,并亲任会宗谱总修,谱成后捐资付梓。除环岩派外,柘田、潜口、联临三派对会宗谱的撰修积极响应。会宗谱所收《家传》、《行状》、《墓志》共涉及传主58人[③j],12派虽都有先人被收入,但主要是根据其社会地位及对真应庙和会宗谱的资金投入而收入的。环岩收传主19人,占32%;柘田8人,占13.8%;联临6人,占10.3%;潜口4人,占6.9%。这4派占传主总数的63.8%。这个数字与他们在科举成功者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对应的。其他各派则分别在1至3人之间。值得一提的是苏磻派收入5人,占8.6%,居第4位。这是因为真应庙在苏磻派居住的苏村附近,他们对真应庙的日常管理承担起最大责任。环岩等4派的热情以及12派的普遍投入,证实了宗族圈扩大的趋势是与方氏的迁徙和商业经营活动相关的。明清时期方氏各派的族谱也直言不讳地阐述这种关系,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桂林方氏谱序》云:“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也。”嘉靖戊申(1548年)《重修方氏家谱序》云:“凡族属之逾于五服,其疏者也。而视同祖于玄英不又有间乎?等而上之,为世益邈,为属益疏,然苟同所出则同所宗,同所宗则同所亲。虽百世之外,千里之远,一旦遇而相考识焉,其与夫途之人不犹有间乎?是故言乎宗亲则蔼然同矣。”嘉靖辛酉(1561年)《方氏族谱序》,系由莆田方氏族人万有所撰。谱序谈到《莆阳方氏谱》附有方氏浙、广二派的《鄞谱略》和《广谱略》,表示希望能得“《歙谱略》归并藏之”。合谱的动议,“千里之远,一旦遇而相考识焉”,足见“联其族”是“为其实而已”。
远徙经商者往往在定居的城镇建造宗祠。《歙事闲谭》第7册载方士*[原字广内加捷去手]“性孝友睦族,创建宗祠于扬州,置祀田”。同时,他们对于家乡本土的统宗祠及支祠的修建也十分热心。《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载,清初(真应)“庙貌全堕,祠祭不备”。于是“维扬征收,输银肆百叁拾两,竣役于庚戌(1607年)”[①k]。由统宗祠谱到各地的分祠谱,血缘纽带编织起方氏的。
血缘网络继续扩大则为地缘网络。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十分精辟地指出,徽商“建立起一张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一些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如北京、山东临清、南京、扬州、汉口、苏州、杭州、广州等,都是徽商麇集之地,它们是网络的枢纽和基点。网络从这些基点再散衍到周边的村镇”[②k]。宗族圈的扩大,对传统中国的转型起了积极作用,它造就了地域性的徽州商帮以及“无徽不成镇”的局面。正是在这些江浙市镇滋生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
宗族圈的扩大,也为地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多山的徽州其内部的开发,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毕竟是有极限的。迁徙以及徽商利润源源不断地返回徽州,解决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以前述唐川村和磻溪村而言,据笔者调查,民国时在家与在外的人口比例为2∶1,在家的大多靠在外经商的人养活。这在徽州是普遍现象。但是,宗族制度的应变力和顽强的再生力,虽然可能一度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利于社会转型的启动,然而它最终是与社会转型异向的。
注释:
①a 方弘静:《方氏家谱序》(万历二十二年)。
②a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一。
③a 万历《歙志·风土》。
④a 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前卷,第32页。
①b 《新安名族志》前卷,第32页。
②b 方善祖总修《方氏会宗统谱》(乾隆十八年刻本)卷二《历代谱牒序》,第2页。
③b 同上,卷一八《碑记·后汉故大匠卿兼洛阳令加拜太常卿黟县侯赠尚书令丹阳方氏之碑》。
④b⑤b 同上,卷一七《庙额·敕赐黟县侯庙额》,第63页。
⑥b 同上,卷三《原始世系》,第3页。
⑦b 同上,卷一《存疑》,第11页。
①c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修谱表·诸宗修谱人物表》,第20页。
②c 《三国志·贺齐传》。
③c 《隋书·地理志下》。
④c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六《联临分派世系》。
⑤c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五《方村分派世系》。
①d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三《磻溪分派分系》。
②d 《方氏族谱》抄本,原件抄自三十年代,现藏磻溪方德礼家。
③d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
④d 《方氏会宗统谱》卷八《瀹潭分派世系》。
①e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一《苏磻分派世系》。
②e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家传》,第24页《方元之先生传》。
③e 同治《黟县三志·艺文志》。
①f 参见拙作《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研究》1991年第1期。
②f 《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f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
④f 关于方腊的出身,《宋九朝编年备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青溪寇轨》等均载方腊“家有漆园”;《桂林方氏宗谱》中元人刘彭寿、徐直之的两篇传记,则称方腊系“佣人”;民间则有方腊为“桶匠”的传说。关于方腊的籍贯,则有淳安(青溪)说与歙县说之分。
①g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②g 《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g 《续修柘源方氏宗谱》(明天顺年间)。
①h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四《柘田派分罗田》。
①i 参见拙作《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论徽州海商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①j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潜口派上方支》。
②j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九《墓志》、卷二○《赠序》。
③j 传主58人中,业儒或入仕者17人,义士3人,商人23人,手者1人(族谱刻工之父),妇女14人(其中明确为商人妇者7人)。始祖方储及12派始祖传记未计入内。
①k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八《纪事》。
②k 《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上一篇:乡镇企业改制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