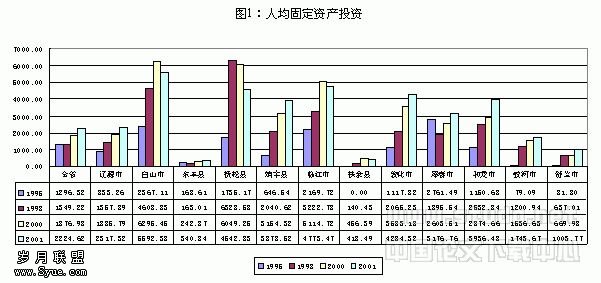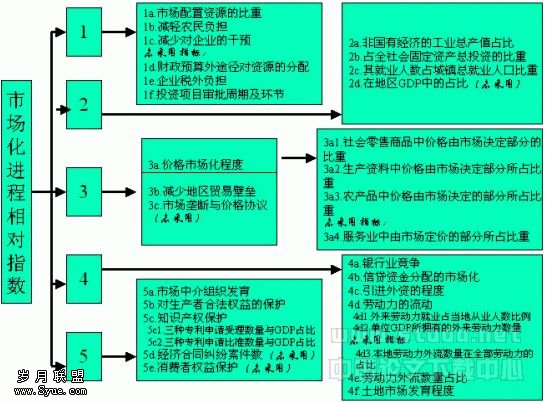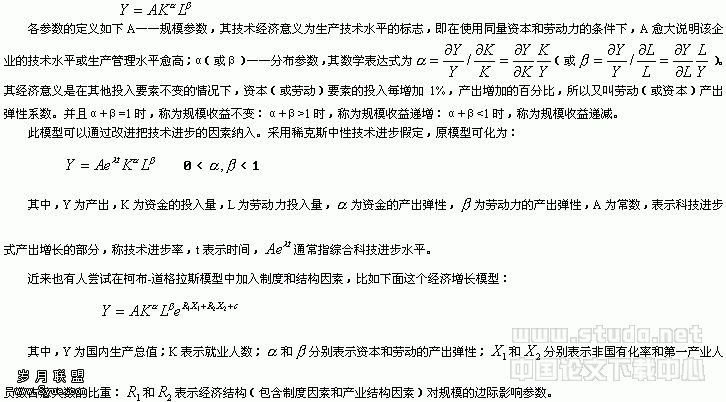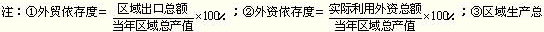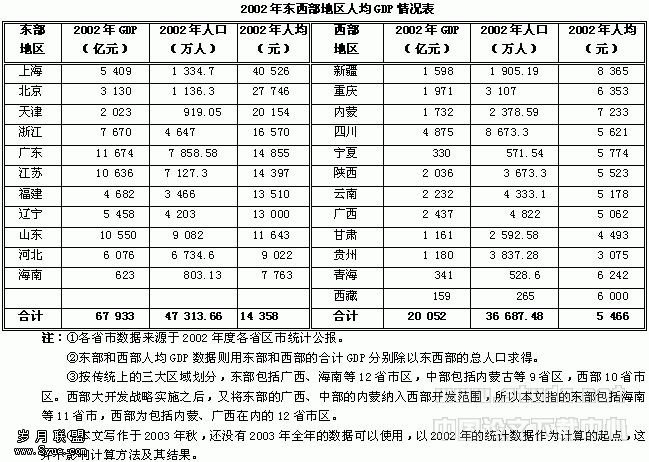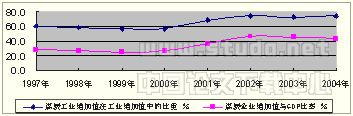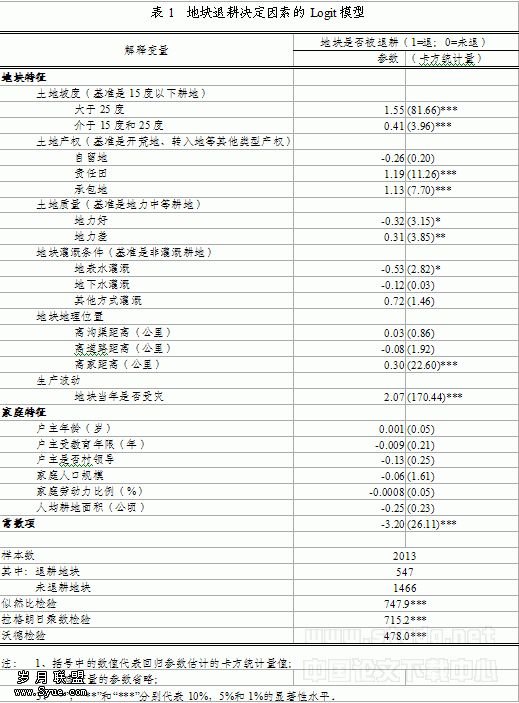道德的共同体:教育的政治哲学观
【关键词】道德 共同体 教育
【作 者】叶国文,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陈洁,宁波大学
今天许多社会成就的获得无疑应该直接归功于教育。但是,教育在塑造成功者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社会诚信等问题,导致福山认为的“大分裂”,使作为社会黏合剂和共同规范的道德缺乏共同体的支撑而失去效用,结果是人类再一次面临兽性化的问题。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教育普及化的问题在于,它在成功地实现了参与的民众化的同时,却削减了教育本身的政治功能。”[1]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也许只是杞人忧天,但从教育的逻辑看是确实存在的。
一、教育的逻辑:教育与道德的疏离
首先,教育的世俗化。诚然,今天的教育提高了我们的专业素养,但在功利、实用等商业精神的影响下,已经逐步异化为工具性、应景性的临时加工过程。一方面,教育的涵义简约为通过标准化的获得资格认证的工具。人只是为了获得标准化资格认证的“一种受约束的、循规蹈矩的动物;”[2]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只为当下流行的资格认证工作服务,既没有对过去的继承,也没有对未来的考量;再一方面,教育的结果和目的在于世俗的成功—发财或者得到一个好的地位,使人做一个平常的人或学会立身社会的技术。结果,受教育越多,思想和精神生活变得越萎缩,因为他们只需要一定量的机械式的才能而不需要生动的思想。[3]结果,对居间其中的人类来说,教育是使人平庸而不是高尚。
其次,道德多元主义。伴随世俗化对教育的要求,按照个人标准出现的道德不断云涌。正如布鲁姆所说,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一种崭新的关于道德善恶、人类行为标准的语言开始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诸如自我、存在……等等语汇已经广泛见诸于人们的日常语言。”[4]每个人、每个文化都是合理的,由此推而极之,“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就殊难判定,从而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只要有所信奉、有他自己的价值择定,不管其信奉或价值的内容如何,就是好人。”[5]在这样的时代,道德获得了新生,但它不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道德,而是一个多元的道德。“要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和高贵的人,就不能去追求或者发现善的生活,而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样式(life-style)'。”[6]于是,原来道德蕴涵的共通性消失了,“今天,人们不可能再坚持认为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道德。”[7]这一方面源于教育的结果——主体崇拜,他们导致了多元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道德多元主义进一步疏离了道德的共通性。结果,推动人类追求高尚、优秀的动力消失。教育产生了多元道德,公共道德却走向沦丧。
其三,道德教育的异化。也许人类认识到了这种公共道德沦丧的可怕后果,于是各种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加强了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然而,一方面,现在的道德教育“不能给青年人的想象展示道德秩序和惩罚扬善的景象,不能提供伴随行为和解释行为的高尚演说,不能展示道德选择剧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行为,不能揭示处于这样的选择之中人的利害关系感,以及当世界破除传统忽然'醒悟'时给人们带来的失望,” 只有空洞的说教和无物的宣泄;另一方,这种没有的道德教育,仅仅是“灌输'价值观念'的徒劳形式,”[8]它不仅不能产生道德本能,相反导致道德逆反,道德教育成为道德的异己力量。
可见,今天的教育,一方面,渗入了商业精神塑造的理性标准,使实用、功利和自私重新成为我们的“德行”,我们在强调权利的同时忘却了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摒弃了传统高尚道德的追求。教育不再讲求友爱、正义和共通,结果“用以把成员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历史、习俗、语言或教育中的铠甲,正在逐步地变得越来越破旧不堪,”[9]维系或整合共同体秩序的这种政治或道德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弱。共同体随着教育与道德的疏离而走向衰落。
共同体的衰退显示,将来我们可能会变成只关心己事、追求私人安慰的商业成功之人,忘了为更高的目标进行有气魄的努力;或者在自我满足和繁荣的自由民主中,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社会体系可以满足所有场所中的所有人,人类成为没有归宿的野兽。因而,以唤起美德为内容的英雄主义,将在尼采预示的“无限战”中出现,人再一次回归“第一个人”。难道教育真的使“人类在文明形式下的重新野兽化”?[10]
二、共同体道德的解救:洛克与卢梭的教育观
教育与道德疏离,使人类面临共同体解体带来的危险,在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认识到,并试图通过各种努力寻求解救之道。十七、十八世纪的洛克和卢梭就是其中两个具有比较代表性的思想家。洛克提出自由、理性的“绅士”道德教育观,从而把社会人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绅士,继承和维护共同体的道德。卢梭则试图通过对的“回归”,在自然教育中恢复人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的一种正义和道德”,[11]并通过公意这种公共道德体约束和规范个人道德,实现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共通,重新恢复传统共同体的道德理想。
(一)洛克的道德教育观。洛克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私人的,更是为共同体服务的。他认为“教育上的失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失误和配错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12]不仅如此,教育还关系到“国家的幸福和繁荣”,[13]
洛克指出,“人心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符号,没有任何观念。”[14]“我敢说我们的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5]正因为如此,他认为通过接受教育和感化,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洛克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他反对普遍教育方法上叫儿童记住许多规则和教训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总是随时学到又随时忘却,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给予被教育者充分的自由。自由的教育,一方面可以在快乐中学会需要的知识,另一方面“刚毅自由的品行能够保持他的德行。”[16]因而,教育不需要注重各种规范,却十分强调榜样的作用,并把实践作为教育十分重要的内容。其目的是被教育者在榜样的引导下、在实践中自由发展并获得克制的能力,培养优雅和崇高的德行习惯。他相信,“人人总有一个一切纯凭自己与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一个善良的、有德行的、能干的人是要从内心去养成的。”[17]
同时,洛克的教育是道德教育。他的教育有一种严厉、自我克制的道德要求,而不是消费享受和人人随意自发的行为。如他谴责酗酒、耽于夜夜笙歌、因虚荣而花费、流于懒惰又浪费时间等行为。他认为“幸福建立在德行与良好的教育上面,那才是唯一可靠的和保险的办法。”“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会今生来世就得不到幸福。”“青年人失掉了德行是很难再能恢复的。”[18]而“一个没有德行,不懂人情世故,没有礼仪,却有成就的人,哪儿都是找不到的。”[19]“德行是真实的善,导师不只应该进行劝导谈论它,而且应该利用教育的工作的技巧,把它供给心理,把它固定到心田里面,在青年人对它发生真正的爱好,把它的力量、荣誉和快乐放在 德行上面以前不要停止。”[20]这些观点说明,洛克强调个人德行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政治共同体服务。塔科夫认为洛克的道德教育“并不局限于他们的私生活,它有个特别具政治含义的目的,”[21]为政治共同体培养好公民。道德教育出来的人“不仅能处理自己的事务,又能有助于管理自己的国家。”[22]“尽心竭力地给祖国服务,乃是每一个人不可不尽的义务;谁若没有这种想法,他变得与家里的牲口没有什么区别了。”[23]所以,洛克教育的绅士是有教养、有操守和担当、有产业和独立谋生能力、佩剑,又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教育和政治一样,“最终都为达到使人民成为健全公民的目的。”[24]
由此,洛克的教育是通过自由、理性教育,实现个人的绅士化,然后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自由道德教育观。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自由教育。这是道德教育的前提,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理性,更不可能培养具有崇高个人德行的绅士;二是共同体的道德教育。这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借助个人绅士化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绅士化,使个人与共同体的道德同构,维持并增进共同体的道德,解决共同体瓦解的困境。
(二)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是有道德的。但是,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人被迫成为社会的人,而枷锁一样的社会状态中却充满了贪婪、虚荣、仇恨、压制和冲突,人由此失去了自然状态中的本真性,失去了对善恶的关怀。“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人道、礼仪和崇高的原则,我们现在却只有一种浮华的欺人的外表,没有道德的荣誉,没有智慧的理性和没有幸福的欢乐,”[25]这是产生不道德和道德堕落的根源。所以,卢梭的教育目的是恢复人的本性,并通过公意恢复个人道德和共同体的道德。
首先,自然的道德教育。卢梭认为“现存的教育是不平等的社会的帮凶,它把人像驯马场的马那样加以练习;把人像花园的树木那样,弄得歪歪扭扭。”[26]因为现在教育是理性的教育,试图从外部灌输进教条,于是不得不用管束来达到目的,而不是像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教育,是从人的内部去呵护良心,因而道德的解救是回归人的自然本性。道德教育就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最好的道德就是自然的道德。
所以,卢梭的教育是把爱弥尔带到乡下,在人性的自然和纯粹的自然秩序中获得道德的品格,形成自然人。这种自然人“在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良心。”因此,“邪恶即使具备了神威,也徒然从上天降临人间,因为道德的本能是不让它进入人类的心的。”[27]除此之外,为了使良心免于受到侵害,卢梭通过英雄故事、寓言等教育爱弥尔,因为英雄故事和寓言就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在与自然和英雄故事、寓言等教育中养成了自爱。自爱始终是好的,也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我们首先要对自己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原始情感是以我们自身为中心的;我们所有一切本能的活动首先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我们的幸福。所以,第一个正义感不是产生于我们怎样对别人,而是产生于怎样对我们。”[28]只有这种保有良心的自爱在自然的秩序中充分展示,付诸实践和行动,自然人的道德才能是完善的,才能使人自然地凭借正义和道德去向善和行善。
其次,整体道德。卢梭在强调自然道德教育的同时,也承认人类进入社会状态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人类“不能始终是那样地单独生活,他们要始终保持那样的善良是困难的。这种困难还必然随着他们的利害关系的增加而增加,何况还有社会的毒害,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不能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和办法防止人心由于有了新的需要而日趋堕落。”[29]这种手段和办法就是通过契约组成共同体,因为“我们所谓的'善',就是由于爱秩序而创造秩序的行为,我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由于爱秩序而保持秩序的行为,”[30]只有共同体的秩序才能确保善和正义这些传统道德。
卢梭的契约为实现这种共同体的整体道德提供了可能,即在自然道德的基础上,契约订立者让渡互相可以认知的自由和道德组成一个意志共同体--公意。在这种共同体下,尽管个人仍然享有自由,但共同体是强制的,个人是服从和归顺的,“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31]于是,在共同体中,有一种强迫个人服从道德的要求。这种道德既是公共道德又是个人道德,它是防止进入社会后道德堕落的一种强制但自由的手段和办法。一方面,个人道德的自然化,即恢复个人的至善;另一方面,通过公意这个共同体实现公共道德,而公共道德是个人道德的整合,因而既可以保持个人道德的纯真,又能实现共同体的公共道德。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的回归和公意的指引,重新在人身上培养出原始的道德的直觉,从而使人成为共同体的人。
卢梭试图通过自然人的道德教育,恢复天赋的正义和道德的良心,从而使人以纯真的感情进入社会状态,然后通过公意(公共道德)使人能在社会状态保有并维持道德,实现公意共同体。由此,人的自然道德本性与共同体的道德就实现了互洽。
比较两者的解救之道,尽管有一些不同,如洛克希望通过理性实现道德教育,而卢梭却极力反对,认为这正是导致道德堕落的原因,但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下列两点尤为突显:一是强调个人道德教育是拯救共同体的前提,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不管是洛克的自由教育还是卢梭的自然教育,都是使他免于“活在自己以外”(洛克和卢梭均指人不应该活在自己以外,即人不应该活在他人满足自己的需求之上,亦即活在对他人的依赖之上),[32]这是人的道德本能,也是道德回归的基础;二是为共同体提供服务。洛克的道德是建立在已有政治共同体基础上的,道德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适应现存共同体体制的好公民—绅士,而卢梭则不满于现存体制,认为现存的社会是道德堕落的根源,因而目的是为他的道德理想国—具有道德的公意共同体培养公民,所以他们的道德教育的目的都是政治的,也就是都为共同体服务的,而这正是传统教育观的道德诉求。
三、传统观:道德的共同体
尽管洛克和卢梭提出不尽相同的恢复共同体道德之道,但他们思想深处的一个共通之处却是无法抹去的,即对传统教育的追念。
在西方启蒙运动以前,尤其是古希腊,有一个共同体(城邦)在先理念,认为城邦是具有神性的,“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33]作为人类最高的道德的善体现在共同体中,“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所以“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34]教育就是如何使人成为城邦的动物,如何实现这种最高的善,因而古希腊的教育是道德教育,一方面通过教育成为城邦公民,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使公民在语言和行动中体现符合自己的德行,正如在查拉斯图拉那里认为的,教育是一个雕塑过程。当然,“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35]称为雕塑是指教育消除外界对心灵本性造成侵害的东西,同时把传统的道德固定化的过程。“心灵的优点似乎确定有比较神圣的性质,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的能力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它可以变得有用而有益也可以变得无用而有害。”[36]教育就是使“被习惯毁坏了迷盲了之后重新被建议的这些学习除去尘垢,恢复明亮,”[37]因此,古希腊的教育是一个道德教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教育、学习是实现个人德行和共同体道德共通的一种途径。因而,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就是教育,即通过和培养公民成为“显得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而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的人。”[38]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特别强调对护卫者的教育,尤其是其中的音乐教育,目的就是把音乐所叙述的故事内化到护卫者,成为护卫者的一种本能,使之行动本能化,符合勇敢的激情,同时克制激情的过度,不僭越其职份,实现个人德行,而这种德行同时也是共同体的道德需要。所以,传统教育实现了共同体的灵魂和个人灵魂的同构,是追求最佳制度的“大事。”因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好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39]这种秩序,只有具有为正义而甘愿牺牲但又坚守职分的护卫者才能做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共同体中像护卫者那样的公民,才能自觉实现康德那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道德律”。
在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中,人必须克服心中的私欲,成为卡尔·波普尔的“齿轮精神”。古希腊美德的核心是参与城邦、服务城邦、献身城邦的公共美德,“要求把城邦当成'大学校'培养新型公民。”[40]在关心他人、城邦中,获得个人的最高的善,教育的结果是城邦的公共利益绝对地在先于个人利益。
与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一样,传统的教育也是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1]显然,中国传统教育是道德教育(至善),至善主要是官员的事(明德、亲民)。在中国古代,有道德的官员被称为君子是显例。清儒陈立在《疏注》中注曰:“君子,在位者之通称。”[42]东汉的《白虎通义》也指出:“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43]君子“既指有官位的人又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44]君子就是道德的实践者—有德行的官员。这与孔子的“为政以德”相一致,蔡元培认为“孔子之言政治,亦以道德为根本。”[45]因而,传统中国的“教育是伦理的,亦是政治的,教育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培养良好公民,以孕育他成为一个完人的德性。”[46]显见,中国传统教育是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道德教育。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先贤,孔子整日孜孜致力于品行的切磋、道德的培养,为君子、为仁者、为圣贤是他的教育目的。对于德行不好的人,则严厉加以斥责,“季氏富比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47]从教育内容看,也显见是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对此,“正义曰: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48]文、行、忠、信显然是成为君子的道德之道。因此,朱维铮教授谓之“特点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使学生通过学习知识,从谈话到行为,从意识到作风,都逐步养成君子的风格。”同时通过“礼”教,“将教育活动当作参与政治的一种途径。”[49]
要之,中国教育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的最直接目的是培养君子。君子是从政者,再附之以三纲五常等礼制和德行,使君子成为先贤或者圣人,这是一种从个人道德教育开始,通过政治共同体的道德同化和提升,实现与政治共同体共通的过程。这与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使人成为好公民并在其中追求个人和共同体最高的善目的,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四、道德教育:共同体的政治理解
在道德教育被淡漠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道德教育的诉求,其原因在于道德教育对人类社会,尤其对人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合法性。今天,许多学者提出了合法性问题,其主要在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为共同体提供权威支撑。在主体崇拜的时代,任何与主体没有共通的权力体系已经失去了效力,本来“道德不只是一个习惯体系,而是一个命令体系。”[50]这个命令体系不是通过强力实现的,而是一种本能的追求,因为它是自己对自己的服从。然而,公共道德的日渐缺失,不由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人共有的目标和公认的美德不存在了,社会契约还可能存在吗?”[51]因为社会契约存在问题,共同体权威合法性也就存在问题。而在“古代学校之于政事,乃密切相关。《白虎通》所谓'行礼乐,宣教化',此乃政治上之莫大任务。”[52]教育,本质上是道德教育,目的是为共同体的权威提供合法性。
其次,整合力量。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激战时,两位古希腊的巨人却能够抛弃战争而谈论理想问题。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希腊就要陷落了但传统的希腊道德不会丢失。只要道德存在,人与人就有共通之处,共同体就有存在的基础。“道德的功能是把个人或几个社会群体连接起来,而且道德是以这种依恋关系为前提的。”[53]然而,后来的战争却把这种共通性也一起毁灭了。由此,克服异己、解决冲突的基础消失了,整合的力量也没有了。所以,战争成为常态,和平反而是变态。人们曾经以为商业一体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54]然而,商业精神不仅不能解决共同体的整合问题,反而加剧了这种分离现象,只有道德才能扮演这种整合的力量。因为“正是通过(道德)教育,才产生出那些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出来维持国家的人。”[55]
其三,秩序。涂尔干认为,“在权威观念扮演着绝对优先角色的地方,道德才能构成规范的范畴。”[56]现在的权威受到挑战已经是事实,究其根源来自道德的缺失,而这导致了规范失范、秩序失序。因为,“在社会秩序中,所有的地位都是有标记的,每个人就应该为取得他的地位而受到教育。”[57]道德教育是迈向正确政治秩序最必要的一步,并把这种教育和立法作为统治者两项最主要的责任。[58]所以,道德是确立权威观念、构成自范、产生并维护秩序的基础。
其四,政治共同体。康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人的所有能力得到完善的发展。使每个人认识和热爱共同体、参与共同体、追求共同体的卓越性。但是,今天的社会代替了政治,人是自主的,但没有偶然性,没有创造和激情,只是社会的一部机器,没有追求卓越的动力。“公共领域都分裂成许多对立的利益团体(或文化身份),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念、情感和话语,及其经常对受害者的认同诉求—所有这些都在远离一般政治领域,有时甚至是与其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59]于是出现了“认同的困惑”问题。康德认为,个人作为道德人格,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靠共同体形成的。“道德目标也就是那些以社会为对象的目标。而合乎道德地行动,也就是根据集中利益而行动。”[60]所以,只有恢复公共道德,才能使人具有共通性,人才能在共同体中过政治的生活。
四、结语
教育的目的是个人德行的卓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61]这是个人的道德教育。而教育不仅仅如此,它还有更高的道德使命,即使人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固有传统规矩和秩序,不使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败坏。所以,钱穆认为,“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自己的传统。”[62]
然而,我们的教育已经没有的道德的目的,个人已经没有了追求卓越的动力,共同体的道德也渐渐缺失,那么是不是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既然我们所说的古老的个人目标已经不够了,那些绝望的人把自己托付给社会的信仰,放弃对他们父辈来说已经足够的个人崇拜,那么他们就会尝试通过一种新的形式让城邦国家的膜拜复兴起来”[63]?
注释:
[1] 特伦斯·K.霍普金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1945-2025》,高等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3] (英)伯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96页
[4]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5]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6]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7] (美)弗兰西斯·福山:《的终结》,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第385页
[8]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57页
[9]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性》,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63页
[10]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第147页
[11]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14页
[12]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13]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14]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Dover Pub. Inc, 1959, p57
[15]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16]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17]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0页
[18]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8-69页
[19]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20]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21] 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三联书店2001年,第307页
[22] 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00页
[23] 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三联书店2001年,第24页
[24] 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
[25] 维·彼·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3页
[26]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27]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14页
[28]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3页
[29]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1页
[30]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3-404页
[31]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
[32] 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三联书店2001年,第174页
[33] 亚里士多德:《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页,1252a
[3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页,1253a
[35]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7页,518b-c
[36]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8页,518e-519a
[37]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527d
[38]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5页,412e
[3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9页,1253a
[40] 刘军宁:《美德与黑暗时代》,见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
[4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
[42] 转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43] 转自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44]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6-157页
[45] 蔡元培:《中国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页
[46] 陈大络:《儒家政治、伦理、教育思想的管窥》,见《中华文化》1994年第1期第61页
[47] 《论语·先进》,见杨伯峻注译:《论语》,岳麓书社2001年,第99页
[48] 李学勤主编:《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49] 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76页
[50] 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51]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52]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页
[53] 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54] 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和罗尔斯的“万民法”就是这种观念的显例
[55]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56] 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57] 卢梭:《爱弥尔》,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13页
[58] (英)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7-268,577页
[59] (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
[60]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第60页
[6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3页,同见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33-1034页
[62]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229页
[63]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