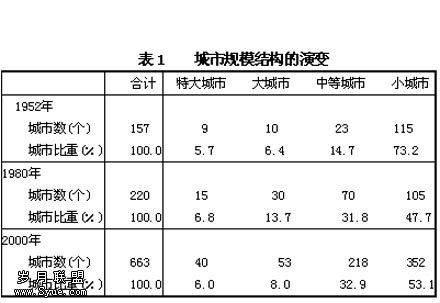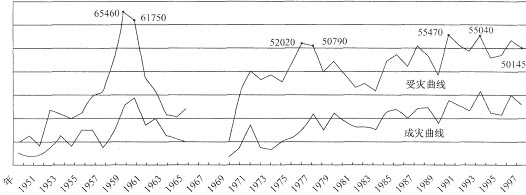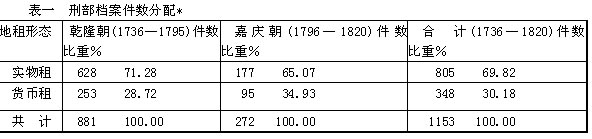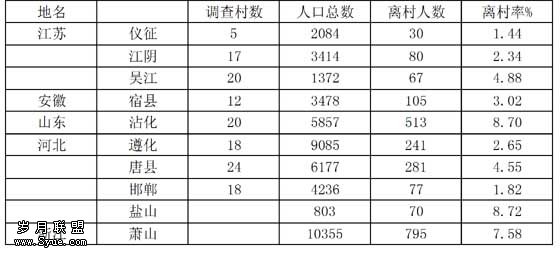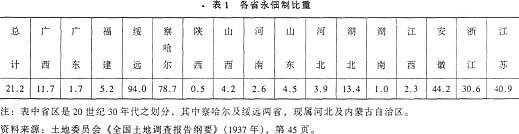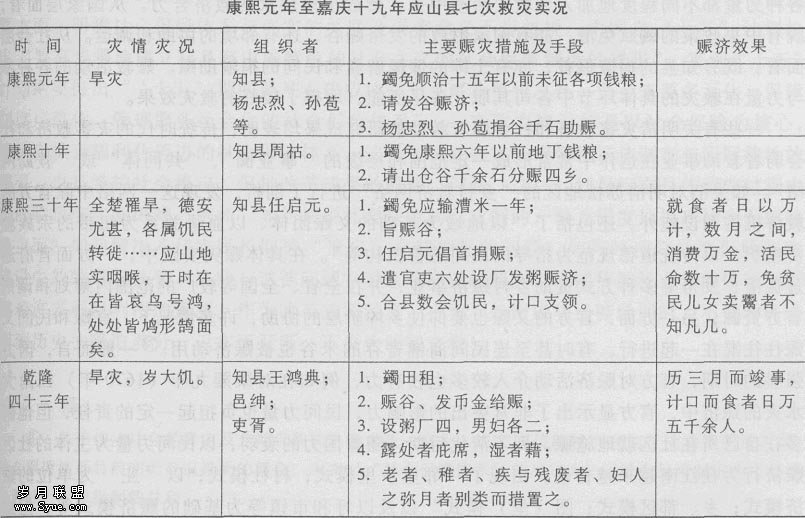浅论网络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及其社会控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论文摘要: 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采取有效社会手段控制社会谣言,意义重大。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所强调的“遗忘”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成为“以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发布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发布“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发布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发布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新闻网》,2003.5.9)”。
: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法]卡普费雷,1991,《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社会的崛起》,社会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8]编写组,1987,《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9]邓东蕙主编,1993,《实用社会心》,南京大学出版社
[10]董娅,2006,《困惑于超越--西方文化与转型期的中国青少年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一篇:浅论农村气象信息的具体保障
下一篇:论全球化的网络结构